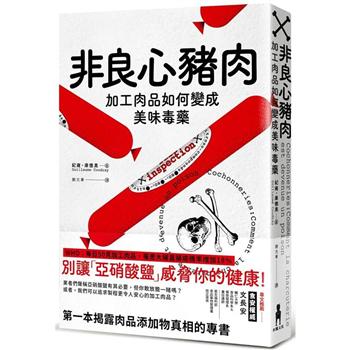新春試筆
星野兄來函,囑我為中央社撰稿,星野真熱腸人也。函中未明言如何發表。若謂每週撰稿,只是報道紐約消息,則未敢從命。若一月兩次三次,說說話,借此使國內外文人得通聲氣,自是不錯。記得 《 人間世 》 發刊詞,曾作數語,以表此意。原文不在手下,大意謂 《 人間世 》 略如世人點卯下班之餘、飯後無聊之際,批讓既平,長夜縵饅,何以逍此。忽逢舊友不約而來,排閥而人,不衫不履,亦不揖讓,亦不寒暄。由是飲茶教舊,隨興所之。所謂或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言無法度,談無題目,所言必自己的話,所發必自己衷情。夜半各回家去,明晨齒頰猶香。如此半月一次,以文會友,便是 《 人 間世 》 發刊詞之本意。
前 《 紐約時報 》 有艾金蓀( Brooks Atkinson )專撰劇評。此打在抗戰時,曾住重慶一二年,國內當有知者。因其別具文學眼光,不捧場,不敷衍,成為劇評權威。凡百老匯新劇開演之夜,老闆捏一把汗,未知艾君以為可取否。後來艾右以年老退休,《 紐約時報 》 給以專欄,不拘題目,聽其自由,眼界一新。艾君讀古書多,看新書少,故有其獨特見解及風趣。憚壽平謂不落畦徑,謂之土氣,不人時趨,謂之逸格,畫事如此,文章亦是如此。創制風流,在於學者。政治非不可談,能談者甚多,且目前急要消息,明年看來,便成隔日黃花,以明年讀今年所作,當啞然一笑。住紐約尤易入此圈套,看日報人多,看週刊月刊人少。無論何事,朝報宣揚之,織之以晚報,繼之以無線電,又繼之以電視。電視一而再,再而三,由是轟轟轟頭昏腦脹,以為世事除此一事外,別無他事。及時移境遷,向之所謂非談不可之陳跡,今日連記也記不得,更無所謂感慨繫之。此報紙弄人也。每到法國,便如跳出此圈套,心曠神怡。況政治舞台,亦如觀劇,劇情有緊張、有散漫者。甘乃迪總統被刺,一旦成為英雄,在專長轟轟轟之美國報界,幾乎奉為聖人。有專書,有電影,有甘乃迪飛機場,有甘乃迪太空發射場。於是甘乃迪之哥哥,弟弟、夫人、幼子、老太爺一舉一動,無不為電視及刊物之好材料。何苦呢?何苦來?
承星野兄之好意,囑我撰稿。政治既不足談,惟談文藝思想山川人物罷了。我居國外,凡三十年,不教書,不演講,不應酬,不投刺,惟與文房四寶為老伴,朝於斯,夕於斯,樂此不疲,三十年如一日。星野兄叫我擁重兵,征西域,必謝不敏。叫我揮禿筆,寫我心中所得,以與國內學者共之,則當勉強。美國編輯,倒有一樣好處,凡文稿不好,雖為名作家所作,亦請修改,或退稿。故美國出書,絕無送人情之事。大約每月二次至三次奉上一篇,或意到筆不到,或意思平平,無甚可說,請刪節或投之字紙簍可也。
論色即是空
我們山居,商外所見的是竹籬茅舍,廊外所見的是稻田菜畦,滿目蒼蒼橫翠微,飽享眼福,自妖一身心偷快。半夜蛙聲呱呱,破曉鄰舍雞嗚,覺得這都是應該的,自然的。城居高樓大廈,離地甚遠,又水泥大道,全無曲折,宇宙文章,已不復見,白雲蒼狗,偶爾一瞥而已。想來少年青松白石之盟,至今始遂心願。我就不相信,這蒼綠一片山陰滴翠的景色,就是空空。
近閱報載,洛杉磯某少年,因吃新近馳名的靈感藥,名 LSD ,覺得四大皆空,正如佛家所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藥實在靈,於是少年橫立大街中,看對面汽車來,只當幻影視之,原來色即是空,乃被車軋死。據報載,美國政府的藥物管理局稱,美國大學生,估量有幾萬人曾經或是常服這靈感藥。好萊塢和紐約百老匯的戲業董事人,戲劇批評家三位同意,電影及戲台的演員,有六成常服這藥。所謂靈感藥,就是因神經受了某種的刺激,特別敏感,如醉如癡,如眼前景物,忽變為燦爛世界,紅的、綠的、黃的、藍的,各色異樣鮮明,像萬花筒,變幻無已。同時精神特別興奮,或者翱翔天空,或者掠水走過,都不算一回事。因此平常人也有好奇心,偶然嘗試一下,倒不一定成癮。美國醫藥管理局,因為這藥對於心理病態的研究有正當用途,所以也反對完全禁用。現在美國人說起 LSD ,如。DDT(減蟲散)一樣,大家知道。 LSD 即Lysergic Acid Dithylamide 之簡,是取某種菌煉成的。以前希臘詩人荷馬紀載,也有Nepenthe ,吃了可與神仙為友,荷馬書中又有「吃蓮子者」Louts Eaters,舟子到那島上,吃過都樂而忘返。這正與古書所謂不吃人間煙火相同。至今西文稱遠東人的雅號,亦稱為「吃蓮子行」。近代Lafcardio Hearn專講日本文化最常用,前三四年Arthur Koestier 漫遊日本、印度,書名即 《 The Louts and The Robot 》。最引起並普通讀者注意的,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 《 妙見之門 》 一書,一九五四年出版,專講吃這種藥的人的經驗。赫胥黎氏及以前多瑪,赫胥黎(贊助達爾文而著 《 天演論 》 的作者)之係。他的哥哥Julain梁利安,就是聯合國文教組UNESCO的創辦人及第一任總幹事。所以這位已故的文豪,我於一九四八年在巴黎會過。Aldous注意印度運氣攝生之法,因及這些事超乎尋常敏覺的經驗。但他所試的,是墨西哥印第安人的Mescaline (也是特種仙人掌所取出的),而 LSD 的效力卻比Mescaline高出千倍,服了可忘卻一切煩惱,看破俗見,神遊太虛,直上兜率天。但是吃了發瘋的也有。
這種經驗,自然與佛法「色即是空」的猛悟相關,亦與各宗教克服物慾,克服肉身,以理與慾相對,靈與肉相對的態度不無關係,方法也有相同之處。中世紀天主教僧院也有長期禁食,長期唸經,長期思維(靜坐),鞭肉,及穿發衫自苦其肉身的辦法,以得到某種的超凡默示,如同佛家以襌定,穿「糞掃衣」及達摩面壁九年,以求證道,修得認識宇宙皆空之理。這都是克服物慾以得神感的特殊辦法。這些以理與慾相對,靈與肉相對的宗教看法,我都不贊成。戴東原在 《 原善 》 及 《 孟子字義疏證 》 專譏宋儒誤解孟子,別孟子性善之性為二類,氣稟歸人,理義歸天,說到理,「如有物焉」(像煞有介事),所以「宋以來之言理慾也,徒以正邪之辨而已」。赫胥黎說,這些以苦楚肉身達到超凡境界的辦法,現在都不必了,因為所需要的是「得到超凡入聖的某種化學元素而已」。
(以上一些材料,可以詳見於最近六月十七日 《 時代週報 》 (Time Newsmagazine ))
原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科學的,無可訾議。英國科學家 A.S. Eddington《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所言最詳。我們所見所觸的杯然椅桌,無一非空,只是原子結合而成,而原子中間電子繞中心,亦如日會行星繞日之太空。西方哲學家Hume Berkeley以至康德所言,與佛經形而上學的論證無異。也可以說釋迦所見,遠在康德之前。佛教哲學之所以令學人看得起,就是這闢妄見的論證。只不該因此而求寂滅,度說輪迴的無邊苦海。佛家的道理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可憐的人生」何苦來?蘇東坡何嘗不知道色即是空?《 赤壁賦 》 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耳得為聲,目遇成色,即聲色乃我所見,非目無色,非耳無聲,聲色在我不在彼。所見聲色,非本來面目,非康德所謂Das Ding An Sich也。但是我所見之聲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而吾與子所共適」。林子亦願與東坡共適之,不要像釋氏那樣悲觀吧!
嘗閱陳繼儒 《 嶺棲幽事 》 論釋氏白骨觀法。我想靠這種人生觀求解脫,未免太慘了。「白骨觀法;想右腳大指爛流惡水,漸漸至經至膝至腰。左腳亦如此。漸漸爛過腰至腹至胸,以至頸頂皆爛了,惟有白骨。須分明歷歷觀看,白骨一一盡見。靜心觀看良久,乃思觀骨者是誰,白骨是誰。是知身體與我常為二物矣。又漸漸離白骨觀看,先離一丈,以至五十丈,乃至百丈千丈,是知白骨與我不相下也。常作此想,則我與形骸本為一一物,我轉寄於形骸中,豈真謂此形骸終久不壞,而我常住其中?如此便可齊死生矣。」據說服 LSD 亦常可以齊生死,一彭殤。生命雖無常,我不願意襌定,也不願意超度了。
此文可為「論色」第一篇,亦可名為「論色相」。今日「色」字,普通指「女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就是作「我有小毛病,我好女人」講。這是男子的看法,男子不是沒有色相的。在女人看來,這話說去就長了。但是人生處世,不可不把「理、性 • 色、情、慾」諸字弄清楚。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無所不談合集的圖書 |
 |
$ 238 ~ 623 | 無所不談合集
作者:林語堂 出版社:天地圖書(香港) 出版日期:2012-03-0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60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無所不談合集
林語堂寫無所不談合集。所謂無所不談,即是包羅萬有的話題。本書內容包括中國歷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近人近事、生活點滴及對歷史文化生活議題的個人觀感。
作者簡介:
林語堂先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十月十日生於福建省龍溪(漳州)縣。他曾獲上海聖約翰大學學士學位、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學位、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是一位以英文書寫而揚名海外的中國作家,也是集語言學、哲學家、文學家、旅遊家、發明家於一身的知名學者。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三本雜誌,提倡幽默文學,並著《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京華煙雲》、《風聲鶴唳》、《朱門》、《老子的智慧》、《蘇東坡傳》、《孔子的智慧》等經典名著。林語堂先生於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六日在香港去世。
章節試閱
新春試筆星野兄來函,囑我為中央社撰稿,星野真熱腸人也。函中未明言如何發表。若謂每週撰稿,只是報道紐約消息,則未敢從命。若一月兩次三次,說說話,借此使國內外文人得通聲氣,自是不錯。記得 《 人間世 》 發刊詞,曾作數語,以表此意。原文不在手下,大意謂 《 人間世 》 略如世人點卯下班之餘、飯後無聊之際,批讓既平,長夜縵饅,何以逍此。忽逢舊友不約而來,排閥而人,不衫不履,亦不揖讓,亦不寒暄。由是飲茶教舊,隨興所之。所謂或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言無法度,談無題目,所言必自己的話,所發必自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語堂
- 出版社: 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12-03-05 ISBN/ISSN:978988211982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6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