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瀕死的慰藉
當病人進入尋求靈性層面的支柱大於醫療照護的階段,
他們尋求的正是介於維續生存的醫療手段與死後宗教信仰之間的橋樑,
這也正是「臨終關懷師」存在的意義──
替瀕死的靈魂提供慰藉。
因為對於死亡的未知與恐懼,
人們常常避於面對,
連身為護理師的作者也曾經如此;
在照顧癌末丈夫的居家療養及臨終後,
她才因此瞭解臨終之人與家屬的身心變化。
癌末病人臨終之際沒胃口是正常現象,
想回家過自己最後想過的生活也是有可能的,
但家屬往往對此感到疑惑與憂心。
如果你是病人家屬,你會順從他的選擇,還是堅持著「為你好」的己見?
此時如果有第三方的人來傾聽臨終之人與家屬的心聲,或許雙方都能更加坦承面對各自的不同立場。
瀕死的靈魂不只僅限於臨終之人,
精神疾病患者亦是如此,
只要是單靠醫療手段難以應對的人,
臨床宗教師便可以從精神層面給予他們適當地心靈撫慰。
這也是作者想要實現的,醫療與宗教不再只是平行線,而是形成一個相輔相成的交會點。
「當病人需要護理師的專業技能時,我就以護理師的身分提供服務;
當病人進入尋求靈性層面的支柱大於醫療照護的階段,我就以僧侶的身分陪伴。
隨時為病人提供當下所需的協助,乃是最好的做法。」──玉置妙憂
作者簡介
玉置妙憂
作者玉置妙憂身兼護理師、護理教師、照護經紀人與僧侶。
出生於東京都中野區,專門大學法律系畢業。
由於體會到丈夫「自然死亡」臨終樣貌的美好,因而頓悟出家,前往高野山真言宗修行,成為僧侶。
因有鑑於台灣有良善且成熟的臨終關懷師制度,於2015年起每年造訪台灣,學習相關的制度,也會跟隨臨床宗教師一同前往病人的家裡進行訪視。回日本後也致力於發展日本安寧療養制度,目前於小岩榎本診所擔任護理師,工作之餘也持續投入靈性照顧的活動。擔任「一般社團法人照護設計實驗室」代表人,舉辦讓子女學習「父母的看護與照護」之「養老指南班」,以及讓護理師、照護經紀人、照護人員、僧侶學習的「靈性照顧支援培訓講座」。亦舉辦各種演講與座談會等多元活動。著有《先將您的杯子盛滿吧!》(暫譯)(飛鳥新社)等書。
譯者簡介
洪玉珊
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
旅居美國,曾任職於國會圖書館,現為自由譯者。目前為止的人生和用字遣詞都充滿驚嘆號,認為生活就是要為了旅行、美食、電影、動漫和演唱會四處奔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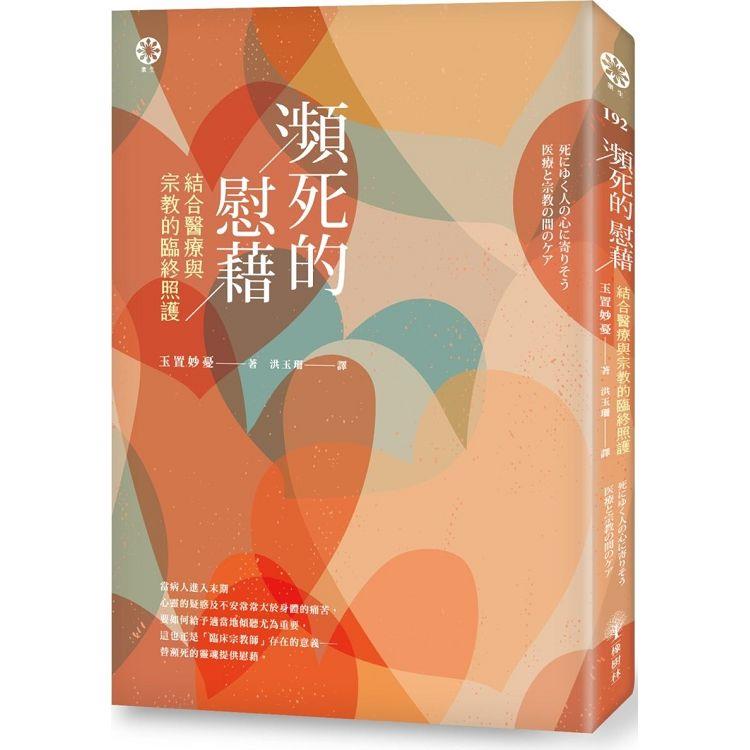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