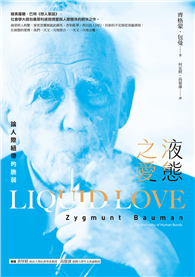前言
昨天我參加了狩獵海豹的活動。在清早八點,我裹著馴鹿皮,爬上一條獨木舟,滑進加拿大哈德遜灣的冰冷河水中。同行的人還有我的伊努伊特導遊和一支攝影小組。到了下午三點的時候,我盤腿坐在鋪著塑膠布的廚房地上,聽著男主人查理和他的家人,以及幾位部落長老開心地咯咯笑著,他們正連切帶撕地處理海豹屍體,弄開我們剛捕到的獵物的肉、脂肪及腦子。當查理敲開海豹的頭蓋骨,露出牠的大腦時,祖母開心地尖叫──她快速地用手指插進那團黏糊的東西裡。孩子們很負責地幫忙切開腎臟。他們的母親則大方割開一粒眼球(這是最精采的部分),然後向我示範如何吸出裡面的東西,彷彿她拿著的是一粒超大的康科德葡萄(Concord grape)。這群快樂的家庭成員分工合作,忙著從各種角度下手分解海豹,有時則停下來大嚼一塊美味的部位。不久,每個人的臉上和手上就沾滿了血污。儘管此刻活像電影《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的場景,而塑膠布上血流成河(相當多),屋子裡卻充滿著微笑和歡樂氣氛。隔壁那間一般擺設的客廳裡,電視機無聲重播著老電視劇〈牧野風雲〉(Bonanza),這時女主人正切下海豹鼻子和鬍鬚部位,指導我握著稻草般濃密的毛髮,吸食埋藏在皮革般肉裡的粉紅色小核。在徹底品嚐過生的海豹腦、肝、腎、肋排以及脂肪後,一位長者跨過地板拿來一盤冷凍黑莓,她大方地抓了一整把,在潮濕的屍體內面擦了一圈,沾滿血跟肥油後邀請我品嚐。說真的,相當好吃。
我一次又一次說不出話來。或者,是我失去了語言表達能力。對於那天的奇特事件,我描述地很傳神了,應該是吧……然而,實際上還差得遠呢。我該如何述說在那不起眼的廚房裡所擁有的親密感覺?十五歲的孫女和八十五歲的祖母面對面,幾乎是鼻子對著鼻子,然後開始「喉歌」(throat singing)。先同時用咕嚕聲以及快速的呼吸聲發音,然後開唱,聲調和歌詞是從她們嘴裡的某個部位發出的,從某個……其他地方?他們就在那種渾然不覺的喜悅(和驕傲)中將海豹大卸八塊──我該如何完美地描述這般場景?還有查理的樣子,他滿臉是血,有些還從他的臉頰淌下……祖母邁開馬步,用一把彎月型的菜刀劃開脂肪,將黑色的海豹肉一條條剝下。我該如何用語言將這副情景描述得恰當而美好,就如同其實際發生的樣子?
「如果沒有海豹,我們就不會在這裡,」查理說。「我們就無法活著了。」這樣的說法已十分貼切,卻還無法解釋真正的狀況。你必須親自去感受那裡的寒冷,親自看看那個數百哩沒有一棵樹的地方。你得跟著查理,就像我一樣,到那個冰冷的海灣,那片像海一樣寬廣的水域,看他穿過薄而傾斜的冰層將海豹拖上獨木舟。你必須親耳聽到,像我一樣,從查理的無線電裡傳來其他獵人那聽天由命的呼叫,他們整夜與暴風雪周旋,既沒有避風處,也沒有火堆。你必需親自在那個房間裡待過。照片無法表達一切,我心知肚明。在旅途中我帶著這些照片,不時拿出來看看──然而他們無可避免又可悲地平板,只能作為該地方的氣味以及身歷其境之感的可憐替代品。錄影帶呢?那完全成了另一種調調。你必須把用希臘文體驗到的東西轉換成拉丁文,把地方與人改編成另一種樣子,無論有多美、多有戲劇張力、多有趣,它依然是……不一樣的。或許只有音樂能捕捉那地方或那些人的感覺,如此貼近,你幾乎可以從空氣中聞到他們的存在。可惜我不會彈吉他。
這只是部分的片段。是一趟奇異旅程的某些花絮,也是我人生中較重要的、失序卻又美好的奇遇。過去五年來我都是這樣過的。終年漂泊不定,這樣的生活占據十二個月中的九個月、十個月到十一個月。每個月大概只有三、四個晚上睡在自己的床上──其餘都是在飛機、汽車、火車、雪橇、遊艇、直昇機、飯店、印地安長屋、帳棚、木屋,還有叢林的地上度過的。我變成了某種旅行業務員或是領薪水的流浪漢,既被祝福又被詛咒地繞著地球跑,直到走不動為止。當一個人的夢想成真,那情況還真是啼笑皆非。
我的食評家老友吉爾(A. A. Gill)曾說過,當他年紀越長,到過越多地方,則所知越少。如今我能體會他的意思了。用我的方式來看這個世界,它會不斷告知還有哪些你不知道的地方──有多少必須去看、去學習的事物,以及這個世界有多他媽的大而神秘。這樣的認知既讓人感到挫折,又讓人著迷。並且這只會讓你在第一次到像中國那樣的地方旅遊時,更感到困難。你會覺得那裡有太多東西要看──而你能遍覽的時間是那麼少。這在我本已荒謬的人生裡又添上一項狂躁的性格,以及兼具絕望和順從的個性特質。
旅遊使你產生變化。在經歷人生、遊歷世界時,會逐漸改變許多事,不管有多細微。你或許沒有發現這些變化。然而,相對的,人生──以及旅行──將改變留在你身上。大多時候,無論在你身上或在你心中,這些改變都是美好的。然而也經常是痛苦的。當我回顧從我寫了那本討人厭、精力過剩的回憶錄以來的五年時光(那本回憶錄將我帶出廚房,進入一個壓力艙和機場貴賓室的無盡隧道),那些一閃而逝的片段,都蜂擁而上想引起我的注意。有的好,有的壞,有些愉快──有些則苦不堪言。不過,我想大多數都如同這本選集裡的文章。
在過去幾年裡,我為報章雜誌寫了許多文章,而接下來的文章是其中比較可口的(我希望是)。有許多文章已無可救藥地過時,或者很明顯是寫給英國或澳洲媒體的,我已在書末附上說明(或道歉啟事)指出了。我寫這些東西跟我的旅遊狂熱有著相同原因:因為我做得到。因為時間總是不夠用。因為世界上有太多必須去看去記錄的地方。因為我總是覺得下本書或下個節目會石沉大海,因此最好趁我還能賺錢的時候,賺些他媽的錢。
很多地方和事件難以描述,這點是挺煩人的。好比說吳哥窟和馬丘比丘都選擇了沉默,像是你無法談論的一段感情。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你搜索枯腸,試圖用適當的語言去組織一段文字,一個解釋,一個恰當的方式來構築起你曾經到過的地方和發生的事情。到最後,你只是很高興自己曾經到過那裡──大開眼界──而且可以活著看到一切。


 共
共  王丹,原籍山東省鄄城縣,生於北京,北京天安門八九民主運動領袖之一,與吾爾開希、柴玲等同為學生領袖,曾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也是一位詩人。八九學運前曾組織過悼念病逝的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撰文支持民主等活動,六四清場後拒絕逃亡,多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逮捕入獄、1998年後流亡至美國,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常居台灣、美國等地,並為國立成功大學客座專家,參與該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2010年9月起,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2015年8月起,受聘於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為期2年。2017年7月離開台灣,返回美國。
王丹,原籍山東省鄄城縣,生於北京,北京天安門八九民主運動領袖之一,與吾爾開希、柴玲等同為學生領袖,曾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也是一位詩人。八九學運前曾組織過悼念病逝的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撰文支持民主等活動,六四清場後拒絕逃亡,多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逮捕入獄、1998年後流亡至美國,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常居台灣、美國等地,並為國立成功大學客座專家,參與該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2010年9月起,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2015年8月起,受聘於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為期2年。2017年7月離開台灣,返回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