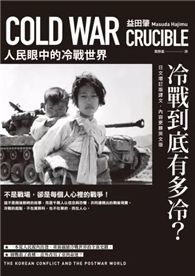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珍妮‧德‧喬凡尼的圖書 |
 |
$ 121 ~ 264 | 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 :我走過敘利亞內戰,看見自由的代價
作者:珍妮‧德‧喬凡尼 / 譯者:溫澤元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07-26 語言:繁體/中文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本書作者喬凡尼(Janine di Giovanni)是一名戰地記者,曾經歷世界最危險的國家,包括波士尼亞、獅子山共和國與敘利亞。她抵達敘利亞時,該國還是一片和平景象,但不久開始砲聲隆隆,革命聲勢沸騰不已。最後,敘利亞內戰演變成一場恐怖殘暴,彷彿永不止息的戰事。
喬凡尼見到敘利亞難民四散,村莊被燒毀;軍人在街上大搖大擺地走著,女人帶著恐懼神情逃離家園,深怕被凌辱強暴。她經歷盧安達、索馬利亞、賴比瑞亞、獅子山共和國,還有車臣共和國殘暴的戰爭,然而現在她再度進入無情烽火。
本書記述作者在敘利亞的戰火經歷。在戰爭中,她看到很多非常英勇的人,他們之中有人是為民主自由而戰,為我們每天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而戰;她也見到幸與不幸的人,看到的不只是死亡,還有失望與恐懼,即使她努力救援,但面對殘酷戰爭時,她僅能是一位目擊者。
離台灣很遠的敘利亞,我們或許毫無感覺,但對喬凡尼來說,她的工作就是為無辜的人民做見證,記錄歷史的真相,成為那些亡者的代言人。她宛如照亮黑暗角落的一道光。
作者簡介
珍妮‧德‧喬凡尼(Janine di Giovanni)
美國愛荷華作家創作坊、塔夫茲大學佛萊契爾外交法律研究院畢業,擔任《新聞週刊》中東地區編輯、《浮華世界》雜誌特約編輯、戰地記者,曾經歷世界最危險的國家,包括波士尼亞、獅子山共和國與敘利亞。因記述軍事衝突裡的人性故事,獲頒美國國家雜誌獎、國際特赦組織新聞報導獎,她的作品被著名作家梭羅(Paul Theroux)讚譽為美國最佳旅行書寫,現居住在法國。
譯者簡介
溫澤元
畢業於政治大學,現就讀師大翻譯研究所,熱愛電影與翻譯。譯有《砲彈下的渴望》,合譯《我在紐約當農夫》、《遠離塵囂》、《機艙機密》等。譯稿賜教:lars801011@gmail.com
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