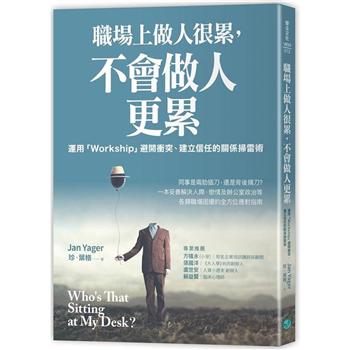偽裝
我的存在建築在我的記憶之上,然而我記憶中的人生,很可能根本不是我的真實人生……
精神分析師阿默農有項特殊能力──能藉由肢體碰觸探知對方的記憶,即使是連對方都早已徹底遺忘的記憶。這使他的心理治療備受好評。他意外認識小提琴工匠明斯基,並為他心中關於集中營記憶感到震撼,遂鼓勵明斯基書寫過往,且成暢銷之作。但未料竟引發媒體爭議,明斯基堅持其記憶為真,而讀取明斯基記憶的阿默農,亦遭貶為騙徒同夥,楊‧威赫斯勒更著書證明兩人偽造與欺世盜名。他們只好隱姓埋名避居世外。怎料,數年後,楊‧威赫斯勒尋跡而來,他究竟還想從他們這裡奪走什麼?
遺失
對於過去,我依然只能看見斷片殘影,也許我是殺人兇手,但我卻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
作家楊‧威赫斯勒某天收到一只標示他名字的手提箱,裡面有文件、書稿與一本書《偽裝》。他以為這屬於與他同名同姓的陌生人,為了物歸原主,他開始尋著手提箱中的線索,尋找另一個楊‧威赫斯勒。怎奈與他接觸的人,都認定他就是他要尋找的對象。他急於證明自己,卻接連發現不存在自己記憶中的昔日往事,甚至認為絕不是自己做過的事──揭發明斯基之書為偽作。他需要明斯基與阿默農證明他並非那個楊‧威赫斯勒,於是啟程前往以色列。只是,當他飛抵阿默農隱居處之時,等待他的竟是監獄牢房……
本書特色
★ 這一本書沒有封底,不論從正面、從反面開始翻閱,都是故事的入口。當兩位主角相遇之時,就是衝突之始。
★ 情節緊湊、扣人心弦,關於我們的記憶是如何不可信賴,以及自我認同的問題。
★ 「明斯基」的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講的是發生在班雅明‧威爾高米司基(Benjamin Wilmorski)身上的事件。威爾高米司基於一九九五年在德國出版《碎片》一書,以集中營倖存者的身分書寫回憶,結果被揭穿為騙局。但威爾高米司基堅持,對他而言他的回憶是千真萬確。
媒體讚譽
一本特別的、動人並能流傳於世的新書……瀰漫奇特的氛圍與魔力。──《南德日報》
《心靈映寫師》是本關於記憶的祝福與詛咒的小說:讓人得以認清自我的記憶,同時也是傷痛的記憶,如果此記憶一直揮之不去的話。──《新蘇黎士報》
它是世界性的,它靠智慧與幽默維生,它反射出對自我的不理解,它也能助人對宗教文化的世俗創作有些許了解,而且幾乎處處可見精神分析師一角的存在。──德國《時代》雜誌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