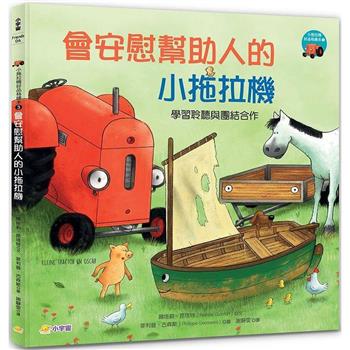在生命的天空裡展翅翱翔
何大一 / 何弘一 / 何純一
這本傳記記載了一個平常人度過的極不平凡的一生。這本傳記成書問世以前,除了家人,很少人詳知他的生命歷程。也就因為如此,以他為傳主的本書更有其特殊性。傳主雖不是聞名的大人物,連他的體型都是矮矮小小的,然而他的精神和毅力至高至大,悠長的一生充滿了悲辛和歡笑。他咬著牙挺過了無數艱難困苦,也做出各種自我犧牲,但最後終於從他一手建立的家庭得到了安慰和快樂。這位傳主就是我們的慈父何步基先生,本傳記就是父親從一九一九年到二○○九年在人間跋涉奮鬥的故實。
父親最堅毅的精神就是能歷經萬難而屹立不倒。他在童年期,由於生母是姨太太,飽受歧視。青年時代為了抗日,幾乎徒步千里到大後方求學。到了抗戰勝利,由於國共內戰,他離開了在江西的妻兒,獨自去到台灣,經受了許多他鄉漂泊的苦楚(二十八年後才與江西家人重見)。後來他又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深造求學,和他在台灣建立的第二個家分別了八年之久。幾年後他又眼看自己苦心創造的電子中文打字機被竊盜。然而這種種苦難和挫折一點沒讓他灰心氣餒,他不怨不恨,仍然保持他對人世的理想和希望以及對人的誠意和信任。
父親苦盡甘來的日子,始於他將母親(何江雙如女士)和我們從台灣接來美國重聚。後來,中國開放,與美國復交,父親回江西探望他年邁的母親(我們的奶奶)和三個兒女(也就是我們的哥哥姐姐們)。父親雖深知家人多年受盡不可言喻的痛苦,但他對中國並無一絲怨恨。相反地,父親對中國的開放、發展與崛起感到驕傲。父親看到自己發明出來但被人竊盜的中文電子打字機問世,還是覺得很興奮。在本傳記開始撰寫時,父親更是興高采烈,積極與撰寫人合作,提供所有記憶所及的事蹟和各種所需資料,熱情地和我們一起重溫點點滴滴的往事舊夢。
父親和我們家人(他的子孫們)歡聚一堂,他無時不是慈祥歡喜,笑逐顏開。他對我們兄弟們的建樹和成就都十分欣慰,深知我們今天走的這條安穩路,完全是他和母親二人篳路藍縷親手修築起來的。我們更深深體悟到,他和母親給予我們的這份禮物珍貴無比。沒有父親和母親在這片凶波險浪的大海上掌穩了舵,我們怎能抵達現在這光明美麗的海岸?沒有他們兩位老人家辛苦種植,我們今天又怎能在這平和寧靜的綠蔭下憩息?父親到了晚年常歎道:「我真幸運啊,真幸運!」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們做為他的子孫才是真正的幸運啊!
中國有兩句古詩最能做為父親一生的寫照:「人生在世應何似,當如飛鴻留雪泥。」父親就是那在生命天空裡展翅翱翔的鴻雁,活了有目的、有意義的一世。他老人家雖已走了,然而在人間,在我們的心田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本傳記是他勇敢奮鬥的紀錄,藉以感念他贈予我們芬芳長存的精神遺產!
序幕
溯記憶之河而上
二○○七年,何步基老先生帶著作者等一行人,第一站來到重慶。此地有許多天險:山聚千峰,江分二水(長江和嘉陵江),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到了二十世紀中期抗日戰爭時,又扮演了軍事和政治上極重要的角色。我們之所前來,是因為這個城市與本書傳主何步基的一生有關,因而從重慶開始回顧。
抗日戰爭中,步基在重慶住了一年半,那時他還是個年輕小伙子。二○○七年是他戰後多年首次回到此地;與我們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雙如女士,以及他們三個兒子中的老二何弘一、老三何純一;他們的長子何大一要幾天後才與我們會合。
步基在美國的家,可說是美國華裔追求新生活的典範家庭。他們克服了身為移民的重重困難,兒子各自都有所成就;大一更是舉世聞名的愛滋病研究專家,做父親的步基終於苦盡甘來。不過這一切都得來非易。要說步基的悲欣路,必須回溯他與中國和台灣的根源;他的故事有其一定的歷史重要性。
步基的一生與大時代的動盪關係密切。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使他嘗盡顛沛流離之苦、悲歡離合之情。後來獨自來到台灣,與美麗賢淑的江雙如女士成婚,兩人婚姻美滿,子孫滿堂,但期間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步基經歷了許多辛苦,以致於年輕時不能發揮自己的潛力,無法如願成為學者;在他的生命中,也曾發生許多悲劇,但這一切他都承受下來了。他憑著自己的毅力和奮鬥精神,在無望中找到希望,在黑暗裡見到光明。經歷這一切後,他仍屹立不搖,並親自敘述他這不凡的一生,值得慶幸。
◆少小離家老大回
我們在二○○七年三月前往重慶,目的是尋找步基當年的住處和工作所在。這不是件容易的事,畢竟事隔多年,步基記不清楚那些地方的確實位置,我們只有邊走邊找,同時不斷詢問當地人。
步基起先能提供的線索相當有限,但八十八高齡的他精力飽滿,身體健康,且極有幽默感;他時而笑逐顏開,時而邊說邊笑,很少分心,帶領大家鍥而不捨地尋找他往日在那兒留下的雪泥鴻爪。然而,重回重慶對步基而言,不只是一趟追溯記憶的旅程,更需面對回憶的消逝。
我們抵達重慶時已是傍晚,天下著雨,從機場到金源飯店的路上看到的是燈火輝煌,但第二天白天時的重慶給我們的感覺就不同了,全市籠罩在煙霧與空氣污染之中,市區裡的房子都是同一樣式的灰濛濛老建築,和新式的飯店大不相同,還有許多修建一半就停工、生鏽的鋼筋水泥房屋。
這時春節剛過不久,四處還留著很多紅燈籠、彩色的迎豬年春聯,為周遭灰色的建築平添一些顏色。市區裡嘈雜喧嘩,車輛擁擠、阻塞,喇叭聲此起彼落,鬧成一片。至於人們,百業雜陳,跑的跑,走的走,吃東西的吃東西,擦鞋的擦鞋,挖耳朵的挖耳朵,打麻將的打麻將,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融會。到處都聽到音樂歌聲,解放軍革命歌曲和美國流行歌曲混成大雜燴,震耳欲聾。
我們租了一輛美國別克汽車去尋找步基的舊時行跡,但在重慶市區四處兜了半天,什麼也沒找到。離開市區之前,我們去了市中心的解放紀念碑,憑弔在抗日戰爭因日本飛機轟炸而喪生的許多無辜老百姓。在紀念碑一旁,我們看了陳列的黑白照片,內容都是當年遇害民眾罹難的各種慘況。步基運氣好,得以倖免,此時他帶著嚴肅的心情,來到這裡追思苦難的同胞。
看完紀念碑,我們上車繼續前進,來到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處。這裡的景色在煙霧細雨中有種特別迷濛的美,很像中國國畫裡的山水。重慶這種陰沈沈的天氣,在抗日戰爭中為日本空軍增加了許多難度;而我們這種大海撈針的找法,也很難找到步基往日的舊行跡。為我們開車的司機先生十分機靈,聽了步基的一些描述,把車開到江北,朝重慶最高處前進,來到市裡最貧苦的一區。
這裡的房屋建築十分簡陋,沒有一間是完整的;街道狹窄,藍白交錯的布篷下有些小市集,但商品不多,稀稀疏疏地擺著。車子繼續往上開,步基看起來愈來愈興奮,隨後要求司機停下車來。
這時雨又開始下了,我們下了車,走到一間磚砌的房子前。這就是步基當年住的地方嗎?不是。步基望著河水的方向,指著另一個較高的地方。於是我們繼續往上行,沿路有不少卡車、關閉的工廠、無窗的水泥小屋,以及一群群野狗。
除了步基外,沒有人知道我們要去哪裡。車子抵達山上後停了下來,我們都下了車,眼前的山下即是嘉陵江。看著兩旁破舊無人居住的建築,步基忽然記起六十多年前的事,大聲說:「就是這裡!我當時常在這裡看山下河中的小島,再過去就是市區!」那麼,兩旁建築其中的某一棟就是他當時的住處嗎?「不是,那時我住的地方不在了。」
眾人聽了之後,靜靜站在原地,不禁有點惘然。此地現在是個垃圾場,弘一看到垃圾堆裡有支用完丟棄的高露潔牙膏,問父親步基:「那時您常下山去城裡嗎?」步基說他很少有機會去城裡,有時會搭美軍的吉普車去一趟。不過去城裡沒什麼意思,因為大半都被炸塌了,四處都是難民,又缺水,吃的東西也匱乏。
前往重慶之前,步基已告訴過大家,要找到當時他的舊行跡恐怕很困難。「當時的熟人朋友,一九四五年仗打完都走了,沒認識的人了。」他說。不過總算不虛此行,多虧司機先生的配合,竟能找到他以前的住處。步基在這破瓦殘垣旁拍了一張照片,為他的過去留下一點紀念。這也是這趟為期六星期的中國之行所拍的第一張照片。
第二天,我們啟程前往距離重慶三百多公里的遵義,雙如因疲憊沒有同行,留下來陪她的是純一。遵義位於中國最窮苦的省分之一──貴州,當地出產有名的茅台酒。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間中國共產黨有名的「長征」路上,毛澤東在遵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遵義對本傳記也有其重要性,由於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浙江大學遷校到遵義,步基就是在這裡上大學的;這是他開始大學生活的地方。
過去從重慶到遵義開車需要兩天的時間,現在建了四線高速公路,方便多了,只要三個多小時,也取代了著名的滇緬公路。滇緬公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中美合作開通,是美援進入中國的主要途徑,由於山路崎嶇,當時開發非常艱苦,人力和物力都消耗很大。不過現在有火車通連重慶和貴陽,公路用處不大了,所以車輛稀少,兩旁都很荒涼。
在三個半小時的旅程上,我們看見清潔公路的工人大多是女工,還看見一個頂多四歲的男孩,大步在公路旁走著。這裡已遠離市區,周圍的地形都是梯形,房子就蓋在梯邊上,偶爾可看到衛星電視的天線、墳場上林立的白色墓碑,更特別的是很多房子的屋頂上都點綴著黑白的大足球。快到遵義時,山谷下有許多菜田,種滿了金色的花菜,還有許多梅花園。這時,公路上的車輛也多了些。
出乎意料的,遵義完全不是想像中毫無生氣的地方。這裡的人們穿著整齊,個個都興致勃勃地過著日子。城裡有河水穿流其間,河旁的公園裡有游泳池,樹木茂盛,四處可見怒放的花朵。可惜遵義計畫將最有意思的老房子拆除,改建新房子。步基端詳著這個小城說:「都變了,都變了!」
到了城中心,步基看見一座古老的橋橫跨於鴨西河的一條支流上,上游還有間殘破的廟宇。這一切觸動了步基的記憶,不過他還不能確定,詢問了兩位路人,但他們都不知道有關遵義過去的事。最後,步基遇到一位八十四歲的老人,是久住遵義的居民。他說,是的,這兒在抗日戰爭時曾是浙江大學的一部分。他們正說著,走過來一位老太太(後來她說自己八十七歲,看來真不像有那麼大歲數),她絲毫不在意步基懷疑的口氣,堅定地說,這兒就是當年浙江大學的校址。於是步基終於相信了,興奮得不得了。「簡直是驚喜不已。」弘一後來憶道。
這時周遭的人們都猜到了我們應是從國外來的,圍過來的人愈來愈多,有的瞪著我們看,有的要賣芝麻糕給我們,有的叫我們到旁邊一家店裡去量量身高和體重,還有要飯的過來要錢。
步基這時對身旁的一切都不在意了,精神振奮地告訴我們幾十年前在此地的往事:就是這裡!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就是當年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在河對面剛才停車的地方。「沒錯!」步基笑道:「我經常過橋去看那些女生呢!」我扶步基到橋邊石凳上坐下,大家紛紛為他照相。步基看起來精神抖擻,那是那幾天最快樂的一刻。有了這個收穫,我們也開心,於是吃了芝麻糕,量了體重身高,給了要飯的幾塊錢,然後就打道回重慶,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在重慶等著我們的雙如和純一。
◆重逢
第二天我們一行從重慶飛往江西的南昌,步基的精神還是十分好,弘一和純一也都很高興,因為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南昌等著和他們會合。長子大一和妻子素玉及兒子將仁原本也計畫在南昌和我們會合,但他們從紐約出發時,飛機因大風雪停飛,無法按時抵達。
我們搭乘的是晚上的飛機,所以無法欣賞沿途的山水風景。到了南昌,江西海外華僑聯誼會、江西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都派了代表來歡迎我們。這不僅因為久別江西的遊子步基回鄉,主要也是因為何大一的聲譽;這時全江西省都知道大一是發明「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科學家,名聞遐邇。
到南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探尋步基在故鄉江西的回憶。政府安排了一輛小型巴士和一位翻譯員。第一站就到了南昌二中,應該就是步基在一九三○年代曾就讀的母校。儘管我們在此得到了一些問題的答案,同時也發現了許多問題,畢竟過去七十多年來經歷了這麼多的動盪。
我們發現,步基曾就讀的南昌二中,早在抗日戰爭中炸毀了大部分,學校所有的舊檔案也都不在了,以前的校舍如今已是一個電子工廠。當年二中舊校址不是現在二中的所在,而是位於優美的東湖旁邊,但在日軍逼近南昌時,遷校到南昌南邊三百二十公里處的石灰橋。然而,我們去的是如今的二中,位於南昌郊外,有三千名學生。這兒既不是以前的二中,又沒有寫傳記所需要的資料,該如何喚起步基的回憶?
我們抵達學校後,發現大樓上掛著「熱烈歡迎何大一蒞校訪問」的大紅旗,校長吳勤帶著歡迎團上前迎接,眾人寒暄一回,來到樓上一個大教室改成的臨時禮堂,學生的書桌圍成貴賓座,桌上放著各式鮮花水果,因天氣寒冷,也準備了熱茶。我們在此坐下,聽校方請來的人士敘述一九三○年代有關學校的史實。
吳校長首先致辭,為我們介紹二中的校訓「勤樸肅毅」,出自論語。她也把二中校史和今日情況做了簡介,最後讚許步基是二中最優秀傑出的校友,也是第一個從海外重回母校的學生。
步基的臉上一直帶著笑容。這時候,這裡究竟是不是他當初就讀的地方,此時學校裡的工作人員也已不是當年的師長,而所有人等待的大一也尚未抵達……這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
他愉快地上台致答詞,感謝母校的熱烈歡迎,然後與在場的幾位年長校友一同回憶當年的情況,重溫許多在校時溫馨、可愛的時光,也細數了那些飽受戰亂之苦的日子。他們所說的內容不太一致,有些矛盾或不連貫的地方,但都相當有趣,而且也在我心中引起了許多問題。例如:這麼大的學校是如何遷到石灰橋的?日軍幾乎切斷了所有交通方式,步基又是怎麼到石灰橋的?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隨校撤退了?他的同學是否在想,如果他在一九四七年沒去台灣,命運會如何?當會議結束走出二中時,這些念頭還在我的腦海裡迴盪。
我們走下學校大門前的石階,一輛黑色大型禮車開了過來,車上下來的是大一、素玉和將仁。大家見到他們都非常欣喜,連忙和他握手、問好,學校的幹部更是高興,因為他們就等著見到這位鼎鼎大名的科學家。這時大家又忙著照相,照片裡,步基和雙如坐在正中間,兩旁簇擁著家人和二中的校長、其他領導,以及其他和步基一樣的長者,無論他們當年曾經歷了什麼,都從未放棄學習。
我們一行人終算到齊了,而且在接下來的八天裡,由於大一的聲譽而受到熱情且盛大的歡迎,當地所有單位人員都說會儘量協助我進行這本傳記的研究工作,為步基的一生留下紀錄。我們所到之處都有人向大一表示敬仰,連鄉村的土牆上,都用大字寫著他的名字。
隨後我們訪問了新余的大一中學,當然,大一也為全校師生致了詞。他用英語演講,對中學生是個考驗,但他們竟都能聽懂,在演講告一段落後,也提了不少問題:「您是哪年結婚的?」回答很簡單:一九七六年。「您自己覺得您在科學方面最大的貢獻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好像很容易猜到,卻有點出人意外:「你們可能認為答案一定是發明『愛滋病雞尾酒療法』,但不是的,答案是:在所有其他科學家之前先發現了愛滋病病毒如何危害人體。」大一說。又有學生問他覺得事業上什麼是讓他最感到滿足的。大一答道:「不是領獎或拿到各種榮譽,而是一個陌生人對我說『您救了我的命』的那一刻。」又有一位女士問道:「您覺得要成為成功的科學家,必須具備什麼條件?」大一不假思索地答道:「決心和毅力。」最後一個問題坦誠、直接、又幽默,是校長提出來的:「您的大名就是我們學校的校名,您又是我們的名譽校長,但您怎麼這麼難得才來看我們一次呢?」
接著我們訪問南昌大學,大一應大學之邀,接受了醫學院榮譽院長的職銜,在大學舉行了隆重的受譽典禮。後來我們前往杭州,大一在那兒也應邀前往浙江大學為醫學院學生做了一場演講。浙江大學就是以前步基的母校。由於步基和大一的盛名,我們在各地都受到高級幹部(省長、副省長、黨委書記和市長等)的熱烈招待,受邀參加了無數豪華的宴席。
宴席上,賓主彼此讚揚對方的成就,同時也互送禮物,中國方面送了我們上好的瓷盤、手製的瓷花瓶、精緻的珍珠項練,以及裝訂精美的書籍和絹畫等,大一則回贈製作雅麗的上等玻璃蘋果(代表紐約)或其他紀念品。隨後晚宴正式開始,菜餚極為豐富,彼此相互敬酒,賓主盡歡。
離開南昌前,我們應邀遊覽贛江旁著名的滕王閣,這是詩人王勃寫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名句的所在。此外,我們也參觀了絕世畫家八大山人的紀念館,該館位於湖中一恬靜小島上,我們在此欣賞了他的許多不朽作品。
步基的家鄉新余就在江西省,離南昌不到二百公里,不過兩個城市有很大不同。南昌是江西省會,是個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的大城市,相當富足;但當車子一出南昌,離開農作物生長茂盛的贛江平原,開進山區並逐漸接近新余時,就會發現新余是個典型的省城,有火車和現代化的高速公路與其他城市相連,不過四周的農村都相當貧窮。
我們的座車來到新余,在城中心北湖賓館前邊停下,外事辦公室劉主任帶著幾位下屬幹部正等著歡迎我們,旁邊還有幾位穿著普通的人,是步基的家人。
步基的老家在松林,在新余北邊十多公里的山腳下,老家的村子叫何家村,居民都姓何。這天有許多步基直系親屬和遠親都騎車來到新余迎接我們。人群裡有三個人走上前來迎接步基和雙如,他們是步基還在中學時就因媒灼之言結婚生育的三個孩子:大女兒鴻蓮已經六十九歲了,大兒子棠祥,六十八,小女兒香保,六十五。他們一一熱烈拉住父親問好,然後又熱情地向雙如問安。
當時我因眼前的景象而震驚,原因是步基第一次婚姻生育的三個孩子,和他與雙如生育的三個孩子太不相像,簡直有天壤之別。他們彼此之間的不同,不只在於年齡,當時大一也已五十五歲,弘一五十三,純一四十;也不只是皮膚的粗細程度或牙齒保養的差異,更不在於衣著的不同。也許所有這些方面都有極大的差別,但立刻讓人明顯感覺到的,是步基這三位留在中國的兒女,由於經歷了太多的人世滄桑,才會看起來和三位同父異母弟弟這麼不同。
步基留在江西的這三個孩子,因為有地主背景,文革結束前都被政府視為「出身不好」,在一九五○年代土改時就被掃地出門,失去了家。到了文革時期,更是飽經折磨,嘗盡赤貧之苦。在我們來江西之前,弘一就曾告訴過我,這些年的痛苦,在棠祥的臉上深深烙下了無法磨滅的疤痕。當時因為他們的爺爺是地主,爸爸又在美國,鴻蓮、棠祥和香保三個孩子被判定不准接受正常的教育,結果鴻蓮一共只上了五年學,棠祥和香保二人只讀了三年書。
◆母親啊,母親!
我們在新余時,住在官員安排的招待所裡,不管在哪兒、去哪兒,都有負責歡迎和招待的幹部陪同,他們同時也為我們安排每天的節目;吃的喝的當然豐富,另外還有一輛小型巴士與司機一位供我們使用,車上裝有警車的喇叭,無論是紅燈綠燈都通行無阻。
其實我們去松林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去何家村給步基的祖宗先人上墳。因此,一到新余,受當地黨委書記邀請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後,棠祥、鴻蓮和香保就和我們一起上車,直奔何家村。
在路上,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知道如今的何家村經過這麼多年的動盪和風雨,村子一定殘破不堪;加上村子裡的人大半跑到沿海大城市謀生,當然不可能和步基小時候的何家村一樣,因而只能想像在這所有破壞之前的何家村的模樣。
步基小時候,從何家村到新余要走整整半天的路,現在搭車只要十五分鐘。到了村口,看見幾棟水泥蓋的兩層樓新房子,車子開進村裡,只見老房屋都陳舊殘破,連整修都不可能了。不過村子裡還是有很多人,我們的車開到村中心的小廣場上停下,一旁是個水潭,另一邊是一棟大磚房,一大堆人在那兒等著我們。下車後,有幾位穿白襯衫戴紅帽的孩子,約莫十二歲左右,吹著喇叭,敲鑼打鼓,表示歡迎,另一邊何氏宗祠的門口石階上擠著四、五十個人,爭先恐後搶著看我們。一旁還有人放鞭炮,喧嘩震耳。這所有熱烈的盛情,都說明了何家村的人是多麼因為有步基和大一這樣的親戚而感到驕傲。步基離開故鄉那麼久,終於衣錦還鄉了。
這時步基也很愉快地和周圍的鄉親打招呼,他從人群裡請出一位婦女為我介紹:「這是我的弟媳,謝氏。」我與她握了手。步基又指著旁邊的磚房說:「這是我們何家的宗祠。」他帶著大家走進宗祠,由於年久失修,裡面除了一個大桶和一些春節留下的紅紙旗,什麼都沒有。「以前這兒是全村最美的建築。」步基說。
走出宗祠,我們沿著一條狹窄的巷弄穿過村子,學生演奏的音樂依稀可聞,鞭炮餘味仍繚繞四周,這時來到步基母親度過生前最後幾年時光的簡樸屋子。短暫停留後,我們動身前往拜謁她的墓地。
眾人坐車來到村外不遠的山下,這是當地的燕山,步基母親的遺言就是要葬在此地。這時,除了雙如和兩個孫女還留在車上,所有人都朝著陡峭的山上走,陪同的幹部也各自回去了。下午的天氣暖和,我們將衣物留在車上,有機會下車舒散舒散,都很高興。
文革期間,毛主席下令,人死後不准土葬,只能火葬。步基母親傅氏一九八二年去世時,文革已結束六年,這個規定也已取消,因此步基他們為她置了一具壽棺,並依照她的遺願,將她安葬在雞坑山麓。沿著山路往上走,兩邊都是盛開燦爛的紅色杜鵑花。有人在我們去之前將山路上的樹木草叢加以清理過了,但上山還是相當不容易。我們在路上看到了一旁的老禁山,是步基父親文閣的埋葬處。「山區還是如舊,沒有什麼改變。」步基說。再往上爬,眼前忽然出現一塊石板,走近才認出是墓碑,接著又看見旁邊還有另外三塊,而第一塊就是步基母親傅氏的墓地。
傅氏在世時,對步基他們說過,她去世後不要把她和丈夫文閣或何家村其他村民葬在一起,並且自己挑了這塊山地做為安葬之處。村裡的人知道了,都說傅氏挑了這個葬地,若不是會為子孫帶來幸福,就是會為他們帶來晦氣。傅氏一九八三年下葬後,步基、雙如和大一他們全家喜事重重,聲譽蒸蒸日上,何家村村民於是認定了傅氏挑的是吉祥的一塊墳地,這才有人也決定死後要葬在此地。
傅氏是第一個挑選此地安葬的人,她的墳地特別優美,可以遠眺家園。在她的墓碑後面有個饅頭型的高土堆,「土壤可以讓她的靈魂覺得溫暖。」步基說。他的兩個侄兒挖了些土塊,添在土堆上。這時棠祥將帶來的竹籃放在奶奶墳前,籃子裡放著煮好的雞蛋和紅燒肉,供奶奶的靈魂享用。食物放定後,棠祥點了幾柱香,在土堆中間放了幾柱,在墓碑的兩邊也各放了幾柱。
這時,步基帶著他的四個兒子──棠祥、大一、弘一和純一,後面是女兒、媳婦和女婿及孫輩,他們依序走向傅氏墳前,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禮。禮畢,大家拍了照片留念,照片上是傅氏墳前的祭品、墳上的香,還有香保在山路上摘的一枝杜鵑花,也在墳上放著,供奶奶的靈魂欣賞。
一切結束後,我們準備下山,步基的一個侄兒開始點放鞭炮,據說奶奶墳地如有惡鬼,喧天的鞭炮聲可以將牠們嚇跑。下山時,仍可聽見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回頭只見一縷縷青煙裊裊繚繞在墳地上。
拜謁步基母親傅氏的墓地,對步基和他們全家都是重要的一刻。步基告訴我,他在墳前對母親之靈說,他們三代人都來給她行禮了;他告訴母親,他們的日子過得都還可以,孩子們學習努力,都是優秀學生。他還對母親說,她是個最好的賢妻良母,魂靈一定已經在天堂了。對大一的兒子將仁來說,這次拜謁曾祖母的墓地,讓他「心神震撼」;見到許多以前都不認識的伯伯和姑姑,也使他十分驚喜。
這次拜謁母靈,也是棠祥、鴻蓮和香保第一次正式與步基美國全家人一起完成的家庭大事;在這之前,所有幹部邀請步基的宴席活動,都不包括棠祥他們三人。上墳時,一切禮節按照中國文化傳統,棠祥是第一個跟著父親步基向奶奶行禮的孫子,這證實了他是步基長子的身分和地位。弟弟弘一後來說道:「真是太好了,棠祥是父親的大兒子,是大哥,就該在前頭帶著我們。」
中國之行不但在步基的腦海裡勾起了許多往事,也讓我決定把步基的故事及中國二十世紀的背景寫下來。這豐富、緊湊又發人深思的三週中國行,燃亮了步基腦海裡的記憶之燈,也讓我心裡產生了更多令人想一探究竟的問題。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