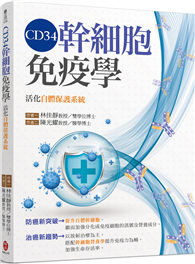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
第一節 《形上學》談什麼?「存有是什麼?」的問題
本書所談及題目為《形上學》(Metaphysics)的著作,乃全部或大部分由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撰寫的一套十四卷文集,是他生命最晚期的作品。《形上學》是亞里斯多德在雅典創辦了他自己的哲學學校呂克昂(Lyceum)學園或稱逍遙學園(Peripatos)之後(335 BC)才寫的;也就是說,即使《形上學》是亞里斯多德花費很長的時間才寫成的,也應該是在他離開了柏拉圖(Plato, 427-347BC),並且在雅典的學園待了好幾年之後才創作的。因為他在十七歲時成為柏拉圖的弟子,起先只是門生,不久就成為一位相對獨立的研究者,前後共約二十年。不過,柏拉圖去世之後他就離開學園了。
然而,亞里斯多德並非作為單一著作來撰寫《形上學》的,甚至其中的單獨書卷(或整部文集)可能都不是已完成的作品。直到他死後,大概在西元前二百至前一百年之間,這套十四卷書才被整理出版,一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次序。其書名《形上學》並非亞里斯多德自己命名的,而很可能是羅德島的安德羅尼柯(Andronicus of Rhodes)在編輯亞氏作品全集時(西元前一世紀)想出來的。他想出這個書名(原名 ta meta ta physika,《物理學後諸篇》),可能是因為以他的觀點來看,《形上學》很自然地應列在亞里斯多德另一著作《物理學》的後頭。
我們可以猜想,安德羅尼柯之所以認為這是《形上學》理所當然的位置,是因為他認為一切事物的研究,以及事物單純在它們乃存有物之範圍內的研究,亦即亞里斯多德所賦予形上學的特徵,很自然地應在我們直接從感官知覺和經驗中所熟悉的、變化的有形事物的研究之後,亦即亞里斯多德所賦予物理學的特徵之後。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十四卷書如果有任何共同之處使它們得以輯集成為單一作品,就在於《形上學》乃整個研究的核心。這是對一切事物及事物單純在它們乃存有物的範圍內──事物的所是──之研究。所以,書名《形上學》或許可以指出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與什麼有關,只是其說明方式顯得有些迂迴而不那麼直接清晰罷了。我們當然已經習慣於認為《形上學》顯然是有關形上學的,這樣想準不會錯。不過,亞里斯多德並沒有使用「形上學」這個詞,而且當他想要表示自己當下的研究與什麼有關時,他習慣用的是諸如「智慧」(sophia),「第一哲學」(prt philosophia)和「第一科學」(prt epistm)這樣的詞語。
再者,《形上學》乃是關於某一事物的,而且有著單一主題,也就是「存有是什麼?」(t?to on;to on 意謂「哪一個是」,「存有」)的問題。《形上學》就兩種意義而言,乃關於「存有是什麼?」的問題。一方面,亞里斯多德提出這個問題,並長久致力於為之尋求一個答案,而且他顯然提供了答案。另一方面,他也詳加考慮所提出的和所為之尋求答案的問題本身是什麼,甚至究竟是否有可能尋求到一個答案。我們不妨說,他也考慮了形上學何以有可能。所以,讓我們一開始就專注於《形上學》中的主要問題「存有是什麼?」吧。
首先,「存有是什麼?」的問題乃關於存有(being),而非關於名詞「生存」(being)或動詞「成為」(to be,或生成)。它是關於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的問題,而非關於使我們去想和說及某物的所是為何的問題。當然,當我們想和說及某物之所是時,我們怎麼思考和談論,在我們問「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這些問題時,就種種方面而言可能很重要。不過,這個問題仍然不是關於當我們想或說及所是的某物時,我們怎麼思考和談論的問題;而是關於存有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是關於什麼的呢?我們問「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所問的是什麼?亞里斯多德顯然認為我們正在問事物所是的存有物(onta)的這個問題;亦即我們正在問使某物所是的一個存有物成為該事物的是什麼。然而,他也假定在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已經熟悉存有物了;而且它是如此眾所周知的事物,因此他認為我們也許想要問這個問題。所以,他認為我們乃前哲學地從尋常經驗中熟悉了存有物;因為存有物是直接地顯現給我們、出現在我們面前,它們就圍繞在我們身邊,構成了我們居住其間的世界。它是如此為我們所熟悉的事物,以至於他認為我們也許想問「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人、植物、動物,那些我們周遭所見的東西;太陽、月亮和其他行星,那些我們在天空中所見,有關運動、時間和空間之概念核心的事物;甚至所顯現給我們的,構成了所有這些事物的整個宇宙萬有。當然,每當問及我們耳熟能詳的事物,關於「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這類問題,我們也可以繼續問那些並非直接顯現或出現在我們面前,但我們相信它們存在於其他土地上的事物這個問題。不過這是第二個步驟,現在必須從我們早就熟悉的存有物開始。
然而,重要的是認知到,當亞里斯多德問「存有是什麼?」時,他希望這個問題能以一個特殊的意義被了解。如同他所了解的,主要不是「有什麼?」的問題,更要緊的是「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的問題。「有什麼?」的問題要求完全一般的存在著什麼的描述,我們可以說它要求存有的擴延性(extension)。不過,「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問的是使所是的任何事物成為該事物的是什麼。它要求所是的某物之所以是某物,或者所是的某物憑藉什麼而為某物,所需的一個解釋。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要求存有的本質(essence),而且要求存有之本質的一個解釋性說明。亞里斯多德說(例如在第四卷開頭),他想要研究「作為存有的存有」,意思是他想要研究存有物,而且單純在它們乃事物所是的存有物之範圍內(in so far as)研究它們,而這恰好是研究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存有的本質。所以,如同亞里斯多德所了解的,形上學不在於尋求一個完整的和一般的存在著什麼之描述;重要的是在於尋求所是的某物之所以是某物,或者所是的某物憑藉什麼而為某物,這樣的一個解釋。
從《形上學》的一開頭(第一卷第二章),亞里斯多德即賦予形上學,或者在這個階段他所謂的「智慧」(sophia),以尋求解釋(aitiai,也可譯為「原因」)和解釋性的知識(epistm),亦即某物為什麼如其所是的知識的一個特徵。我們可以稱這種知識為「科學性的知識」和「科學」,亞里斯多德也一再地把形上學說成是對這種知識的探索;尤其是,他說形上學即為最根本的科學(prt epistm,見 VI.1, 1026a29),因為它尋求的是最根本的解釋。他稱這些解釋為「第一解釋」和「第一原理」(prtai aitiai, prtai archai),並說它們乃一切存有物(panta)和存在著的一切事物之解釋。不過,他認為這種根本的、普遍的解釋,恰好是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之解釋。
我們將越來越熟悉形上學的基本問題:「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但值得強調的是,亞里斯多德從一開始就把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之探索,與對解釋性的知識,亦即事物為什麼如其所是的知識之探索聯結起來。所以,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同樣可以明確地陳述為:「存有物為什麼是事物所是的存有物?」當然,這不得與「為什麼存在著事物所是的存有物?」的問題混為一談。一般而言,我們不得將類型(1):「為什麼存在著為F的事物?」與類型(2):「為什麼為F的事物是F?」這兩個問題互相混淆。《形上學》中的基本問題「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乃關聯到類型(2)而非類型(1)。
最後順便一提的是,亞里斯多德並不認為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存有是什麼?」乃他個人之發明。反之,在《形上學》核心的一個重要章節中,他強調這個問題就像樹木一樣古老,而且一直是「人們所尋求的」(to ztoumenon)問題,也是「困惑的根源」(to aporoumenon):
誠然,現在和許久以前,「存有是什麼?」的問題始終是人們所尋求的,也是困惑的根源……(Ⅶ.1, 1028b2-4)
從《形上學》一開頭(第一卷第三至十章),他顯然就認為早先的思想家同樣也曾致力於一般而言的和整體而言的存有之研究(見Ⅰ.3, 983b1-3的例子)。在這裡(第一卷第三至十章)他召集了許許多多的早期思想家加入這項分有的探索當中: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阿那克薩戈拉(Anaxagoras)、畢達哥拉斯派(Pythagoreans),以及最重要的,當時才剛剛去世的柏拉圖。
第二節 「存有是什麼?」問題的根源
然而,為什麼亞里斯多德認為我們也許想要問「存有是什麼?」這個問題呢?他在《形上學》開頭(第一卷第一章)就主張說,因為我們是人,因此我們會問這個問題。他主張,所有動物都渴求某些種類的知識(to eidenai),特別是感官知覺(aisthsis)的知識。但使人類與其他動物有別的是,我們不單渴求那些我們能力所及的知識,包括其他動物也渴求的知識,還渴求解釋性的或科學性的知識(epistm),也就是解釋的知識(aitiai)。他進一步主張,解釋性的知識需要知道事物的本質的知識是什麼;因為藉由認識一個事物真正的本質,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事物如其所是。例如(這是以亞里斯多德第一卷第一章中的例子為基礎的),藉由嘗試去認識某種疾病真正的本質,一個具備科學頭腦的醫師才可以試著去解釋為什麼這個疾病如其所是,並且呈現它所呈現的症狀:為什麼它具有該症狀、病因,以及它具有的結果;為什麼它對某一療法有反應,對另一種療法則否。
所以,亞里斯多德主張,單純因為我們是人,因此我們尋求科學和解釋性的知識;而且解釋性的知識需要認識事物的本質。不過他也主張(在《形上學》第一卷第二章中),形上學乃最根本種類的解釋性知識;它是最根本的解釋和一切事物的解釋之知識。而這恰好是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的知識,亦即它是存有的本質的知識,也是「存有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所以他主張,因為我們是人,因此我們想要問「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而且想要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然而,在《形上學》的第一和第三卷中,關於為什麼我們也許想要問「存有是什麼?」這個問題,卻似乎顯現出不同的理由來。因為亞里斯多德主張(第三卷第一章),通常激發我們去問有關存有的問題並尋求答案的,乃它們本身出現在我們面前之關於存有的特殊 aporiai1(疑難)──就我們為之困惑不解的特殊疑問和難題之意義而言的疑難。他接著(在第三卷第二至六章中)列出大約十五個關於存有的疑難。但在這樣做之前,他主張(第三卷第一章),激發我們去尋求存有是什麼的,恰好是關於存有的這種疑難,而且如果我們並未困惑於這種疑問和難題的話,那麼我們甚至無法開始尋求存有是什麼。這暗示,亞里斯多德認為「存有是什麼?」並非我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提出的、隨隨便便的問題;它毋寧是作為一個疑問和難題(aporia)自己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或者作為自己本身出現在我們面前,類似疑問和難題之直接結果的一個問題。一般而言可見到的是,關於存有的疑難絕對是《形上學》一書的核心,實際上也是《形上學》的整個研究課題,對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之探索課題。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中所用的方法,根本就是以「疑難」為基礎的(見第三章)。
因此,亞里斯多德認為「存有是什麼?」正好不是什麼問題,而是一個「疑難」;亦即一個自己出現在我們面前並使我們為之困惑不解的疑問和難題。這個迷人的觀點有待辯證地追溯到了柏拉圖,特別是在《智者篇》(Sophist, 242bff.)的對話中,柏拉圖主張:我們徹徹底底地困窘、困惑於存有。柏拉圖確認了這個困惑,他也稱之為「疑難」的,一個特殊根源。因為他主張,我們關於存有的困惑最重要的是從我們所遭遇的,關於實際上和根本上存在著什麼的不同觀點中冒出來的。他指出,某些人(多元論者)主張實際上和根本上存在著不同種類的事物,但其他人(一元論者)卻主張實際上和根本上只存在著一種事物(《智者篇》242b-245e)。此外,某些人(唯物論者)主張唯獨變化且有形的(material,或譯物質的、具體的)事物乃實在的事物,但其他人(非唯物論者)卻主張唯獨不變而無形的事物才是實在的事物(《智者篇》245e-249d)。不過,柏拉圖說所有這些觀點都有問題。該問題不在於我們不知道哪個觀點是對的,而在於我們甚至不能真正了解每個觀點意味著什麼(《智者篇》243b)。因為他主張,除非我們追問存有是什麼和存有的本質是什麼,亦即除非我們問「存有是什麼?」,否則我們就無法正確地問實際上存在著什麼事物,亦即我們無法正確地問:「存在著什麼?」所以,除非我們問存有是什麼,否則便無法正確地問諸如實際上存在著的事物乃一或多、有形或無形等等問題。柏拉圖斷言,如果我們要問「事物根本上是有形的或無形的?」這樣的問題,我們也必須問「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等基本問題。不過,他認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曾經好好地問過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柏拉圖的論點似乎是這個。如果我們想要做任何全然普遍的聲稱,亦即聲稱「一切事物根根本本是某某(例如有形的)」形式的,那麼我們必須同時提出「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之基本問題。我們必須如此以便證明,實際上是為了正確地了解我們也許想要做的,任何全然普遍的聲稱。
這似乎也是亞里斯多德的全部觀點──在這點上,他可能曾經受到柏拉圖的影響。這個總觀點認為,「存有是什麼?」不只是那種我們也許會問也許不會問的隨便一個問題;它是為了特殊理由而自行出現在我們面前,並使我們為之困惑不解的一個疑難,一個疑問和難題。因此,在《形上學》中亞里斯多德很早(第一卷第二章)就主張,最初激發我們去問有關存在著什麼之普遍問題的就是疑難(aporiai)。他接著(第一卷第三至十章)列出若干不同的普遍聲稱,乃前輩思想家們曾經抱持的有關存在著什麼的聲稱。然後(第三卷第一章)他主張,若無關於存有的特殊疑難,我們根本無法尋求存有是什麼。他接著(第三卷第二至六章)列出有關存有的大約十五個疑難,是他打算在《形上學》的其餘部分予以回答的。最後(在第四卷開頭),他意味深長地提出了「作為存有的存有是什麼?」這個問題,亦即「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我們應該留意到,第一、三、四卷乃結合為一體的,而第二卷則是稍後才被安插到第一和第三卷之間的)。
所以,如同亞里斯多德所了解的,每當我們思考而碰巧別人也思考著,根本上存在著什麼和事物根本像什麼樣子的時候,「存有是什麼?」的問題,似乎就從那可能自己現身在我們面前的某一疑問和難題當中冒了出來。一般而言,「存有是什麼?」似乎是從某一自己現身在我們面前的疑難當中產生,每當我們想做全然普遍的聲稱「一切事物根根本本就是某某(例如有形的)」形式的時候。它是關於這種全然普遍之聲稱的意見,以及由這種聲稱所產生的難題,因此可能促使我們去問「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的基本問題,並且開始去尋求答案。
這也暗示,每當亞里斯多德主張(在《形上學》頭兩章中)我們之所以想要問有關事物的本質的問題,尤其想要問有關存有本身之本質的問題(「使某物成為某物所是的一個存有物的是什麼?」),乃因為我們是人,他心裡所想的是人類的一個特殊特徵:成為人就是成為容易因為特殊的疑難(aporiai)感到困惑不解(aporia)的。當然,這並非人類的唯一特徵。然而,它卻是最終會促使我們去問有關存有本身並且去尋求存有是什麼的困惑。
值得留意的是,這也說明亞里斯多德並不認為「存有是什麼?」的問題,單純由我們日常地、前哲學地想和說什麼而引起,儘管我們說某物是或者不是什麼,例如,當我們說花園裡有樹木或花園裡沒有樹木的時候。因為我們所問的類似「事物根本上是有形的或無形的?」這種問題,以及我們所想要做的全然普遍的聲稱,顯然不是就日常的情形和前哲學的心境而言。更確切地說,全然普遍的問題和聲稱恰好是哲學的,概括地說乃形上學的。
一般而言如同亞里斯多德所了解的,形上學就某種可能以理所當然且強而有力的方式自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疑問和難題而言,具有它自己的根源。不過,這不是形上學之外的根源。反之,作為形上學根源的疑問和難題── aporiai,本身就是形上學的疑問和難題,亦即當我們省思全然普遍的問題和聲稱時,所顯現出來的疑問和難題。關於這一點,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概念就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而言,有別於主張如果形上學完全有可能的話,它之所以有可能乃因為它是立基於在它之外的某物:認識論,或邏輯學,或一般語言,或別的某物,或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之某個典型的現代概念。我們稍後會回到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概念,與某個典型的現代概念之間的重要差異(見第三章第二至三節)。該差異在於形上學的現代概念於形上學之外,例如在邏輯學或認識論當中,典型地尋求形上學的根源,實際上尋求形上學之真正可能性的根源;亞里斯多德卻主張形上學以及其真正可能性的根源,乃在於形上學本身之內。
這同樣暗示到,正好和亞里斯多德或柏拉圖一樣,我們也許想要問:「存有是什麼?」因為今日的哲學家,或至少某些哲學家,同樣也會問諸如「事物是有形的或無形的──特別是精神的(心理的),或者也許兩者都是?」或「一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或者也存在著非物質的事物?」或「一切事物都是個別物或者也存在著普遍物?」或甚至「事物是什麼乃無關乎我們,或者它們是什麼單單與我們有關,以及與我們怎麼表述它們有關?」等問題。一般而言,問全然普遍的問題和做全然普遍的聲稱之趨勢,未曾銷聲匿跡或緩慢下來。不過,我們極可能感覺這樣的問題多多少少總是與「存有是什麼?」,以及「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之基本問題聯結在一起。所以,我們極可能認為問這問題是很自然的,或者是很合理的。當然,這並非意味著我們必須問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也許想要拒絕其根源,亦即拒絕認真地問,以及認真地接納那些問諸如事物是否根本是有形的,或者是否存在著普遍物,又或者事物之所以是什麼無關乎我們等等這些問題的人。一般而言,我們也許想要拒絕做任何普遍聲稱,和提出任何普遍問題之趨勢。然而,這將會一起拒絕掉形上學,即使形上學乃廣泛地被了解為意欲尋求存在著什麼,以及事物一般而言像什麼樣子。不過,雖然在今日這或許是一種普遍態度,卻絕非人人分有的態度,而且形上學概括而言依然生氣勃勃,一如往昔。至於它是否真的有可能成功地拒絕做任何普遍聲稱,或提出任何普遍問題,而不一起拒絕掉哲學,以及實際上在科學之內的一個重要趨勢,同樣令人懷疑。
我們已經看到,亞里斯多德認為形上學的基本問題,「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乃深植於某個形上學的 aporiai(疑難)之中,亦即深植於當我們省思關於一般的事物,以及所有事物的某個問題時所產生的某個難題和疑問之中。在這裡,區別一下在《形上學》中將變得更為凸顯的,形上學的三個一般種類之疑難可能是有用的,我們稍後打算詳細地予以討論。
首先,第一種形上學的疑難與事物怎麼能夠具有屬性,以及一般而言某物怎麼能夠適用於某物的問題相關聯。這個問題尤其可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早期作品《範疇篇》(Categories,見第四章第四節)。我們將回到這個根本關係,亦即x 適用於y 的關係,待會兒(見第四節)以及稍後(第四章第四節,尤其是第七章第三節和第五節之第六、五、八小節)將再次詳細討論。在那裡我們也將考慮這個問題所引起的某個根本疑難,以及亞里斯多德如何予以回答。
其次,第二種形上學的疑難與事物怎麼能夠是可理解的且容易解釋的之問題相關聯。這個問題尤其可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早期著作《分析後篇》(Posterior Analytics),稍後我們將考慮亞里斯多德關於解釋的理論(第二章第三節),更後面也會考慮這個問題所引起的某個根本疑難,而亞里斯多德又是如何予以回答的(第七章第五節之第八至第十小節和第八章)。
最後,第三種形上學的疑難與事物怎麼能夠是變化的,尤其事物怎麼能夠就它們乃容易解釋的這樣一種意義而言是變化的之問題相關聯。這個問題可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早期作品《物理學》(Physics)。稍後我們將考慮亞里斯多德有關變化和變化的事物之理論(見第二章第四節),更後面則會考慮這個問題所引起的某個根本疑難,以及亞里斯多德如何回答(第七章第五節之第六、七和九小節)。
第三節 《形上學》中的一個主要差別:一般而言的存有vs.第一實體
《形上學》一書中的主要重點在於亞里斯多德關於一般而言的(to on)存有與第一實體〔prt ousia,通常簡寫作 ousia;以下選擇將 prt ousia 譯作「第一存有」(primary being; prinary 有第一的、根本的、最初的、原始的和首要的之涵義)而非譯作「第一實體」(primary substance)〕之間的差別。他在第四卷第二章中首先提出這個差別,在第七至九卷,《形上學》的核心之卷中則更為凸顯。我們稍後(第四章第一至三節和第七章第一、四節)將詳細考慮這個差別,但立即留意到這個差別也很重要。亞里斯多德介紹這個差別以便提出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因為他主張,為了提出「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等問題,我們必須提出「第一存有是什麼?」和「使某物就最先的意義而言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之問題。尤其,他主張如果我們想要尋求存有是什麼,以及使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我們必須藉由尋求第一存有是什麼,以及使某物就最先的意義而言成為某物的是什麼而如此行。
斷言我們唯獨藉由尋求第一存有是什麼,才可以尋求存有是什麼的這個論據,足以提出第一存有(prt ousia)的概念,以及提出一般而言的(to on)存有與第一存有之間的差別。第一存有這個概念,以及一般而言的存有與第一存有之間的差別,將會變成《形上學》的絕對核心。因為在《形上學》的核心之卷,第七至第九卷中,亞里斯多德打算尋求關於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存有是什麼?」的答案,而且最終將提供一個答案,恰好藉由尋求「第一存有是什麼?」之問題且最終提供其答案而如此行。我們不妨為我們唯獨藉由尋求存有是什麼,才可以尋求存有是什麼的結論,簡短地預備論據(關於第一存有之概念的充分論據和說明,見後面第四章第一至三節)。
這將顯示,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存有是什麼?」和「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引起了有關形上學的真正可能性的根本疑難(aporia):表述一般而言的存有和整體而言的存有,以及意味深長地問「使任何某物成為某物的是什麼?」何以甚至有可能?亞里斯多德在第三卷,疑難之卷,將提出這個疑難(見第三個疑難,997a15-25,以及第七個疑難,998b22-27的一部分)。扼要言之,該疑難如下面所言:我們無法藉由將存有與非存有區別開來以表述存有,我們也無法將存有表述為存在著的所有種類之存有物的總合。所以,我們要麼藉由將存有與在它之外的某物,亦即與非存有區別開來,要麼藉由將存有與在它之內的什麼區別開來,亦即藉由將它表述為存在著的所有種類之存有物的總和,以及一般而言將它表述為存在著的一切事物的總合,否則顯然完全無法表述之。
亞里斯多德之所以打算(在第四卷第二章中)提出第一存有的概念和一般而言的存有與第一存有之間的差別,乃為了回答有關形上學的可能性的這個疑難。扼要言之,這就是該疑難的答案。假定我們要麼藉由將存有與在它之外的某物區別開來,要麼藉由將存有與在它之內的什麼區別開來,否則便無法表述一般而言的存有和整體而言的存有。或許我們仍然可能表述存有,如果我們假定在單純憑藉它們本身而為存有物的事物(亦即第一存有物),與憑藉它們和那些事物的關係而為存有物的事物(亦即非第一存有物)之間,有著一個差別的話。因為那樣我們就能夠以下述方式來表述存有:藉由假定所是的任何事物,亦即任何存有物,要麼單純憑藉其本身而非憑藉它與其他事物的關係而為一個存有物(在此情形下它是一個第一存有物),要麼憑藉它與一個第一存有物的關係而為一個存有物(在此情形下它是一個非第一存有物)。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瓦薩利.波利提斯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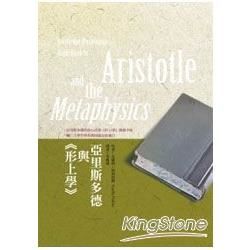 |
$ 360 ~ 475 | 亞里斯多德與形上學-經典哲學名著導讀 002
作者:瓦薩利.波利提斯(Vasilis Politis) / 譯者:李鳳珠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09-08-2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92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亞里斯多德與《形上學》-經典哲學名著導讀02
亞里斯多德是西洋上古哲學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形上學》為其代表作,影響後世的思維方式千餘年,至今《形上學》仍舊為哲學的主流研究。系統性地討論《形上學》的各個層面,除提供亞里斯多德的背景資料,更討論了形上學的定義、本體論、神與眾神、以及與科學的關係,為一本深入淺出的導讀入門書。
作者敘述精確、結構嚴謹……不但對研究哲學的學生是一個愉快的閱讀,對哲學的研究者們也是如此。 -- Journal of Philosophy
迷人、發人深省的《形上學》導讀書籍。 -- Stasinos V. Stavrianeas, Philosophical Books
這本書帶著哲學性的敏銳,寫的極好。 -- David Charles, Oxford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瓦薩利•波利堤(Vasilis Politis)
牛津大學哲學博士,目前任教於都伯林大學的三一學院哲學系,研究領域以上古哲學為主,近年特別關注亞里斯多德及柏拉圖的思想。此外,興趣亦擴及現代的形上學,以及形上學與科學間的各種爭議。
譯者簡介:
李鳳珠
學歷:臺灣大學夜間部中文系畢業
經歷:從事編輯校對、潤稿工作二十年,樂在其中
酷愛閱讀,文史哲及自然科學皆為所好,自我要求認真,近乎苛求完美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第一節 《形上學》談什麼?「存有是什麼?」的問題 本書所談及題目為《形上學》(Metaphysics)的著作,乃全部或大部分由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撰寫的一套十四卷文集,是他生命最晚期的作品。《形上學》是亞里斯多德在雅典創辦了他自己的哲學學校呂克昂(Lyceum)學園或稱逍遙學園(Peripatos)之後(335 BC)才寫的;也就是說,即使《形上學》是亞里斯多德花費很長的時間才寫成的,也應該是在他離開了柏拉圖(Plato, 427-347BC),並且在雅典的學園待了好幾年之後才創作的。因為他在十七...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
第二章 作為一切事物的終極解釋之科學的形上學?(第一卷)
第三章 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中的方法(第三卷)
第四章 作為存有的存有之科學的形上學─原始存有vs.非原始存有
第五章 非矛盾律的辯護(第四卷第三至六章,尤其第三至四章)
第六章 對現象論和相對論的回答(第四卷第五至六章)
第七章 對原始存有的探索(第七卷)
第八章 變化的終極原因:神(第十二卷)
第九章 對柏拉圖的形式論之批評
第二章 作為一切事物的終極解釋之科學的形上學?(第一卷)
第三章 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中的方法(第三卷)
第四章 作為存有的存有之科學的形上學─原始存有vs.非原始存有
第五章 非矛盾律的辯護(第四卷第三至六章,尤其第三至四章)
第六章 對現象論和相對論的回答(第四卷第五至六章)
第七章 對原始存有的探索(第七卷)
第八章 變化的終極原因:神(第十二卷)
第九章 對柏拉圖的形式論之批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鳳珠, Vasilis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1 ISBN/ISSN:97895711556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西方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