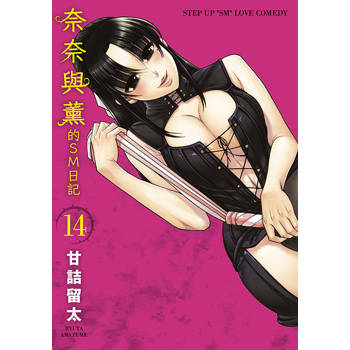18 世界盡頭的午餐
智利
南美大陸呈三角形,下方算起約五分之一的地區叫巴塔哥尼亞,大半都是荒涼的地域,只有小部分是森林,人煙極為稀少,整年都颳著颱風般的狂風,「世界盡頭」的稱號確實十分貼切。騎完這長達二千五百公里的地區,就能抵達美洲大陸的終點——世界最南端的城市「烏斯懷亞」。
巴塔哥尼亞的旅程終於進入後半段了。
平緩的褐色丘陵無盡延伸,令我不禁感嘆:地球果然也是座行星哪!我拚命維持平衡,不被風吹倒,默默騎過砂礫滿布的道路。這一帶緯度很高,相當於北半球的堪察加半島,還是初秋,風已冷得刺骨。
空中烏雲密布,風勢更強了,大雨開始斜斜飛落。正好看到前方有戶人家,我連忙衝進屋簷下。
這房子或許因為整年都受巴塔哥尼亞狂風吹襲,牆壁已經像枯樹一樣腐朽了,乍看之下也不曉得有沒有人住。
門突然打開,有個老人探出頭來。像反射動作一樣,我露出笑臉說:「Hola!」老爺爺卻沒回話,只是一直凝視著我,眼神彷彿帶點怒意,一頭白髮亂蓬蓬的,牛仔褲也泛黃得厲害,好像隨時會冒出酸臭味。
「我可以在這裡躲雨嗎?」我問道。
老人依舊不苟言笑,朝裡面撇了撇頭,看來是叫我進去。
屋裡給人的印象完全不一樣,不像牛仔褲,反而整理得相當乾淨。正中央有座鐵製的陳舊燒柴暖爐,上頭有個平底鍋。
他讓我坐在餐桌邊,走到廚房去,馬上端了兩杯咖啡過來,坐在我面前,還是板著一張臉望著我。
這位老爺爺不只沉默寡言,根本一句話也不講。我無可奈何,只好主動問他幾個問題,是一個人住這裡嗎?他說是。
外頭風勢更強了轟隆隆的重低音傳來,窗戶也像歇斯底里發作般激烈地喀吱搖晃。每天聽著這樣的聲音,感受又是如何?
老爺爺拿起爐子上的平底鍋,用盤子盛了些菜給我吃,是羊肉炒馬鈴薯。材料潦草地切成大塊,有種寂寥的感覺,好像在說:既然一個人吃,長相怎樣就不用在意了!
可這菜非常好吃,一點都不像已經擱了段時間。羊肉黏稠的肉汁裹著馬鈴薯,芳香又濃郁。我撕開法國麵包沾著肉汁吃,柔軟的麵包和肉類濃醇的味道非常搭配。
突然,我注意到餐桌下的椅子。五、六張木椅散發沉穩的光芒,好像經常打磨。這椅子如同整理好的房間,似乎是在等待客人光臨。
會有客人跑到這麼偏僻的地方嗎?想到這裡,我有點恍然大悟,腦中浮現老爺爺一個人打磨椅子的模樣,難道他一直在等待不知會不會到來的訪客嗎……
風的怒吼越來越強,敲打窗玻璃的雨聲也更激昂了。
老爺爺還是老樣子,一直瞪著我猛瞧。我無聲地吃完飯,他終於主動開口說話:
「Quieve más?(要再添嗎)」
真是出乎我意料。我望著老爺爺,他還是瞪大眼睛,一點表情也沒有,該不會已經忘記要怎麼跟人相處了吧?還是因為住在這種海角天涯,不再和別人交流後,也就不會把感情表露出來了?
我請他再添一盤,又吃起馬鈴薯和羊肉。
中午一過,雨聲漸轉稀疏,慢慢地聽不見了。我向老爺爺道過謝,走到外頭,雨已經停了,吹起濕潤的風。
開始騎車前進。往房子的方向一看,老爺爺在屋裡,站在灰暗的玻璃窗旁。雖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不管我回過頭看幾次,他仍一直望著我。
19 火地島的鱒魚
阿根廷
巴塔哥尼亞的河裡都是密密麻麻的虹鱒和棕鱒,由於人煙稀少,魚也特別老實,只要選對地點,長二十到三十公分的鱒魚就會接二連三上鉤。我都拿來做成炸魚塊,或用奶油煎著吃。本以為牠們在大自然的河流中長大,一定沒有腥臭味,口味也會很清爽,沒想到,還是帶有一絲淡水魚特有的腥味。
我從蓬塔阿雷納斯搭船來到火地島。雖說是島,面積還比日本九州大了一圈。看看地圖上的形狀,應當是南美大陸尖端被海峽切斷形成的,其實應該比較接近「大陸的一部分」。世界最南端的城市「烏斯懷亞」,就在島上南方約五百公里處。
在火地島上騎了四天車,進入山區,開始出現叢生的南極山毛櫸,整座樹林紅葉似火。我一邊讚嘆,一邊在鮮紅的隧道中緩緩前進。來到這裡之後,巴塔哥尼亞的「名產」狂風也跟著乍然止息了。
森林空地的盡頭出現一條小河。我停下自行車張望,河底一片漆黑,看來頗深,卻不寬,幾乎不用助跑就可以一口氣跳到對岸,雖然我猜想這種地方可能沒什麼魚,還是拿出釣竿。聽說巴塔哥尼亞地區,特別是火地島,是釣魚翁憧憬的勝地!
我朝接近對岸的地方甩出魚鉤,再拉回自己面前,一點「徵兆」也沒有,我喃喃自語:這條河果然不行嗎?正想放棄,下一瞬間,幽暗的河底有個巨大的陰影在移動——
「!」
影子隨即翻身潛入河底,但我還是清楚看見了,的確有張巨大的嘴巴對著魚鉤開闔。
我心頭怦怦亂跳,慎重地第二次拋竿,讓魚鉤沉入水中,再慢慢捲線。格登一聲,強烈的魚信來了,釣竿跟著一彈,我鼓足勁拉扯,竿子就彎得跟長弓一樣,捲軸也猛轉,不斷放出釣線,巨大的黑影在河底狂亂掙扎,我的膝蓋也在發抖,竟然有這麼大的獵物!
經過十分鐘左右的拉鋸戰,好不容易把魚釣上來了。是條圓滾滾的大棕鱒,花紋褪去,已化為「銀色」了。用捲尺一量,竟有六十一公分長,我猶豫了很久,一個人畢竟怎麼吃都吃不完,最後還是放生了。
我重新拋餌,這次又有大魚上鉤。釣了一個半小時,陸續釣到四條鱒魚,每條都超過五十公分。我的心情非常複雜,每釣到一條,就放走一條,根本釣不到一人份的鱒魚,真是一大失算!不,火地島果然是「釣魚天堂」哪!比傳聞更驚人。
隔天傍晚,我翻過最後的山頭,往下坡騎時可以望見烏斯懷亞的燈火。從阿拉斯加出發,經過一年九個月,我終於完成縱貫美洲大陸的旅程了!即使如此,還是一點真實感也沒有,自己邊騎下城鎮,邊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心情會如此平靜呢?
烏斯懷亞和想像中完全不一樣,洗練而美觀,高聳的群山環繞,氣氛儼然是瑞士的山間小鎮。
這裡有位日裔名人,名叫上野大叔。他提供自己的家給日本遊客住,口耳相傳後,乾脆開放別墅,經營起旅館來了。
我來到那裡,一打開交誼廳的大門——
「哦哦!辛苦啦!」
有人熱鬧地齊聲大喊,南美洲的老臉孔齊聚一堂。
「什麼嘛!你們還在啊?」
大家似乎都很喜歡這座城鎮和旅館,臉上都洋溢著抵達大陸終點的充實感,情緒也鬆懈下來。我完成目標,接受他們的祝福,終於也漸漸湧起「抵達了」的感受。
在南美洲經常遇到「自力」移動的旅人,那時在場的的人物有騎機車旅行的四人組、環遊世界的情侶檔、同樣以環遊世界為目標的小哥,及在南美洲旅遊的醫生等,形形色色。
有次,我和他們去露營釣魚。
我坐在機車後座,穿越山區,騎了一個鐘頭左右,來到布滿大顆砂礫的美麗河岸,眼前是極為澄澈而廣闊的清流。
接近黃昏時分,我們不斷釣上二十至三十公分長的鱒魚。
把剛釣上的魚灑上鹽巴,用樹枝刺穿,再用營火烤著吃,一直烤到表皮焦黃,皺了起來。這時,烤魚冒出白色蒸汽,淡粉紅色的魚肉露了出來,不可思議的是,一點腥味也沒有,味道和大陸上的鱒魚明顯不同。有人叫道:
「哇!這是什麼?」
朝他那邊一看,他咬過的魚肉就像鮭魚肉,是鮮紅色的。可是,他會這麼大叫,並不是因為魚肉的顏色,我拿來嘗了一口,反應一樣激動:
「這是什麼?」
味道和一般鱒魚完全是天壤之別,入口逐漸融化,濃郁而甘美。要是把一般鱒魚比喻成蕃薯,這種「紅肉鱒魚」就是加入大量高級奶油和和白醬一起搗碎的甜馬鈴薯泥了!
「哦哦!這條也是!」另一個人叫道。
似乎又有人嘗到「紅肉鱒魚」了。大家都躍躍欲試,大口咬起烤鱒魚來。
「哇!太好了,中獎啦!」
「可惡,這隻也不是!」
大概七、八條魚裡會有一隻是「紅肉」,同一條河流竟會有這種差別,不是有點稀奇嗎?
不過,大家幸運吃到「紅肉鱒魚」時的歡喜,又該怎麼形容呢?我笑著說:
「簡直就像小孩子吃到『再來一支』的冰棒嘛!」
才剛說完,就有人隨即還嘴:
「最興奮的人應該是你吧?」
眾人放聲大笑。放眼望去,每個人都沐浴在陽光中,露出爽朗愉悅的表情。
我終於重新領會到——我已抵達大陸的終點了!
20 手釀葡萄酒
阿根廷
我由烏斯懷亞搭巴士抵達聖地牙哥,接著便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下一個目的地,打算橫越整座大陸。
一踏進阿根廷門多薩州,葡萄田隨處可見。提起南美洲的葡萄酒,在日本雖然以智利較為有名,其實阿根廷的產量遠在智利之上。可惜季節將近晚秋,採收過的葡萄樹都枯萎了,滿眼寂寥。
路旁可以看到許多寫著「VINO de MANO」的招牌。「VINO」是葡萄酒,「MANO」是手,是指手釀葡萄酒?招牌底下還放有酒樽。
湊過去一看,一杯大約要五十日圓,來試喝一杯吧!
有個像是農場工人的小哥直接把酒樽裡的葡萄酒倒進杯子裡,酒液濃濃稠稠,顏色非常深。
喝下去的瞬間,我的臉馬上皺成一團。怎麼這麼甜?簡直像沒稀釋過的果汁。
打聽之下,這果然是偏甜的酒。接下來我又試喝不甜的,雖然稍微正常了點,還是甜得讓人想加水進去。這東西是像水果酒那樣,先把水果以砂糖醃漬過,再拿去釀嗎?不,等等,這種甜膩感和濃稠度,該不會是尚未過濾的濁酒吧?
換個念頭這麼想,再喝時就覺得「這味道還可以」,我隨即買了一公升。
我請他們把酒裝進保特瓶裡,對著陽光一照,無數沈澱物像木屑般在黑漆漆的液體中飛舞,果然有手工釀造的感覺。
夕陽西下時,我發現前頭有座小小的釀酒廠,建築物前頭還有漂亮的草坪。我拜會廠長,請他讓我在這裡紮營一晚,對方也爽快地答應了。
我在帳棚前恍惚地欣賞夕陽沉入地平線時,有十個男女從工廠走出來,大概是收工了吧。他們看到我搭在空地上的帳棚,說了些什麼,表情愉快地笑了。
隔天早上,我竟然睡過頭,醒來時已經能聽到工廠機器運轉的聲響。正在收拾帳棚時,廠長叫我過去,說要帶我參觀一下。
意外的是,工廠已經自動化了,巨大的銀色機器轟隆作響,不斷吐出紙盒裝的葡萄酒。在只能看見地平線和葡萄田的鄉間,這空間還真是異樣,生產線四周的作業員看到我也露出微笑,揮手打招呼。
參觀完了,廠長送我兩個紙盒,是一公升裝的葡萄酒。我忍不住苦笑,昨天才買了一公升的手釀葡萄酒呢!
我畢竟還是沒力氣帶三公升葡萄酒上路,鄭重向廠長道歉,還他一盒,另一盒則倒進保特瓶裡,放在自行車的飲料架上,邊騎邊喝時才發現:「哇!味道真好!」
昨天在我眼中很是煞風景的大平原,景色也突然迷人了起來。
翌日,別人送的葡萄酒就喝完了,早知道就應該收下兩盒的!
我抵達下個城鎮時,又買了新的葡萄酒,一公升只要一披索,相當於一二○日圓。把酒倒進瓶子裡,邊騎車邊咕嘟咕嘟地喝,一個人樂呵呵地笑。
從那天開始,飲水瓶裡裝的就不是清水了,我每天都會換上新買的葡萄酒,只有剛開始買的手釀葡萄酒一直不見減少。畢竟對我這種年輕人來說,還是大量生產的葡萄酒比較對味,手釀酒就只好拿來做菜,最後酒已經酸得像葡萄酒醋了,只好雙手合十,讓它回歸大地啦!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用洗臉盆吃羊肉飯: 世界九萬五千公里的自行車單騎之旅III的圖書 |
 |
$ 160 ~ 246 | 用洗臉盆吃羊肉飯-FUN 12
作者:石田裕輔(Yusuke Ishida) / 譯者:劉惠卿 出版社:繆思 出版日期:2008-03-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0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世界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用洗臉盆吃羊肉飯: 世界九萬五千公里的自行車單騎之旅III
作者簡介:
石田裕輔日本單車環遊世界紀錄保持者,1969年生於日本和歌山縣。著有《不去會死》、《最危險的廁所與最美的星空》、《用臉盆吃羊肉飯》三本書。高中一年級自行車環和歌山縣一周後,開始憧憬單車旅行;19歲時休學一年,踏上環遊日本的旅程;1995年辭去食品製造大企業的工作,踏上環遊世界之旅。原本預定三年半完成回國,因旅程太有趣,不知不覺花掉七年半光陰。回國後專心執筆,巡迴日本各地演講,並獲多本知名旅遊雜誌邀稿。本書在日本和韓國都獲得熱烈迴響,書迷甚至為他成立專屬後援會;他在旅途中組成的樂團Hypocrites(偽善者),也在日本推出專輯CD。
章節試閱
18 世界盡頭的午餐智利南美大陸呈三角形,下方算起約五分之一的地區叫巴塔哥尼亞,大半都是荒涼的地域,只有小部分是森林,人煙極為稀少,整年都颳著颱風般的狂風,「世界盡頭」的稱號確實十分貼切。騎完這長達二千五百公里的地區,就能抵達美洲大陸的終點——世界最南端的城市「烏斯懷亞」。巴塔哥尼亞的旅程終於進入後半段了。平緩的褐色丘陵無盡延伸,令我不禁感嘆:地球果然也是座行星哪!我拚命維持平衡,不被風吹倒,默默騎過砂礫滿布的道路。這一帶緯度很高,相當於北半球的堪察加半島,還是初秋,風已冷得刺骨。空中烏雲密布,風...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石田裕輔
- 出版社: 繆思出版 出版日期:2008-03-01 ISBN/ISSN:978986666501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旅遊> 觀光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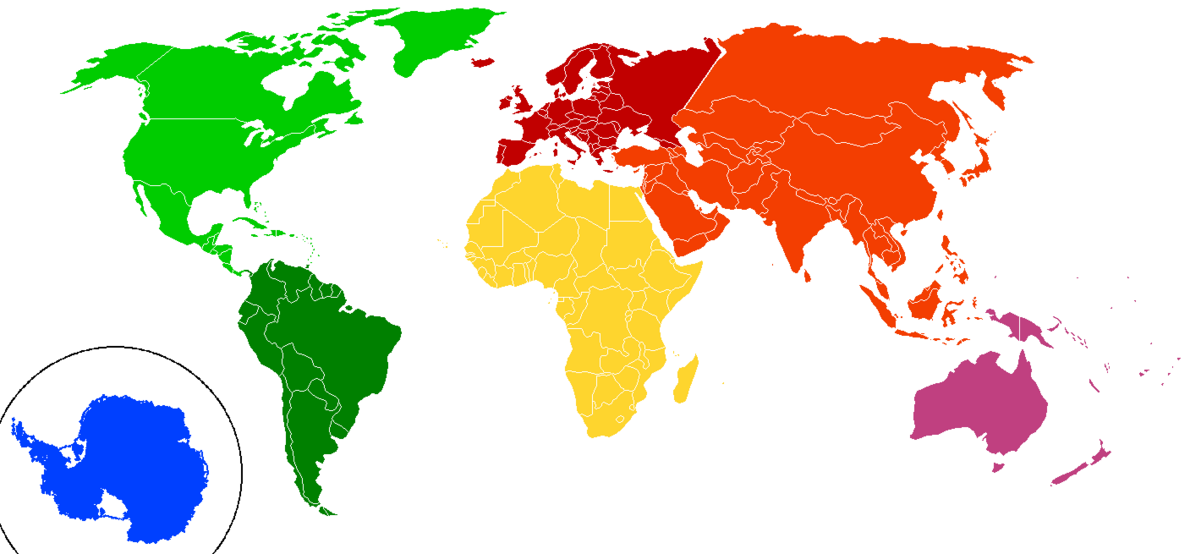 世界一詞在現代社會意為對所有事物的代稱。原本是佛教概念,由「世」和「界」組合而成的世界,即所謂由所有時間空間組成的萬事萬物。
世界一詞在現代社會意為對所有事物的代稱。原本是佛教概念,由「世」和「界」組合而成的世界,即所謂由所有時間空間組成的萬事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