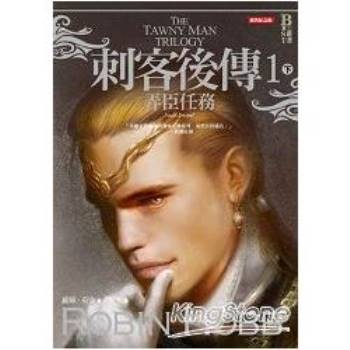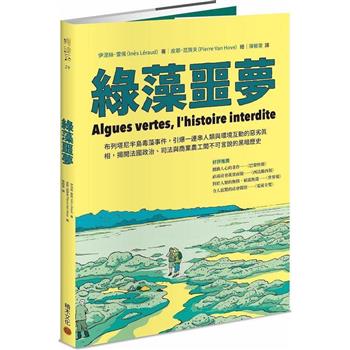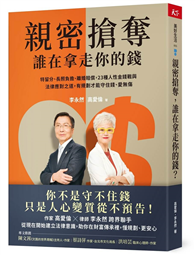第三章《莊子》
《莊子》一書,是莊子和他的門人及其後學所著,是戰國中期到秦漢之間道家莊周學派的文章總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將《莊子》與老子的《道德經》視為道家和道教的宗經寶典。《莊子》成書以來,以其深邃的義理、磅礴的氣勢、豐富的想像、超脫的境界影響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傳統文化,影響了儒家、佛教、道教等理論的發展。通常,人們將儒、釋、道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而正是《莊子》的出現,才使得道家發展成為與儒、釋鼎足而立的重要學派,使道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瞭解道家學說,要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不瞭解《莊子》。
一、《莊子》題解
(一)《莊子》的作者
莊子(約西元前三六九年至西元前二八六年)名周,字子休,戰國時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一說今安徽蒙城)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曾任蒙地管理漆園的小官。他本來是宋國人,因西元前二八六年(楚頃襄王十三年)齊滅宋後,齊與魏、楚三分宋地,蒙地屬楚,故莊子為楚人。他往來於趙、魏各國間,與楚國關係較深,和楚威王、楚頃襄王都有往來。
莊子非常有才,與名家的惠施是好朋友,曾與惠施有過關於「有用無用」、「有情無情」的爭辯,又曾與惠施在濠梁之上有過「魚樂與否」的辯論。莊子還收有一些弟子,曾與弟子談論「材」與「不材」的處世之道。
莊子一生窮困潦倒,《莊子‧列御寇》記載莊子「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即是說莊子居住在窮巷破屋之中,面黃肌瘦,以編織和賣草鞋為生。為了維持生活,莊子曾向監河侯(官名)借糧度日,又曾穿著補丁衣服用草繩繫著破爛的鞋子去見魏惠王。
莊子雖然一生受貧窮之困,但他又安貧樂道,不慕權貴,淡泊名利,鄙視榮華。楚威王聞其賢,派人請他任楚相(令尹),莊子以「寧遊戲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為辭,堅決拒絕。惠施任梁相時莊子去會見他,惠施害怕莊子取其位而代之,便於國中搜捕莊子三日三夜。莊子見到惠施後,自比為發於南海而飛往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的鵷雛,而將梁國相位比為腐鼠,將惠施比為吃老鼠的貓頭鷹。又有宋子曹商,以宋國使臣身分出使秦國而得車數乘,又因得寵於秦王而獲車百乘。曹商以此炫耀於莊子,莊子卻將之譏為舐痔而邀寵者。
莊子的妻子死時,莊子非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在他自己臨死時,弟子欲厚葬之,莊子卻說他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璣,以萬物為殉葬,認為自己的葬具已經很完備了,表現出對死亡的從容與超脫。
莊子學識淵博,與老子的思想一脈相承,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又「著書十餘萬言」,用以反對儒家、墨家的學說。《莊子》中有的篇章是專門針對儒家而發,「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因為莊子對老子的思想進行了繼承和發展,使道家成為一個與儒家、墨家鼎足而立的學派,所以後世以「老莊」並稱,莊子也成為道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二)《莊子》的內容結構
今本《莊子》共三十三篇,分「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三個部分。全書內容比較複雜,內篇與外篇、雜篇存在一些差異。內篇文章比較整齊,每篇都有一個篇名,內容偏重哲學論述,義理深邃;外篇、雜篇每篇基本上取開篇兩個或三個字作為篇名,主要是發揮內篇的思想。但外篇和雜篇在內容上又比較蕪雜,甚至個別篇章語詞低陋、內容平平。所以一般認為,內篇是莊子自著,外篇、雜篇則出自莊子門人及其後學之手。內篇可以作為研究莊子思想的主要依據,外篇和雜篇可以作為參考。現將各篇主旨概括如下:
內篇七篇
《逍遙遊》第一:欲得身心逍遙自在,須突破一己形骸之限制與外在功名、利祿、權位之束縛,而其要在於無己、無功、無名。
《齊物論》第二:是非之爭皆起於一己之私心成見,以道觀之,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如此則一切人與物皆有其存在之獨特意義與價值。
《養生主》第三:行事須順任自然條理,人能懂得此理,即能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於胸次,而可以養生盡年。
《人間世》第四:處世之艱在於人際關係之紛爭糾結,處世與自處之道貴在「虛己」與「無用」,如此則能周旋於亂世而物莫能害。
《德充符》第五:道歸本心可超越外在形體之殘疾與醜陋,和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大宗師》第六:大道為萬物之宗,萬眾之師,能體大道,則可天人合一、死生一如、安時處順。
《應帝王》第七:為政之道,在於效法大道之自然無為,無心而任萬物之自化,如此則可為帝王也。
外篇十五篇
《駢拇》第八:人的行為應合於自然,順人情之常。濫用聰明、矯飾仁義的行為皆非自然正道,自然正道在於「不失其性命之情」。
《馬蹄》第九:種種政教措施、政治權力都有違人之真性,人的理想生活狀態應當自然放任,順應自然天性。
《胠篋》第十:聖智禮法之設,本用以防治盜賊,卻反被盜賊所竊,用為護身的工具,禍害民眾。唯有絕聖棄智,毀棄禮法,方可止息大盜,天下太平。
《在宥》第十一:仁義禮法擾亂人心,為禍害社會之源,皆應棄之。而以無為治之,可使物各得其性命之情。
《天地》第十二:天地運作本於自然,人君之治亦應順天地自然無為之規律而行。欲得大道應滌除貪欲智巧之心,以「無心」求之。
《天道》第十三:自然規律運行不輟,萬物皆自動自為,聖人當順自然而行,與萬化同流,以無為治天下。
《天運》第十四:天地萬物無心運行而自動,唯有順應自然變化方能教化他人,禮儀法度應順時而變,不可拘泥守舊。
《刻意》第十五:天地之道淡然無極,恬淡、寂寞、虛無、無為乃道德修養之最高境域,養心之道貴在守神而勿失。
《繕性》第十六:人心之欲多非本真,求榮華者必喪己於物,故戒去性而從心。修治本性之要在於恬淡與智慧交相涵養,如此則可反情性而復其初。
《秋水》第十七:事物之大小、貴賤、是非等皆為相對,並無固定標準,以道觀之,萬物齊一,故應突破主觀之局限性與執著性,以開放的心靈觀照萬物。
《至樂》第十八:無為為至樂,而至樂者無樂。人生至樂在於超脫俗情欲望而內心恬和,面對生死應安時處順,隨任變化。
《達生》第十九:養生之關鍵在於養神,只有參透生死、拋棄名位、排除雜念、保持心地純樸專一方為通達生命之情。
《山木》第二十:人之處世,材與不材皆可致患,唯有清心寡欲,虛己無為,拋棄權位名利之思,乘道德以浮游,順乎天道自然,方可保生全身。
《田子方》第二十一:此篇內容較駁雜,主要有三。一批評儒家「明乎禮儀而陋於知人心」;二論「哀莫大於心死」;三論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藝術心態。
《知北遊》第二十二:此篇主要論「道」,道無所不在,但不可言說,不可聞見。體道之要在於精神凝聚,思慮專一。
雜篇十一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一切禍福,皆由心造,故心無利害之念,則物莫之能害。
《徐無鬼》第二十四:嗜欲、是非、名利等心理迷惑,致使人不能清靜無為順乎自然,解惑之方在於無知無為無言無求與遵循天道保持天性。
《則陽》第二十五:此篇言天下能歸於道,則可天下為公而息爭止亂,並兼涉宇宙起源及知識、語言之局限等問題。
《外物》第二十六:此篇言外物不可強求,謀慮智巧則傷自然之德,而應具寧靜心態,並兼論得意忘言之旨。
《寓言》第二十七:述《莊子》一書之語言特點──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讓王》第二十八:主旨在於闡述重生思想,以辭讓王位諸事明貴生之旨,以治身為本,以治天下為末。
《盜蹠》第二十九:借盜蹠之口抨擊儒家禮教規範及俗儒富貴顯達之觀念,主張保養自然之性情。
《說劍》第三十:記莊子勸止趙文王好劍之事。
《漁父》第三十一:主旨在於闡揚保真思想,並批評儒家禮樂人倫之觀念,宣導謹慎修身,保持本真,使人與物各還歸自然。
《列御寇》第三十二:本篇內容較為駁雜,主要在於闡述忘我的思想,反對雕琢矯飾,宣導純任自然。
《天下》第三十三:以道術分裂為方術之學術史觀,遍評先秦各家學派。
以上是《莊子》各篇的大旨,為了從總體上把握其思想,我們又可將《莊子》的主體思想概括為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第一,「道」論。「道」是《莊子》哲學的最高範疇,也是其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莊子》直接繼承了老子《道德經》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思想,也把「道」作為天地萬物產生的根源和依據,但「道」本身卻無形無相,不可聽聞感知。「道」的本性是自然,即自然而然,同時「道」又具有絕對性(「道」是產生天地萬物的唯一本原,而其自身卻自本自根)、永恆性(「道」自古長存、無始無終)、普遍性(「道」遍存於萬物之中)和無目的性(「道」無意志、不主宰支配萬物)等特徵。人們只有通過「心齋」、「坐忘」、「虛靜」、「凝神守一」等修養工夫才能與道體合一而把握大道,這時「道」就不僅是人對普遍的、永恆的宇宙發展規律的認知和體悟,而且內化為人的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第二,逍遙觀。逍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莊子》認為,人存在於天地之間,總會受到特定的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從主觀上講,人經常處於對名利、權位等的追逐之中,又常常處於以自我為中心的是非、對錯的糾纏之中;從客觀上講,人受到生死的時限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制約與束縛等。這些限制使人時刻處於一種關係網中而遭受到內在與外在的壓力,這也是人不自由的根源所在。人要獲得絕對的自由,只有通過「無己、無功、無名」的精神修養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使自身突破自我和社會的限制,從主客觀的關係網中超脫出來,從而達到「逍遙乎無何有之鄉」的精神自由。所以,《莊子》所說的逍遙,就是一種超越的、無拘無束的心靈自由狀態。
第三,超脫的生死觀。《莊子》對生死問題作了深刻的思考,其生死觀的根本目的就在於説明人們擺脫對死亡的恐懼而使人獲得自由。《莊子》從三個層次上探尋了超越生死的三種途徑:一是將生死歸結為「時」與「命」,即生死是時勢使然和命定的,不可改變,所以面對生死應「安時處順」;二是將生死看作是氣的聚散,氣聚則為生,氣散則為死,所以生死只是一種自然的變化;三是通過「心齋」、「坐忘」的修養工夫而與「道」合一,從而達到忘懷生死的超越境界。以上三個方面,都是讓人以一種超脫的心態看待和面對生死,從而擺脫世俗生死觀念的糾纏而獲得一種平和的心境。
第四,萬物齊一的平等觀。《莊子》認為,世間的是非爭論、萬物之間的差別,都是來自人的「成心」,都是人的一偏之見,如果從絕對的、超越的「道」的角度來看待萬物,則萬物都是齊一的和平等的,萬物無所謂好壞美醜,其間的一切差別都可消融在大道之中。所以《莊子》中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萬物「道通為一」,「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但是,《莊子》萬物齊一的平等觀,並不是要取消和抹煞萬物之間客觀存在的種種差別而齊同萬物,恰恰相反,它正是看到了萬事萬物存在的種種差異性,而以一種超越差別的觀點來觀察萬物,以此來確認萬事萬物存在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第五,無為反樸的社會觀。《莊子》的社會觀立足於對人類社會文明副作用的深刻反思,揭露和批判了人類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對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而儒家所宣導的道德仁義正是使人性墮落的根源,「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乎禽貪者器」(《徐無鬼》),儒家的仁義規範已經蛻化為統治者爭奪權力的工具,從而出現了「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胠篋》)的異化現象。正是基於此,《莊子》以其自然哲學為基礎,批判了君主制度的危害,在政治上宣導順應和保持人的自然本性的無為政治,並提出了「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馬蹄》)的至德之世的社會理想,而主張返歸於可以避免文明困擾的原始自然狀態。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管國興的圖書 |
 |
$ 493 ~ 522 | 影響中國文化的十大經典
作者:王月清、暴慶剛、管國興 出版社: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8-09-05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影響中國文化的十大經典
本書以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十大古籍為題,以此十大古籍的題解、源流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為切入點,詳細剖析了這些影響中國國民性格、國家風俗習慣,乃至歷史發展的重要古籍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互動關係。本書共分十章,一書一章,各章後還附有各古籍精華片段選讀及延伸書目推薦,有助於讀者深入淺出地把握這些平時難以全面閱讀的古籍之來源、演變歷史、基本結構及其對中國文化整體的深遠影響。
作者簡介:
王月清
一九六六年十月生,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著合著有《中國佛教倫理研究》、《中國哲學關鍵字》、《中國佛教通史》、《中國佛教藝術史》、《宗教與道德勸善》、《無神論與中國佛學》等。
暴慶剛
一九七六年二月生,哲學博士,南京大學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專著有《反思與重構:郭象〈莊子注〉研究》、《千古逍遙:莊子》;合著有《中國哲學關鍵字》、《影響中國文化的十大哲人》、《中國古代哲學經典》等。
管國興
一九六四年九月生,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祕書長,哲學博士。
TOP
章節試閱
第三章《莊子》
《莊子》一書,是莊子和他的門人及其後學所著,是戰國中期到秦漢之間道家莊周學派的文章總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將《莊子》與老子的《道德經》視為道家和道教的宗經寶典。《莊子》成書以來,以其深邃的義理、磅礴的氣勢、豐富的想像、超脫的境界影響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傳統文化,影響了儒家、佛教、道教等理論的發展。通常,人們將儒、釋、道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而正是《莊子》的出現,才使得道家發展成為與儒、釋鼎足而立的重要學派,使道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瞭解道家學說,...
《莊子》一書,是莊子和他的門人及其後學所著,是戰國中期到秦漢之間道家莊周學派的文章總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將《莊子》與老子的《道德經》視為道家和道教的宗經寶典。《莊子》成書以來,以其深邃的義理、磅礴的氣勢、豐富的想像、超脫的境界影響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傳統文化,影響了儒家、佛教、道教等理論的發展。通常,人們將儒、釋、道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而正是《莊子》的出現,才使得道家發展成為與儒、釋鼎足而立的重要學派,使道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瞭解道家學說,...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周易》
一、《周易》題解
二、易學今昔
三、《周易》與中國文化
第二章 《老子》
一、《老子》題解
二、《老子》源流
三、《老子》與中國文化
第三章 《莊子》
一、《莊子》題解
二、《莊子》源流
三、《莊子》與中國文化
第四章 《論語》
一、《論語》題解
二、《論語》源流
三、《論語》與中國文化
第五章《孟子》
一、《孟子》題解
二、《孟子》源流
三、《孟子》與中國文化
第六章 《大學》
一、《大學》題解
二、《大學》源流
三、《大學》與中國文化
第七章 《孝經》
一、《孝經...
一、《周易》題解
二、易學今昔
三、《周易》與中國文化
第二章 《老子》
一、《老子》題解
二、《老子》源流
三、《老子》與中國文化
第三章 《莊子》
一、《莊子》題解
二、《莊子》源流
三、《莊子》與中國文化
第四章 《論語》
一、《論語》題解
二、《論語》源流
三、《論語》與中國文化
第五章《孟子》
一、《孟子》題解
二、《孟子》源流
三、《孟子》與中國文化
第六章 《大學》
一、《大學》題解
二、《大學》源流
三、《大學》與中國文化
第七章 《孝經》
一、《孝經...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月清、暴慶剛、 管國興
- 出版社: 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8-09-05 ISBN/ISSN:978986388076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4頁 開數:18K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