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心理側寫師瑟巴斯欽・柏格曼驚悚系列
瑞典寫實小說、影集全球暢銷
瑞典寫實小說、影集全球暢銷
凡事都有儀式。他必須遵照儀式進行。規定就是規定。
殘忍至極的連續凶殺案在平靜的斯德哥爾摩掀起恐慌。死者全是女性,都在自家臥室以絲襪反綁,再被利刃割頸,卻沒有闖入的痕跡,犯人以近乎儀式般的精準手法行刑,現場完美到不留蛛絲馬跡,讓調查的「全國凶案特別調查組」到處碰壁……
心理醫師暨犯罪心理學家瑟巴斯欽・柏格曼想為自己如同災難般的混亂生活重建秩序,並藉機接近他女兒——瓦妮雅.李納,於是說服特調組組長讓他協助調查……結果卻令他毛骨悚然,因凶案的每一名死者都與他有關,而兇手的作案手法竟像多年前被他送進監牢的連續殺人狂:愛德華.海德。可是海德人在牢裡……時間迫在眉睫,而下一個被鎖定的對象,正是……
繼創下銷售佳績的《我不是兇手》後再度推出「瑟巴斯欽・柏格曼驚悚系列」續集。本書已改編成電視劇,全球熱播,好評如潮。
名人推薦
「精采刺激,高潮迭起,讓你一頁翻過一頁……最後轉折吊足讀者胃口!」——瑞典《Skaraborgs Allehanda早報》
「這書好得不像話,生猛刺激……我已經開始數日子期待下一本問世。」——瑞典《Värmlands Folkblad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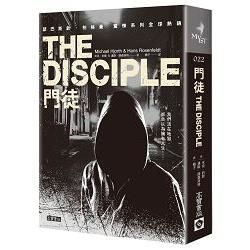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