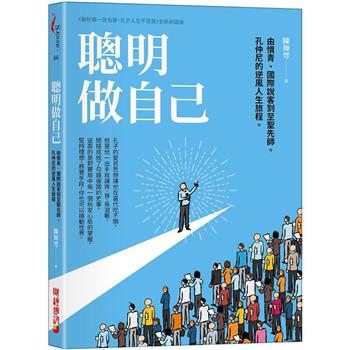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不確定的年代》 導論
一
加爾布雷斯的《不確定的年代》也可譯為《躊躇難決的時代》、《真相難明的時代》或者《變幻莫測的時代》。加爾布雷斯說,以過去一個世紀所確信不疑的觀念與今日面對問題所把握不定的情形相對照,我們到底是要容許政府干預還是信賴市場的力量?真是令人躊躇難決。他又說:在前一個世紀,資本家確信資本主義的成功、社會主義信徒確信社會主義的成功、帝國主義者確信殖民主義的成功,並且統治階級莫不了然他們所企圖的乃是執行統治。然而現在所有這些確信,幾已全然消失。看來人類所遭遇的問題實在複雜難明。他再又談至貨幣的興起與衰退,由希羅多德到凱恩斯,曾經歷無數次波折,時而歡欣、時而氣短,今昔相比,似乎尚未看出有個了局。是則把這時代稱為變幻莫測,誰曰不宜?
二
《不確定的年代》尚有一小標題,是為:。加爾布雷斯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上,闢頭即引證凱恩斯在其《一般理論》中所論及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及其影響力。然而就上面這小標題去看,也許加爾布雷斯思路的形成,還另有其來源。
在他到哈佛之前兩年,亦即1932年,哈佛鼎鼎大名的哲學教授懷海德即已出版了《觀念的探索》(Adventures of Ideas)一書。據稱這本書的名稱有兩個意義:一在探索觀念在促進人類慢慢趨向於文明所具有的影響;二在作者冒險嘗試組成一觀念的思索系統,藉以說明歷史事件的演變過程。
1950年哈佛大學另一馬克里安歷史教授布潤敦(McLean Professor of History, Crane Brinton)寫了另一本《觀念與人:西方思想故事》(Ideas and Men: The Story of Western Thought)的書。他這本書的目的也同樣要促使每個人盡一切努力去作他自己的思考與選擇,並且以此為原則。他曾引證懷海德的話,說:知識的歷史,就從事此種工作的任何人而言乃是「一項觀念的探索」。然而最最重要的任務,還在如何努力去尋求觀念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亦即:一面是哲學家、知識分子、思想家的觀念,而另一面則是擔當文化勞役的千千萬萬人的實際生活方式。
1977年加爾布雷斯的這本小標題為的書出版。這可以說是哈佛教授所寫的有關觀念及其影響的第三部書。它的範圍比起前兩種可能狹窄些,但有關的資料應該是更為豐富。如前面兩位一樣,加爾布雷斯認為時代的支配觀念即是指導人民與政府的那些觀念。這些觀念實有助於歷史之為歷史。試觀加爾布雷斯對觀念的處理方式也可以窺見出他們彼此之間一脈相連的思想路線。加爾布雷斯首先要討論的是人與觀念的問題,其次才是它們的影響或後果。首先是亞當.史密斯、李嘉圖、馬爾薩斯,其次才是他們的思想體系在英國、愛爾蘭,以及新世界所發生的衝擊。這即是說,先談經濟觀念史,然後再論經濟史。前幾章的初步安排即係如此,之後則又由人轉到後果,由觀念轉到制度。
三
加爾布雷斯的《不確定的年代》可以說畢竟還是一部經濟思想史,一部別開生面的經濟思想史。原來他寫這本書的動機乃是十分奇特的。他說哈佛教授習慣上得說他們對教學總是十分愛好,縱令教與學雙方都已感到極端地厭倦,但在口頭上卻依然要繼續表示萬分熱心。他說他愈來愈不願把這種欺騙行為延續下去,所以他想到退休。正當此時他被電視節目製作人邀請去上電視。於是他想一想:既然倦於教學,又何不嘗試一下廣大而無人際關係的電視觀眾呢?就是這樣促成了他寫出這一部別開生面的經濟思想史!
這本書如此的誕生,顯然是很別致的。說它別致,因為一開始它的對象並不是大學教授或大學研究生,而是電視機前的廣大群眾。因此,整本書寫來輕鬆愉快。雖然在本質上這是一本經濟思想史,裡面卻不可能有曲線、有圖解、有謎樣的數學方程式。換言之,這本書缺乏一般的學究氣味,而卻自有其特別的風格,特別的韻味。也即是說,這一本正正實實的經濟思想史,並不曾遵照傳統的規範,按照一般寫經濟思想史的寫法去寫。作者係以融合自傳、遊記、傳奇、諷刺、冷嘲、譏笑以及史話為一體的手法,寫出了他具有若干突出之處的歷史故事。
四
第一、加爾布雷斯反對所謂線型的歷史觀。何謂線型的歷史觀呢?他說: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我們總以為經過一段夠長的時間,人們不斷學習、事物不斷進步。引申言之,關於經濟學,有不少的人認為也像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一樣,滾著雪球下坡似的一天比一天繼續壯大。如果從亞當,史密斯數起,那麼李嘉圖比史密斯進步,接著約翰.彌勒改進了李嘉圖,馬歇爾又再改進了約翰.彌勒,到了現在,凱恩斯可謂登峰造極,而再下一步似乎正等待著一位特具經濟分析能力的人物出現。
這種觀點即是馬克.溥勞(Mark Blaug)所謂絕對主義者的觀點。他在《回顧中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一書中,把經濟思想史分為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兩種。絕對主義者必須集中觀點在問題嚴格的知識發展上,把這個視為一不斷由錯誤到真理的旅程。反之,相對主義者,按照他的解釋,則是把過去發生的每一單獨的理論或多或少都視為當時情境的忠實表現和反映。他並且認為相對主義者不可能把不同時代的理論,按照好壞分成等級,而絕對主義者卻不得不如此做。
這種絕對主義所關注的乃是邏輯錯誤和分析缺口,而不涉及當代事務。這類經濟思想史顯然不是加爾布雷期的興趣所在。這位活躍於政壇,熱心社會運動的人物,何能忘情於社會發展以及國內外事務的演變。他無法把他自己約束在舊日所謂考據,或英國哲人培根所謂「學習的蜘蛛網」的工作範圍之內。按照培根的說法,「學習的螂蛛網」也只能在問題的線索與作品的細微處令人欽佩,然而缺乏內容或益處。關於這種絕對主義或線型的歷史觀,加爾布雷斯特別寫了一章貨幣的興衰史,說明它的前途未可樂觀!
五
第二、加爾布雷斯喜歡從他個人的立足點出發,這即是說,他喜歡把他自己攪和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之中。這種寫法是傳統的經濟思想史家或任何史家所極力要去避免的。理由是這牽涉著個人的立場,因而不可能客觀;不客觀即等於不科學;不科學在經濟分析看來將是何等嚴重的事!可是,反之我們可能犧牲掉活潑生動的描述,以及歷史事件有如擺在眼前那樣的具體重現。
由於他的這種寫法,凡是唸加爾布雷斯這本書的人稍微留心,即可不必去唸他所寫的《蘇格蘭人》與《大使的日記》或席爾克(Leonard Silk)所寫的《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s)便可以得著他身世的全貌。
從圈地運動(或稱清地運動)引起蘇格蘭人移向加拿大說起,原始加爾有雷斯家族隨著這潮流也由蘇格蘭西部阿該爾郡(Angyllshire)移居加拿人離伊利湖塔爾波堤港不過5.6英里的農莊,稱為「舊家院」(The Old Homestead)的地方。第一次大戰之後,加爾布雷斯在安蒂麗阿西部已長大成人。他的父親十分關心政治,曾因反對戰爭遭到地方人士的責難。但在1918年以後,他的立場獲得了大家的諒解。1931年加爾布雷斯由安蒂麗阿農學院轉到柏克萊加州大學,同時也從農學系轉到經濟系。1934年春天他在加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即受聘為哈佛大學的講師。不久,他又被任為文司洛普宿舍(The Winthrop House)的導師,而且在這裡結識了甘家兄弟(即甘迺迪總統兄弟)。除了1937至1938年去英國劍橋大學,1940至48年大部分時間供職政府,以及1961至63年充任駐印度大使外,他主要的歲月是在哈佛擔任教學工作。
在加爾布雷斯這本書上,除了上面這些自傳式的材料外,我們再來看他如何把他自己介入到他所謂「第一位經濟學家,最偉大的蘇格蘭人——亞當.史密斯」的討論之中。在1973年亞當.史密斯誕生二百五十週年紀念時,他曾借機伴同英國賈拉漢首相(那時是財政部長)去朝拜史密斯的故鄉客開第。論到衛布倫《有閒階級論》中炫耀式的消費時,他談起甘迺迪總統如何陪著印度總理尼赫魯去參觀羅德島新港的富豪人家。那時我們作者當然參與其間,並且很高興地聽見這位總理提到美國的富裕社會。
然而他與凱恩斯的會面最為有趣。此事發生在華盛頓,當時他負責著物價管制。1937至38年去劍橋時,他打算能親自在凱恩斯門下受教,可惜那時凱恩斯患了心臟病,全年不能到校。一天他未經預先告知欲突然駕臨加爾布雷斯華盛頓辦公處的外室,交下一篇文章。加爾布雷斯覺得這彷如是聖彼得本人公然降臨到某一教區牧師的面前。此外,讀這本書的人還會覺得,好像作者的影子或那樣一個自我始終隱隱約約浮現在整本書的敘述後面。
六
第三、這本小標題為的書並不曾像上面所指稱的相對主義那樣,把過去每一單獨的理論視為當代社會情況的表現和反映。它也不曾把思想與歷史混為一體,搞任何一種所謂的史觀。我們甚至可以說,它並未曾嚴格的企圖拿歷史來說明觀念,或拿觀念來說明歷史。而毋寧是作者自己說的:先談經濟觀念的歷史,而後經濟史。
所以開頭第一章係檢討所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觀念,之後才接著描寫高度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富貴人家令人搖頭的風尚與品德。另一面則有馬克思的異議,而後指出世界上除了資本主義社會外尚有其他的社會,以及由資本主義所培育出來的殖民主義。繼之,他談到列寧如何加強以農民為基礎的群眾組織,如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混亂,如何終於達成了所謂的赤色革命,而使舊日帝俄以土地為依據的貴族階級歸於幻滅。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使往日的確信不疑歸於消失。貴族與資本家不再感覺他們的地位是安全的,而社會主義的信徒對他們的信心也發生了動搖。不確定的時代於焉開始!加爾布雷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戰,或者我們毋寧說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由此引出了有關貨幣的一段插曲,因而導致所謂「凱恩斯革命」的討論。換言之,這無異是對凱恩斯的觀念及其所引起的後果加以評述。
七
總結言之,加爾布雷斯並不是一位為學術思想而作學問的人。他關心世局,所以反對軍備競賽,不滿意近代的企業組合,尤其憂心第三世界中所繼續存在著的貧困現象。他嘲笑美國新港、法國里維耶拉的富貴人家;諷刺西方社會的酒、色、財、氣——比如說:大學生的酒、牧師的色、暴發戶的財、以及貧苦大眾的氣。不過加爾布雷斯畢竟有他加爾布雷斯的偏見——由他個人的偏愛所產生的偏見,儘管過去一時也曾受過激烈分子的誘惑,他畢竟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關於他對馬克思及列寧在觀念上的若干批評,我們在這裡無暇加以細說。單就蘇聯在東歐施行赤色殖民政策而論,他的斷語仍是值得我們喝彩的。他無異暗示這種統治無法持久,因為他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經過清洗以後都是白的」。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約翰.加爾布雷的圖書 |
 |
$ 170 ~ 308 | 不確定的年代
作者:約翰.加爾布雷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4-05-01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布雷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不確定的年代
在過去兩百年間,世界從充滿確信到游移難定,近代經濟學家與社會哲學家的觀念在其中扮演了主導及決定的角色。本書追溯這些觀念,舉其人物,撮其理論,述其後果,觀其相關時代事件,縱橫經緯。上起古典資本主義先知亞當‧史密斯,中經馬列社會主義,下及凱恩斯、冷戰年、代第三世界、武器競賽,層次廣被。作者素負盛名,說理清通、文字曉暢,是經濟學者作的異數。
此書的誕生,顯然是很別致的。說它別致,因為一開始它的對象並不是大學教授或大學研究生,而是電視機前的廣大群眾。因此本書寫來輕鬆愉快。雖然在本質上言是一本經濟思相史,裡面卻不可能有曲線、圖解、謎樣的數學方程式。作者以合自傳、遊記、諷刺、冷嘲、以史話為一體的手法,寫出了他具有若干突出之處的經濟歷史故事。
推薦序
《不確定的年代》 導論
一
加爾布雷斯的《不確定的年代》也可譯為《躊躇難決的時代》、《真相難明的時代》或者《變幻莫測的時代》。加爾布雷斯說,以過去一個世紀所確信不疑的觀念與今日面對問題所把握不定的情形相對照,我們到底是要容許政府干預還是信賴市場的力量?真是令人躊躇難決。他又說:在前一個世紀,資本家確信資本主義的成功、社會主義信徒確信社會主義的成功、帝國主義者確信殖民主義的成功,並且統治階級莫不了然他們所企圖的乃是執行統治。然而現在所有這些確信,幾已全然消失。看來人類所遭遇的問題實在複雜難明。他再又...
一
加爾布雷斯的《不確定的年代》也可譯為《躊躇難決的時代》、《真相難明的時代》或者《變幻莫測的時代》。加爾布雷斯說,以過去一個世紀所確信不疑的觀念與今日面對問題所把握不定的情形相對照,我們到底是要容許政府干預還是信賴市場的力量?真是令人躊躇難決。他又說:在前一個世紀,資本家確信資本主義的成功、社會主義信徒確信社會主義的成功、帝國主義者確信殖民主義的成功,並且統治階級莫不了然他們所企圖的乃是執行統治。然而現在所有這些確信,幾已全然消失。看來人類所遭遇的問題實在複雜難明。他再又...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約翰.加爾布雷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4-05-01 ISBN/ISSN:9789571311586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經濟
|
 布雷是位於比利時林堡省部的一座城市,人口14,503人。
布雷是位於比利時林堡省部的一座城市,人口14,50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