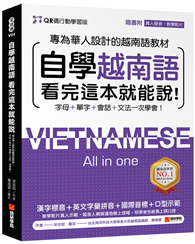第一章 將理性民主化
這個世界向來不太對勁。經濟危機、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債務危機、合法化危機、國際危機和福利國家危機,種種危機接踵而來。工作超載的政府得努力應付無法控制的社會。很少人認為政府會成功,因為公共政策或計畫獲得成效的機會令人悲觀。另一方面,人們不信任市場,愈來愈多人拒絕物質報酬,不管是由於愛好後工業生活風格,或是受到基本教義宗教的啟示。前馬克思主義社會如今看來和其他地方一樣有麻煩。
在這裡,我想對世界當前某些政治疾病做出診斷,想出治療的方法。我推斷這許多的疾病,和曾經令人信服、如今仍然四處可見的理性(rationality)形式逐漸衰頹大有關係。治療之法是那些以理性為訴求的個人行動、政治機構、政策實踐和社會科學都要下猛藥,大量服用我所說的談論式民主。
診斷書
個人的政治行為、政府的政策、政治系統的結構以及研究這些現象的政治學家所持的假設和策略,或多或少都是理性的。啟蒙時期以來幾個世紀,理性要求兩件事。第一、有效的工具性行動。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意指設計、選擇並採取夠好的手段,以達成某些清楚明白的目的之能力。第二,關於事實、甚至價值和道德的理論及信念,應該參照客觀的標準,這些標準適用於每一個人,人人也都可以取用。此後啟蒙理性的第二個面向,通常被稱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
工具理性和客觀主義攜手並行。前者決定理性行為,後者影響理性信仰和道德。兩者進而為可能成為理性個人者提供完整的指引。在社會生活中,客觀主義,本身即為為一種工具理性(就其所在社會系統的目標來看),黏著並協調大量工具理性主義者的行動。工具理性和客觀主義一起像魔法一樣變出一個潔淨有秩序的世界,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在這個世界裡蒸蒸日上。然而,我要說,現代性在政體、經濟和社會中,也提供了很不一樣的機會。
工具理性也許比客觀主義還要普遍。的確,經濟學家就假定工具理性捕捉了所有人類行為的本質,也有愈來愈多政治學家,甚至少數社會學家做如是觀。多數國際關係的分析家相信工具理性足以掌握外交政策行為的全貌。政府行動的顧問和批評者,包括專業政策分析者,都希望公共政策能透過工具理性追求某些明確的目標。
然而這種理性並未進一步在政治分析和政治生活中清楚表現出來,這我們留在後頭的章節解釋。以自由批評為前提,工具理性從其根本強化了自由主義多元政治(liberal polyarchy),那是西方主要的政治系統(見第二章)。工具理性也鑲嵌於許多政治學的實踐和方法之中(見第八章)。
反對這種理性的理由如下:
1.工具理性摧毀了人類交往時更友善、自發、平等和本質上更有意義的面向。這種批評耳熟能詳。韋伯(Max Weber)於世紀之交聲稱工具理性(連同客觀的規則系統)提供官僚體制正當化和組織的原則。韋伯也認為官僚化中展現的工具理性預示了人類存在於「鐵籠」(iron cage)的命運。晚近,哈伯瑪斯(Jugen Habermas)則將韋伯的推斷從官僚體制擴展到文化及社會互動中,而提出「生活世界」(lifeworld)已被「殖民化」的看法。在這個殖民世界裡,行政機構、宗教儀式、影響力和技術專業知識的掌握,都為私利或政治權力服務。行政官員、行銷顧問、警察、社會工作人員、律師、醫師、法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都是入侵過程的先鋒,而這種過程曾經由一般人民來建構與帶領的。此外,在一個工具理性的世界,個人形同經濟人—就像一具主體性貧乏、沒有自我和社群意識的計算機。
2.工具理性是反民主的。這也是韋伯的觀點,因為官僚化要求政治權力的集中。工具理性只有在自由批評的條件下運行,在波普(Popper, 1966)所謂「開放社會」(open society)下的「點滴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中,這種趨勢才會減緩。然而,它對民主的威脅仍然存在於開放社會之中,特別在現實世界中最接近開放社會的體制,例如自由主義多元政治,更是如此。因為社會工程仍須由某些人(或團體)來完成,這些人雖是民選,仍須對他人揮舞權力。因此在開放社會裡,對理性的渴望和平等原則之間,關係仍然緊張。對民主的另一個威脅,是個人簡化為計算機後,很容易被極權主義許諾人們將恢復其生存之意義的訴求所迷惑。
3.工具理性壓制個體。一方面,工具理性給我們權力和技術,來創造人類自由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為了上面這個目的,工具理性卻壓抑了讓人類主體得以瞭解這種自由的愉悅和創造力。這種弔詭即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所謂的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他們因此認為人們無處可逃(也許藝術表現例外)。當代女性主義者對壓抑做出些許不同但相關的陳述,例如,她們認為,複製科技和人口控制的意識形態,讓技術專家能夠控制女性的身體。如此一來,女人對自己繁殖力的控制權就旁落到他人手裡(Diamond, 1988)。
4.工具理性及其附身的政治制度在遭遇複雜的社會問題時是無效的。工具理性附隨著一種分析判斷,即複雜的現象,最好將之分解成部分來理解。然後逐一瞭解這些部分,並工具性地解決這些部份當中有問題的面向。的確,就是這種分解形成了官僚體制分工的組織原則。職此,我在此的批評是反韋伯的;韋伯預言組織將呈現官僚化,正是因為它的理性能有效處理更為複雜的問題。我將在第三章針對複雜性發展我反韋伯的論點。
5.工具理性無法做出有效且適切的政策分析。這項批評主要是針對跨學門的公共政策分析,當然,和前四項比起來,這項批評不見得適用於全世界。多數情況下,這個領域的主宰觀念仍是:公共政策應該適當地、工具性地干預社會、經濟和政體。如果以上一至四項均成立,那麼主流政策分析者就是暴政或無效公共行動的幫凶。第六章將會根據以上討論發展出對政策分析的批評。
6.工具理性引導社會科學採取不適當且無效的工具和方法。第八章裡我們將批評政治學中廣泛採用的方法—民意調查。雖然乍看之下,這種憂心似乎目光偏狹,僅適用於政治學,我卻必須指出,廣泛使用和接受這種工具,結果卻幽微地強化了某些主流政治秩序裡令人討厭的面向。
客觀主義,除了這六項與工具理性有共謀關係的指控以外,本身可能還有三項罪狀。
1.客觀主義來自它所崇拜的科學的錯誤解釋。後經驗主義(postempiricist)科學哲學已經指出,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研究的邏輯」並不存在。這種規則碰到科學史都被摧毀了,特別在與科學史某些重大事件相遇的時候(見例如 Kuhn, 1970b, p. 200; Burian, 1977; MacIntyre, 1977, p. 468)。不同理論和研究計畫抗衡的結果,挑戰了客觀主義的標準。
2.客觀主義是壓制性的。它將自己的標準和實踐強置於與其觀點不同的傳統和生活方式之上,不管是以它自己的論證或者以武力。犧牲者包括原住民文化,非科學的醫療實踐,不同的認識論例如女性主義(更誇張的說法,請見Feyerabend, 1987)。有個死硬派客觀主義甚至為古代雅典使用「某種帝國主義」征服了「部落主義的排他性和自足」而額首稱慶(Popper, 1966, p. 181)。
3.客觀主義妨礙了政治學和政治的進步。在第十章裡,我會論證,由於政治世界以純粹客觀的認知理性為師,所以它和防衛性的政治學及更一般性的真實政治反思,是格格不入的。
治療
如果這些反對工具理性和客觀理性的說法成立,至少有三種方法可以逃離他們的魔掌。兩種要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理性,第三種則認為理性已經病入膏肓。
這三種裡面最不基進的一種是,保留並重申工具理性和客觀理性的基本戒律,但開放修正和補充。這方面最知名的努力也許可以在波普(Popper, 1966, 1972a)的作品中發現。波普認為社會組織中最有效的解決問題方式,不是中央計畫或韋伯式的官僚,而是一個開放社會,在其中,工具理性主義者能夠自由批評他人的設計。開放社會本身是仿照科學社群的模型而打造的,在科學社群裡面,客觀主義者可以自由批評他人的理論。我會在第二章處理波普的說法。海耶克(Von Hayek, 例如1979)為市場做了一個比較︰市場仰賴價格訊號(而非言詞的溝通),不分層級,調和大量工具理性主義者的所作所為。第三章將介紹和批評其他幾種延伸形式的工具理性。
最基進的逃離方式是否認人類理性,將其適用範圍限制在特定領域裡,甚至全盤否認。我們可從許多知識立場來否定理性。有些自由市場的提倡者從海耶克的論點出發,認為有了看不見的手,就不必大規模的計畫和計算(見例如Friedman and Friedman, 1979, pp. 6-9)。那些賞識去中心化政治過程的人,認為市場內的互動能完全取代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內容分析(例如Lindblom and Cohen, 1979)。許多對生態敏感而反對工業社會的人,相信人類宰制自然世界(及其他人類)這種工具理性的惡果,惟有轉向在人類之間以及人類與自然間,建立精神與直覺上的關係,才得以克服(例如Spretnak, 1986)。而基督教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則推崇大不相同的精神價值(spirituality),人們根據超驗的神所給予的啟示,尋求救贖。
在此,不只工具理性和客觀理性遭人物議,還有供稱能夠提供認知保證給任何行動或立場的那種理性也無法倖免。因此,善疑的歐陸哲學家例如傅柯(Foucault, 1980)在所謂的理性論述裡,只見到各種微妙的欺騙和壓制。政治理論和,更廣泛的,思想體系(或他所稱的「論述」)本質上就是各種規訓其追隨者的監牢。人們只有浪漫地投入經驗的美學面向,才能逃脫這種束縛。傅柯無情地抨擊過去和當前的社會形構、社會科學家的共謀,及其理性。但他最終陷入全面否定的困境,卻提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後現代主義者如李歐塔(Lyotard, 1984),解構主義者如德希達(Derrida, 1976)和認識論無政府主義者如費若本(Feyerabend, 1975, 1978, 1987),和傅柯比起來,雖然同是相對主義者,但嬉遊的成份較重,而不會義無反顧,一路否定到底。這種「反理論家」或「萬能破壞份子」目前所在多有(Skinner, 1985, pp. 12-13)。他們多數是「多疑的大陸性格,帶著牽強的觀念和不知怎麼唸的名字」(Ball, 1987a, p. 2)。但是羅逖(Rorty, 1979)指出,這種懷疑主義已經來到英美學術界。羅逖認為所有的知識主張,包括長期以來試圖判斷這些主張的哲學本身,都受限於時間、空間、文化與經驗。
除了再次肯定或完全拋棄工具理性和客觀理性,我們還有第三種選擇,那就是仔細注意理性的意涵。在此我將提出論證,反對現代世界中工具理性和客觀理性的霸權(hegemony)。工具理性常伴我們左右,但是它應該限制在一個比目前更小的領域中。客觀主義則可以完全省略。騰出來的空間,可由一種完全不同的理性來代替,那是談論式和民主的理性,不是工具式和威權的理性。這種理性可以回答「萬能破壞份子」的指控。這種談論式和民主的理性足以管制殘存的工具理性,並取代客觀主義。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約翰.卓策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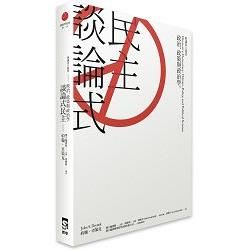 |
$ 210 ~ 428 | 談論式民主-政治、政策與政治學(國編主編,群學出版)
作者:約翰.卓策克(John S. Dryzek) / 譯者:黃維明 出版社:群學 出版日期:2009-12-3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84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談論式民主
民主的漂泊與曙光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代議民主的興起,與爾後主權國家的蓬勃發展密不可分。但從後見之明來看,這段距離我們猶不遙遠的史實所顯露的,卻不盡然是民主勝利的光輝,更是它曲折的命運:就在我們成為民主價值之忠實信徒的這個時候,現代國家以工具理性作為標竿的政經體系與治理模式,竟已走到了一個自我失控的歷史瓶頸,從而使得民主的社會實踐變得十分困難。
本書企圖於此歷史逆境中,扭轉民主的頹勢。作者為了重建民主的理論基礎,從批判理論出發,並吸納漢娜鄂蘭與社群主義的相關論述,提出一個銜接當代溝通理性與古典政治概念的談論式民主模式。這種談論式民主既是扭轉工具理性與客觀主義之迷途的正確指引,
也是化解政治困頓與民主危機的不二法門。凡是對於民主的前程懷有憧憬的讀者,將可在本書中親眼目睹實踐理性的曙光。
――摘編自本書曾國祥序〈民主的奧德賽〉
作者簡介:
約翰.卓策克(John S. Dryzek)
奧勒岡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及系主任著有《理性的生態學:環境選擇的政治經濟學》(Rational Ecolog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Choice, 1987)。
譯者簡介:
黃維明
台大法律系畢業,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碩士。為資深自由工作者,作品散見各處,譯著十餘種。現於某大學攻讀博士,進行台灣的環境論述與公共領域研究。不寫論文時,他喜歡流連在山林裡,嘗試以文字和影像守望自然。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將理性民主化這個世界向來不太對勁。經濟危機、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債務危機、合法化危機、國際危機和福利國家危機,種種危機接踵而來。工作超載的政府得努力應付無法控制的社會。很少人認為政府會成功,因為公共政策或計畫獲得成效的機會令人悲觀。另一方面,人們不信任市場,愈來愈多人拒絕物質報酬,不管是由於愛好後工業生活風格,或是受到基本教義宗教的啟示。前馬克思主義社會如今看來和其他地方一樣有麻煩。 在這裡,我想對世界當前某些政治疾病做出診斷,想出治療的方法。我推斷這許多的疾病,和曾經令人信服、如今仍然四...
»看全部
目錄
台灣版序:民主的奧德賽 / 曾國祥
原文版序
第一篇 導論
第1章 將理性民主化
第二篇 政治制度
第2章 談論設計
第3章 複雜性
第4章 國際談論設計 / 與蘇珊‧韓特(Susan Hunter)合著
第三篇 公共政策
第6章 民主的政策科學
第7章 政策的企圖心 / 與布來恩‧瑞普雷(Brian Ripley)合著)
第四篇 政治科學
第8章 對政治人的錯估
第9章 政治人(男性與女性)的測量
第10章 進步與理性
第五篇 結論
第11章 擴大民主
註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原文版序
第一篇 導論
第1章 將理性民主化
第二篇 政治制度
第2章 談論設計
第3章 複雜性
第4章 國際談論設計 / 與蘇珊‧韓特(Susan Hunter)合著
第三篇 公共政策
第6章 民主的政策科學
第7章 政策的企圖心 / 與布來恩‧瑞普雷(Brian Ripley)合著)
第四篇 政治科學
第8章 對政治人的錯估
第9章 政治人(男性與女性)的測量
第10章 進步與理性
第五篇 結論
第11章 擴大民主
註釋
參考文獻
索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約翰.卓策克 譯者: 黃維明
- 出版社: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ISBN/ISSN:9789866525216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