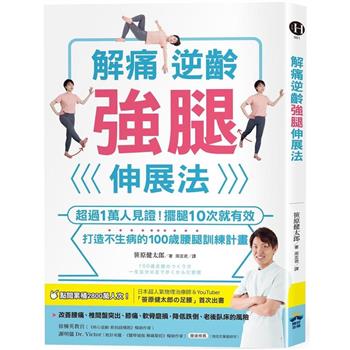推薦序1
歡迎來到債多不愁的世界
「如果你欠銀行一百萬,你的命運掌握在銀行手中;如果你欠銀行一百億,銀行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
這句話,原本是一則古老的笑話,很不幸的,這則笑話今天變成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夢魘!
衍生性金融商品,與資本主義的瘋狂,造成各種光怪陸離的金融怪象。這怪象如今已經不再是華爾街富豪們專屬的遊戲,就算你這輩子不碰投資,它還是會透過通貨膨脹,威脅你的存款安全,傷害你的工作機會,影響你的人生。每個人都必須要徹底地了解現代金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才能在未來不安定的年代中趨吉避凶。
作者Lanchester是一名小說家、記者。在這本書中,用幽默的比喻與故事,精確地描述了今天這些艱深的金融把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於毫無金融知識基礎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是絕佳的入門。
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全球債市危機不但沒有被金融專家解除,相反的,還像難纏的癌症一般,轉移到過去被視為最安全的富裕國家公債上。要徹底解決這場債市災難,恐怕還需要熬上非常、非常久的歲月。
債市問題會如此難解,原因就在於:債務與財富,是完全一體兩面的事。銀行有多少的存款,就會發放出接近等量的債務。當人們致力消除債務時,就表示世界上另一處存款,也會同時消失。如果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擁有大量存款,沒有債務,那只會導致兩件事發生:第一,銀行倒閉,第二,存款變廢紙,擁有糧食的,才是真正富人。
正因為如此,全球債務在人類滅亡前,都很難消失,也不會因人們努力而大幅減少。它會透過通膨,金融危機的形式,偷偷消滅財富,達到新的均衡。當人們自以為創造神奇的高經濟成長,獲取財富時,實際上大多是扭曲風險,濫用信用餵養出新的債務怪獸。
你我都不可能像本書最後一章的總結──喊一聲「夠了」就心滿意足。如何判別手中的財富,是否會突然變成有毒資產,提防自己遇到下一個金融騙子,已經是現代人生存的必備知識。這本書讀完之後,你將會對全球金融現況,有全新的認知!
林洸興
推薦序2
戴起鋼盔,衝向風險的槍林彈雨之後
《大債時代》是一本討論全球債市危機的專書,讓讀者瞭解危機發生的原委。但這本書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作者對這次事件的精闢分析。
許多分析債市危機的書,大多將矛頭指向不負責任的金融業者,或是管制失當的金融體系。但本書作者在最後一章直接點出了關鍵:「信用與資產泡沫,沒有大家的加入,不會無端發生。」換言之,我們,正是禍首。
為什麼?
銀行與金融機構為什麼要無止盡的追求獲利?就算它們很清楚,自己在現代經濟體系位居樞紐位置,應小心維持營運上的順暢。但在金融海嘯前,歐美銀行卻不斷擴增槓桿比率,研發出各種艱深難懂的衍生金融工具,以迎接更大的風險,做為更多獲利的基礎。它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有壓力。這些銀行與金融業者,大多是股東持有的上市公司。有哪位股東不要求公司營運成長、擴增獲利?想像一下,當別的銀行全都在這樣賺錢時,你是一位保守的銀行CEO,跟股東說,「這樣賺錢,恐怕不太好」,你認為自己能否保住職位?
不論何種產業,我們都在追求不斷的獲利,不斷的成長。銀行與金融業者在這樣的社會期待下,戴起鋼盔,衝向風險的槍林彈雨。當它們真的中彈倒下時,我們才會去想:或許,它們真不該向前衝。
在這本書裡,作者用非常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了這場危機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譬如,作者透過一份假想的資產負債表,向外行的讀者解釋,為什麼今天的銀行在本質上是一門高槓桿的生意。從這裡,再接著導引讀者看到,我們的銀行愈來愈會賺錢,不是因為他們有任何進步,而只是因為他們賭很大──下了更大的賭注,將槓桿比一路向上拉。作者也讓我們看見,金融業者如何藉由複雜的財務工程,將本質是「次級」貸款者的房貸,變成AAA 級的債券工具。
心中「不知足」的這把火
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我們不僅如此要求企業,也這樣要求自己。我們希望自己的收入不斷成長,不斷的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追求下一份更高的薪水、更好的享受。快樂永遠是下一次加薪,下一次旅行,下一次購物。我們從不滿足於自己已經所有的。
我們的整個社會,都全神灌注在「金錢至上」的唯一理念中。有了錢,還要更有錢。賺了錢,還要賺更多。這,就是引起全球債市危機的背景心態。這不是金融業才有的心態,這是受到這次債市危機波及的國家,其社會與國民的共同心態。
馬克吐溫曾說過,「缺錢是萬惡淵藪(The lack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現代已開發國家的多數人民,已經享有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富足。但幾乎每一個人都仍在追求更多的收入,與更好的物質享受。我們其實並不缺錢,我們只是認為自己錢不夠多。
想像一下,有一個人在四、五十歲的年紀,有一天突然心臟病發作。雖然事後幸運地復原了,但發作那一霎那心痛如刀剮,讓他以為自己就要離開人世的瞬間,卻讓他看清了人生的目的。從此以後,他過著更健康的生活,更珍惜與家人與朋友相處的時光,更知道拿一些時間來做自己覺得真正重要的事。一次健康上的小打擊,卻讓他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快樂踏實。
作者將這次的債市危機,比擬為人生中的這麼一次心臟病。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追求,已經讓許多人忘記經濟的目的是要帶給人們更快樂的生活,而不是永無止盡的壓力。
這次,是一個反思的機會。日後人類經濟會如何發展,有很大一部份,將取決於我們在這次「心臟病發作」後,做了那些改變。不知足,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不知足,卻也可以是貪婪的委婉說法。就像一把火,能照亮大千世界,也可以焚燬廣廈高樓。我們如何處理心中不知足的這把火,將決定它究竟是好用的工具,或是兇猛的禍害。
綠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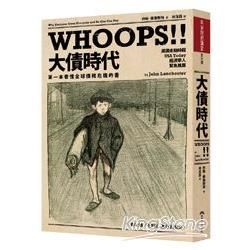
 共
共  2012/08/14
2012/08/14 2012/02/01
201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