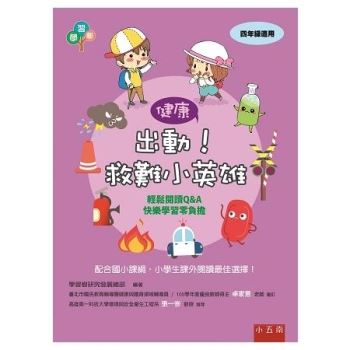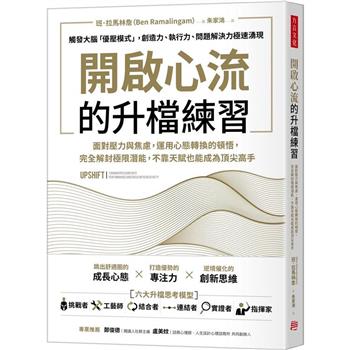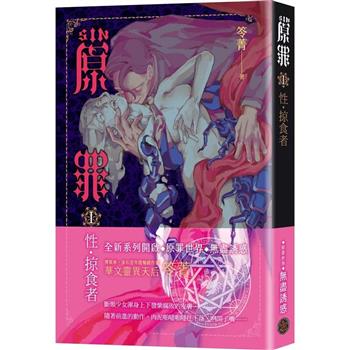妳說妳是我失蹤十年的女兒,
如果是,妳為什麼一點都沒長大?
如果不是,妳為什麼擁有那些回憶?
★ 英國水石書店 4.8顆星超高評價
★ 亞馬遜網路書店 4顆星超高評價
★ 英國心理懸疑小說的亮眼新聲醞釀二十年的初試啼聲之作
★ 英國Orion出版社以六位數英鎊重金簽下
★ 讀者大力推薦:「此書令人坐立難安又引人入勝、媲美S. J. 華森的《別相信任何人》和吉莉安.弗琳的《控制》。」
★ 本書敘事流暢、節奏緊湊,全書衝突不斷,張力十足,無論是女主角內心理性與思念的掙扎、或兩位母親面對著一個似乎有兩個靈魂的女兒、到最後令人震撼的結局,作者都刻畫得絲絲入扣,也頗有與讀者鬥智的味道。
★ 作者關懷的議題深刻有如《母性》和《贖罪》,在心理懸疑小說中加入「輪迴轉世」此一玄/懸而未決的元素更是前所未見。
貝絲十歲的女兒愛咪於千禧年前夕與好友出遊,卻神祕失蹤,貝絲的生活從此變調,她恨自己與丈夫失職、恨女兒的玩伴粗心大意、更恨身分不明的加害人,十年來貝絲對女兒的失蹤始終耿耿於懷,用盡一切方法探尋事實真相。
愛咪消失滿十周年之際,一位名叫莉比的單親媽媽帶著女兒愛絲玫來找貝絲,聲稱愛絲玫是愛咪的輪迴轉世,貝絲對此超乎常理的論調嗤之以鼻,因為愛絲玫還是個十歲小女生的模樣,但貝絲卻逐漸發現愛絲玫知道許多只有愛咪才有可能知道的回憶細節:她最愛的玩偶叫什麼、早餐愛吃什麼、還有在哪裡偷偷刻了自己的名字。
貝絲在理智與對女兒的思念間掙扎,她無法控制地感到重為人母的喜悅,卻又開始懷疑是否這一切都有幕後黑手在操弄,是不是莉比覬覦她豐厚的贍養費以及尋找愛咪的懸賞金,才支使女兒演了一齣完美的戲?但莉比和愛絲玫又是從哪裡獲知那些回憶細節?該不會她的前夫、她的密友也都牽涉其中?而最讓貝絲感到不安的,莫過於愛絲玫確定愛咪已遇害,但卻始終想不起愛咪的遇害經過和葬身之處……
當理智崩解、思念潰堤,唯一的出路是挖掘真相,豈知真相如排山倒海般湧出、黑暗得令人無法直視。
關於失去與失而復得、
關於原諒的可能與不可能。
受傷最深的,是不是就最無辜?
★更多好評★
一本簡潔又扣人心弦的處女作。作者的寫作風格獨特,將角色與場景刻畫得栩栩如生。──« We Love This Book》 雜誌
隨著情節開展,秘密逐一浮現,書中角色也並非你原先所想,讓你渴望知道結局。這本書非讀不可!
──《Irish Examiner》 雜誌
一開始讀之後就無法放下。羅伯•派特曼在本書中展現了令人動容的文字天分。
──愛爾蘭 《Woman's Way》 雜誌
這本書像有魔咒一般,讓讀者不停翻動書頁。
──英國讀者Anne
《兩個靈魂的女孩》是一本驚人的處女作,此書令人坐立難安又引人入勝、媲美S. J. 華森的《別相信任何人》和吉莉安.弗琳的《控制》。
──讀者Zarina於Goodreads網站書評
作者簡介:
羅伯•派特曼
英國懸疑小說的新聲
派特曼在英國長大,畢業於英國華威大學歷史系。他曾在旅行社、夜店、廣告公司工作,但一直都夢想著當一名作家。«兩個靈魂的女孩»是他的第一本小說,但旋即被英國Orion出版社重金簽下。他對以下東西感興趣:歷史、心理學、音樂、網球、公園、游泳、自行車、書、以及你們的讀後感!
譯者簡介:
蘇瑩文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任職外國駐華機構及外商公司十餘年,現專職英、法文筆譯與口譯。譯有《魔鬼遊戲》、《再見寶貝,再見》等書。
章節試閱
兩個靈魂的女孩
有時,我會看到她坐在旋轉木馬上的模糊身影,聽見伴隨溜滑梯嘎吱響的咯咯笑聲。當然,其實她根本不在。溜滑梯、鞦韆也全都不見了。議會決定拆掉搖搖晃晃的蹺蹺板和旋轉木馬,取而代之的是新穎的遊樂設施,此外,他們也把遊樂場遷移到公園另一側的咖啡座旁。現在,家長可以在孩子盪鞦韆、玩沙子或轉圈圈時,邊聊天邊享用卡布奇諾。
但是,他們奪走了我最後一次看到愛咪的地點。
從前的遊樂場──那個愛咪去過,而且鍾愛的樂園,如今成了一片平整的柏油地,上面規劃出各種球類的運動場地,地上的直線與圓圈交錯,像極了散落一地的幾何繪圖尺。
我彎腰放下手上的花束,讓它靠在光滑的藍色欄杆上。欄杆同樣是新的,比從前的欄杆直,我希望也能比從前的欄杆堅固,能阻止孩子們闖進去。
我脫下手套,調整花束上卡片的位置。獻給我親愛的寶貝女兒,原諒我。永遠愛妳的媽媽。
我交握雙手低下頭。我的話語在冷冽的空氣中如同薄霧一般模糊,禱告化成縷縷輕煙,蒸發成空幻,就像愛咪一樣。
我撐著欄杆站了起來,納悶地猜想,不知道公園的管理員是否會和去年一樣,在隔天一早便將這束花清掉?不過,也有可能根本留不到那個時候。
我曾在車禍意外現場看到繫在路燈上標示地點的花束,這些花一直放到花梗凋謝、包裝的玻璃紙變皺變髒之後,才被人收掉。這些花束的安全警示作用勝於紀念價值。我的花束並無不同,只不過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危險,不像超速的車輛那麼明顯易懂,甚至還讓家長難以向孩子解釋。
走到小徑盡頭之後,我回頭看。如果十年前的今天,我曾來到這裡並且回頭望,保持警覺,盡了做母親的責任,也許……
冷空氣刺痛我的臉頰,梧桐的樹枝上結了霜,網球場的網子上同樣看得見閃閃發光的冰霜。這時,聖馬可教堂敲了十聲鐘響。
我拉高外套衣領圍住脖子,走向公園的出入口。
珍在我家裡的電話答錄機留下訊息,提醒我別忘記她的新年「聚會」快到了。
「算不上盛會,」她說,「只不過是幾個朋友聚聚。我知道妳寧願留在家裡,我懂。但是,嗯,如果妳想來點變化或喘口氣,我們絕對歡迎妳。」
我刪除她的留言。我無法面對任何派對,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都一樣。我有自己的除夕儀式:到遊樂場獻花,和靈媒會談,怒氣沖沖地做完家事之後,再放聲哭泣,讓哭聲掩蓋午夜泰晤士河畔炮聲隆隆的慶典。我無法想像自己還能去做其他事,那可是對愛咪不敬啊!
我拿起電話撥打布萊恩的號碼,這也是我這項私人儀式的一部分。響了三聲之後,他接起電話。
「貝絲,」他說,「我就知道是妳打來的。」
他的語氣平淡,不帶感情,顯得沉悶又無趣。我是他除夕夜的例行雜務,和外出倒垃圾一樣。「進行得怎麼樣?」
「我……」我咬著嘴唇,忍住淚水。
「喔,貝絲,拜託。」
「十年了,布萊恩,十年了。」
「我知道,我沒忘。」
「我並沒說你忘了。」
他頓了一下,彷彿默默地數到十,看看我會再說什麼。我聽到電話的另一頭傳來熱門音樂和女孩子的笑聲。他的新家庭正興奮地準備迎接另一個新的年頭。
「聽起來,你們好像正在開派對。」我悶悶不樂地說。
「沒有,不過是女孩們跟著電視上的音樂頻道瞎鬧而已。」
女孩們。不只是一個女兒罷了,而且是兩個。但不管怎麼樣,她們只是他的繼女,是愛咪的替代品。我緊緊握住電話。我不該恨這兩個女孩的,但我就是恨。
「我最好趕快掛電話了,」我說,「新年快樂。」
在他用尖酸刻薄的批評來迎戰我的諷刺之前,我先掛斷電話。
我戴上橡膠手套,帶著清潔用具準備清理屋裡的每一個房間。這是幢大房子,對我一個人來說更是大而無當。但是我不願意搬家。房子裡有愛咪的衣服,而我對她的記憶已經像牆壁及天花板一樣,和房屋結構成了一體。
和布萊恩離婚後,他以為我會想搬到某個我較能掌控、又沒有那麼多回憶的住處。
「我要的是回憶。」我說。
「妳可以把回憶帶往任何地方,愛咪會永遠在妳身邊。」
「而我永遠會在這裡等著她。」
假如──就算機會再渺茫也好,假如愛咪還活著,假如她想找我,就必須讓她能輕鬆地找到。所以,我家門外無論如何都不會立起「出售」的看板。
我噴灑清潔劑,又是擦拭又是打磨,一直到手臂酸痛滿頭大汗,才肯結束手邊的工作。
雖然愛咪沒在她房間裡留下任何實質的可循之跡,但我還是在裡頭坐了一會兒。布萊恩特別整理過,刻意不讓這個房間成為紀念愛咪的聖壇。他在愛咪失蹤的一年後便清掉她的東西,好讓我們學習放下。
當我拉開前門拿出垃圾袋時,外頭的天色已經暗了,四處可見提早施放的煙火,有人拿著煙火棒,火藥的輕響伴隨著陸續綻放的五彩火花,然而,火花跳不到幾呎高便閃閃爍爍地熄滅,正如我獻給愛咪的祈禱,以及呼喚她回家的心聲一般。
我關上門,洗過手,拿著還沒點燃的蠟燭走進起居室,擺在爐臺上愛咪的照片旁邊。照片是她失蹤前一年在希臘扎金索斯海邊拍的,她的皮膚曬成了焦糖色,笑容和浪花一般清新,背景是陽光下閃閃發光的大海和讓人目眩的白沙。愛咪捧在手上的透明死水母彷彿一顆融化的水晶球。
我點亮蠟燭,看著光影在照片上跳動。我先親吻了指尖之後,才將指頭按在照片上,這時淚水刺痛了我的雙眼。
我拉上窗簾,接著打開音響,然後面對著愛咪的照片坐下,看著搖曳的燭光在她日曬過後的臉龐上舞動。
媽咪。
音樂播到一半,有人敲門了。
我調低音量,希望門外不管是誰會自己離開,我想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繼續我的儀式。但是敲門聲又響了,而且更大聲,連信箱都跟著咯咯作響。
「亞契太太,妳在家嗎?」
那是個女人的聲音,我認不出是誰在說話,也分辨不出說話人的腔調。我將音響調到靜音之後立刻後悔,因為這無異是讓外頭的人知道我在家。
「亞契太太,請妳開門,我有重要的事跟妳說。」
我站了起來,撥開窗簾由縫隙往外看,但立刻往後退。外頭那個女人把鼻子貼在我面前的窗玻璃上。我倒抽了一口氣,迅速放下窗簾。
「對不起,」她說,「我不是有意嚇妳的。」
「走開。」我大聲說,好讓玻璃窗外的女人聽到我的聲音,同時也希望她能聽出我的堅持。
「但是我有話要告訴妳。」
「如果是要我換電力公司,我沒興趣。我很忙。」
「我不是為這個來的,」她說話的速度很快,聲音愈來愈大,「拜託,真的很重要,和愛咪有關。」
「我沒有新聞要告訴報社。」
「我不是報社派來的。」
「如果妳是警察,那麼先把警徽讓我看。」
「我也不是警察。」
「那麼妳是誰?妳想做什麼?」
「我叫作莉比•勞倫斯,真的有事要找妳談談。」她的語氣焦急,顯然開始不耐煩。「面對面談,不是隔著玻璃窗說話。我大老遠過來找妳,拜託,妳不會想要隔層窗戶或信箱來聽我所要說的話吧!」
我拉開了窗簾。她有一頭深赭紅色的頭髮,臉色蒼白,藍色的眼眸顯得很急切。她直視我的雙眼,當我打開窗戶時,她勾起嘴角露出了微笑,眼神也緩和下來。
「什麼事?」
「和愛咪有關,」她說,「亞契太太,我知道她在哪裡。」
我記得自己眼前突然一片黑,莉比抱住了我,我聽到腳步聲,是她過去踢開前門。當她扶我穿過門廊,將我安置在沙發上時,她自己的呼吸都還沒緩和過來。
我醒來發現她站在火爐前面凝視愛咪的照片。她拿起照片,臉上露出笑容。
「妳還好嗎?」莉比問道,一面撥開我臉上的頭髮。我縮了一下,她立刻收手。
「對不起。」她站起來走到窗邊。「這陣子我一直很苦惱,不知道該怎麼把愛咪的事情告訴妳……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辦法把整件事說出來。」她瞇起眼睛嘆口氣。「但是她堅持要我說出來。她一直很……不快樂,很生氣。我沒辦法置之不理,或眼睜睜看著她繼續受苦。我要提醒妳的是,聽我說完話,妳可能會更痛苦。總之,我一定會更難過。」她咬咬嘴唇,繼續說:「嗯,無論如何,我總算做了這件事。對不起,我來得太突然,但是,要說出這件事只有一個方式。」
「重點在於妳要說什麼,而不是妳要怎麼講。」我啜了一口水,盯著她的雙眼問道:「愛咪還活著?妳確定?」
她點點頭。
我往後靠坐在沙發上,過去十年間所承受的種種痛苦一湧而上。
這當中最難受的是椎心的懊悔──所有沒說出口的話、沒機會一起做的事,都是最刺骨的遺憾──以及憤怒、憎惡和哀傷。
然而,震驚的情緒攔下了我的淚水,我眨眨眼,發現自己的眼眶是乾燥的。
「可是……這怎麼可能?」我把頭埋入雙掌之間,疑問讓我的腦袋更顯沉重。「這幾年來她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沒和我聯絡?現在呢?她在哪裡?」
「一件一件來,好嗎?對我好,也為妳好。」莉比的肢體僵硬,目光落向地板。
「對妳好?」
她用力地嚥下口水,枯瘦的指頭握緊又鬆開。
「這也會影響到我。」她冷冷地說。
「我是她的母親,」我氣得在沙發上坐直了身子,說,「妳只不過是傳達訊息的人。」
莉比眼底的怒意閃爍,她深吸了一口氣彷彿想反駁,但又忍了下去。
「把事情告訴我。」我把身體往前靠。
她伸手梳了梳頭髮。
「是這樣的,我要講的事可能不容易了解,」她嘆口氣說,「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將會改變一切。」
她回頭看著爐臺上那張愛咪的照片。
我刻意選了一張和警方用來協尋截然不同的照片。愛咪在那張正式照片上的笑容比較刻意,有些忸怩,她的金髮紮成一條長辮,襯在學校的綠色制服上顯得光澤亮麗,領帶V字結打得十分端正。那張照片出現在報紙上、電視新聞記者的背後以及超市的海報上,在全國人民的腦子裡烙印下粗心母親的評斷標準,同時也是對各地兒童的警告。那張照片,不再只是我小女兒的照片。
「妳得先看看這個。」莉比說。
她慢慢地把手伸進外套口袋,像是魔術師掏出帽子裡的兔子般,拿出了一本粉紅色的相簿。
她緩緩地把相簿遞給我,動作中看得出勉強,她似乎覺得我不可能讓她收回相簿。
照片裡的女孩有一雙藍得驚人的眼眸,她的笑容靦腆,用豹紋髮圈將濃密的金髮綁成一束馬尾。孩子細瘦的雙臂垂在身子兩側,粉紅色連帽衫下搭著一條白色緊身褲。
我全身的血液似乎瞬間被抽乾。我認得,我記得,愛咪從前就是這個模樣。
「妳這張照片哪來的?」我的聲音粗啞,語調幾近虔誠。
「照片是我拍的。在曼徹斯特一個朋友家的烤肉派對上。」她把照片轉了個方向,指出照片下方的大寫日期:二〇〇九年七月。
我用顫抖的手將照片拿到眼前近看。
「但她還是個小女孩!愛咪今年應該有二十歲了。」我抬起雙眼,憤怒和失望的情緒讓我幾乎說不出話。「我不知道這是誰,但是我現在可以告訴妳:她不是我的女兒。」
「我發誓,她是愛咪。如果妳願意讓我解釋──」
「我不聽!我不知道妳是誰,想做什麼,但是妳真的有病,妳太邪惡了。我究竟對妳,或對其他人做了什麼事,竟然要受到這樣的對待?妳給我滾出去。」我把照片丟還給她,接著站了起來。「現在就滾!否則我要叫警察了。」
我推她出門的力量大到令自己也覺得驚訝,我推著她穿過門廊和前門,在她出去之後,用力摔上門,鎖上。接著我滑坐在地板上,無淚地大聲啜泣。
莉比又敲門了。
「妳一定得聽我說,」她哀聲懇求,「拜託妳,她人在這裡,就在街上。我去帶她過來。亞契太太!別再失去妳的女兒了。」
我聽到她跑著穿過花園的小徑,接著又聽見柵門發出嘎吱聲響。
「愛絲玫!愛絲玫!」她喊道,「快點過來,愛絲玫!」
我站在門後,渾身僵硬無法動彈,幾乎要窒息。
莉比站在柵門外的街上,她正向某人招手,要那個人過來。
圍籬外傳來腳步聲和我聽不出內容的談話聲。莉比往左邊走過去,一個女孩從右邊走了出來。
我把手搭在牆上,強迫自己的心臟放慢速度,不想讓驚嚇打倒我,這不可能是真的,愛咪回家是個不合邏輯的希望。她和愛咪一樣高,一動也不動地站在柵門邊,外套的帽兜遮住了她的臉。莉比對她說話時,她轉過頭去聽,她呼出的白色霧氣讓我無法辨識她的側面輪廓。
呼吸,她在呼吸,她還活著。
「愛咪?」
我結結巴巴地說出這個名字。女孩慢慢朝我走過來,她每踏出一步,我的呼吸聲就跟著愈大聲,當她抬起手拉開帽兜的時候,我喘得更大聲。
我太害怕,怕到不敢直視。我怕自己即將看到的臉孔,也怕看到的不是我期待的人。
帽兜往後掀了開來。
她沒金色的長髮垂在臉蛋旁,像是一層面紗。她把頭髮往後撥,粉嫩的嘴唇牽動著,想要露出微笑,但藍色眼眸似乎少了些許輕快的湛藍,眼神中帶著幾乎看不出來的悲傷和質問,儘管如此,卻仍充滿活力和興奮。
「嗨,媽咪。」她說。
我屏住呼吸。這不是愛咪,不算是,但是,但是……
她讓我覺得有些熟悉,但也有些不同。
她們相像的程度太讓人不安,混亂的情緒緩緩地湧了上來,最後,我的雙腳再也支撐不住身體的重量。我跪了下去。我看到自己朝她伸出雙手想碰她,確認她不是出自想像,但我又害怕自己的觸碰會讓她消失,就像戳破肥皂泡泡一樣。
女孩朝我跑過來,臉頰貼著我的臉,我無力抗拒。我聞到她身上醉人的杏仁香甜,感受她紮實貼在我身上的小身軀。
愛咪,我的愛咪,她真真確確地在這個地方出現。
她如此接近,這讓我開始動搖,我的本能呼之欲出,雖然還有些猶豫,但卻無法遏止。我想壓抑,她不可能是愛咪,不是愛咪,然而……
莉比沿著小徑朝我們走過來,表情高深莫測,夾雜著寬慰、懊悔、同情與嫉妒。
「我們得好好談一談。」她半帶安撫,半帶勉強地說。
我先是點頭,但隨即忍了下來。這太荒唐,不太可能發生。這麼久以來,我一直努力對抗,但這足以將我推入錯亂的深淵。這女孩的年紀太小,不可能是愛咪,儘管我渴望她是我女兒,但仍不足以讓整件事成真。幻術師的把戲只有在觀眾信以為真的情況下才能達到效果,因為如此一來,這些觀眾才能看見幻術師要他們相信的假象。我雖然很想相信這女孩是愛咪,但我知道她不可能是我的女兒,邏輯打破了我的美夢。
「不必了。」
我推開女孩。她的藍眸泛著淚光,驚訝的眼神中帶著責難。
「走開!」我噓她,「妳不是我的女兒。」
「可是,媽……」
我多麼渴望聽到有人再喊我一聲媽,重拾母親的身分。但我要的不是陌生人口中的稱呼,這個字聽起來既醜陋又虛假,像是嘲笑,也像詐騙,更像洗腦。
「妳休想這樣喊我。」我說。
但是此刻我已經聽到了一聲媽,我多麼渴望能再聽到下一聲。
「亞契太太,拜託妳。」莉比出聲懇求,把一隻手放在女孩的肩膀上。「她不過是個孩子而已,受了不少苦才走到這一步,我也一樣。拜託……別對她這麼兇,我以同樣做母親的身分拜託妳。」
我眨了眨眼睛。
「她是……是妳的女兒?」我問道。
莉比點點頭,用外套袖子擦掉眼淚。
「拜託妳聽我們說──」
「不要,」我舉起雙手,說,「妳自己也說了,她是妳女兒。她不可能同時是我的女兒,這怎麼可能呢?再說,她的年紀也未免太小。」
「她和愛咪一樣大。」
「和當年的愛咪一樣大。還是說,她的光陰暫停了?過去十年的時間對她根本沒有影響?」我挖苦地說。
「妳的話比妳自己所能想像得還更接近真相。」莉比說。
「滾出去!」
我推開女孩,她在門階上絆了一跤,跌到地上。
「媽!」她嚎啕大哭地喊:「別趕我走,我是愛咪,是妳的小女兒。這是我弄的,記得嗎?」她爬到門階,指著一塊瓷磚上的刮痕。「看到了嗎?」
她的指頭劃過瓷磚上模糊的刻字:AA。(譯註:Amy Archer的英文姓名縮寫。)
「愛咪•亞契。」她的手指劃過相鄰瓷磚的刻痕。「DB,唐娜•畢夏(Dana Bishop),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刻下這幾個字母之後,妳還打了我們的腿當作懲罰。」
我倒抽了一口氣,驚訝到沒辦法說話,心跳加速。
兩個靈魂的女孩
有時,我會看到她坐在旋轉木馬上的模糊身影,聽見伴隨溜滑梯嘎吱響的咯咯笑聲。當然,其實她根本不在。溜滑梯、鞦韆也全都不見了。議會決定拆掉搖搖晃晃的蹺蹺板和旋轉木馬,取而代之的是新穎的遊樂設施,此外,他們也把遊樂場遷移到公園另一側的咖啡座旁。現在,家長可以在孩子盪鞦韆、玩沙子或轉圈圈時,邊聊天邊享用卡布奇諾。
但是,他們奪走了我最後一次看到愛咪的地點。
從前的遊樂場──那個愛咪去過,而且鍾愛的樂園,如今成了一片平整的柏油地,上面規劃出各種球類的運動場地,地上的直線與圓圈交錯,像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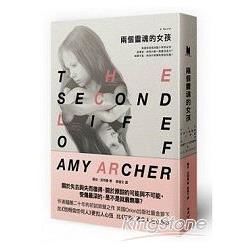

 共
共  2014/05/16
2014/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