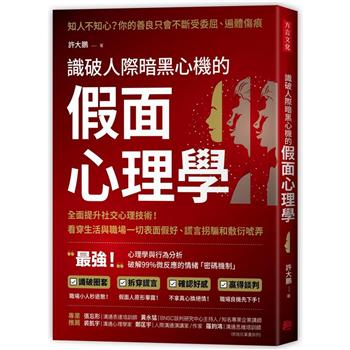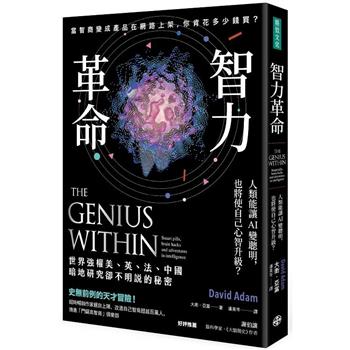序言
歷史是我們對於過去最為熟悉的一種說法,經常被探討並反覆琢磨,事件也被完整地分析和評估。我們視事件的敘述為~歷史,歷史本身也即是事件的敘述。事件發生很長的一段時間後,各種敘述通常便匯集成為歷史──此外,歷史對我們來說有極大的價值。我們總相信歷史是客觀而真實的,但我們將會知道,並不全然是這麼回事。
雖然我們認為新聞只是現實生活的評論,但新聞其實是觀看過去的另一種角度,是過去特寫、加速的版本。新聞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呈現,通常帶來大量的臨場感。一則優質、文筆精湛的新聞似乎能令人身歷其境,彷彿我們都是目擊者。因為新聞記者工作必須迅速,跟緊編輯的截稿時限,他們的故事可能會有所訛誤,而且通常並不完整。最後導致我們在報紙和雜誌中所看到的敘述,和歷史敘述相比之下感覺非常不同。
再者則是目擊者敘述,這是更為接近過去的一種說法。有些目擊者敘述,雖然是由一般人所寫,但卻格外具有說服力;這似乎告訴我們,人們會因為目擊著名或關鍵事件的經驗而感同身受。其中一段敘述是湯瑪士.貝克特(Thomas Becket)的暗殺事件,是由一位剛好在1170年那天造訪坎特伯里(Canterbury)的修道士所寫,他走入了史詩般的殉難事件中,隨後的三百年間,此事件激發了人們對中古歐洲的想像。他的名字是愛德華.格林(Edward Grim),生平不詳──唯一為人所知的光榮時刻,就是當一位聖者被殺死時,他和他站在一起,而且他的敘述歷歷在目。另一段傳神、又令人驚豔的敘述是來自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對於古巴革命的敘述。切格瓦拉是位非常好動的人──不過他寫得也非常傑出。
目擊者敘述最吸引人之處就是,不論我們多久之後才讀到,都能給我們身歷其境的感受,令人走入某些歷史事件的時空。其中有一種特別的樂趣。目擊者敘述有時被認為比歷史敘述更為真實,因為歷史學者對於過去,常持有政治立場、特定意圖和「角度」。例如,我們在看湯瑪斯.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對理查三世(Richard III)統治的敘述就要心存懷疑,因為他是都鐸王朝(Tudor)的擁護者;摩爾很可能會詆毀理查三世,並支持亨利七世(HenryVII)奪取理查三世的英國王位。亨利七世即是他那位著名的繼承人──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父親。
但是,即使是閱讀目擊者的敘述,我們仍需十分謹慎。我們都曾誤解自己看到或是聽到的事,尤其是毫無防備之下突然發生的事件。因為個性、興趣、缺點的關係,我們會特別注意和忽略某些事。因為宗教信仰、社會經濟背景或隸屬於不同政黨,我們可能會選擇強調事件的某些面向──並不是故意想誤導,只是因為有些事情更讓我們感興趣。因為親身投入,我們可能會蓄意或不自覺地對故事有所偏頗。當有不只一位事件目擊者的敘述時,偏頗就會變得非常明顯。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件,例如一場道路上的小車禍,就有受害人敘述(車被撞歪),犯案者敘述(粗心大意撞上某人的車尾),站在人行道上目擊的旁觀者敘述(也許他並沒有真的看到)。三個敘述會各自和其他敘述有所不同,這完全是可以預期的。
我們必須容許可能肇因於社會、政治、種族、宗教背景而產生的偏見。但有時也會發現,我們以為某段敘述被偏見扭曲,結果最後發現是我們的誤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亞歷山大.韋斯(AlexanderWerth)對瑪德尼克死亡集中營(Maidanekdeath camp)的可怕敘述。英國廣播公司(BBC)認為敘述有所偏頗,因為雖然韋斯的國籍是英國人,但他是在俄國出生的。他們也認定敘述太極端了──英國廣播公司認為納粹集中營不可能有那麼壞──但韋斯的敘述被證實所言不虛。
反過來說,在其他情況中,一開始以為是平實客觀的敘述,可能到最後才發現曾以某種方式修飾,反映並強調目擊者的看法和興趣。維多利亞女皇(QueenVictoria)描述自己的就職典禮,告訴我們她感覺到那一歷史時刻的莊嚴隆重,以及她內心新生的自立感;查爾斯.格雷維爾(Charles Greville)對年輕女皇加冕典禮的敘述則告訴我們,他發現現場明顯地絲毫不莊嚴隆重,因為沒有事先預演過。凱撒(Julius Caesar)對於他身為軍事指揮官的敘述不免表達出自圓其說和自鳴得意的態度;他回憶錄的重點,就是使羅馬讀者對於他身為軍事指揮官的卓越表現,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他的履歷,他步入羅馬政治高層官職的平台。當然受害者一定會有非常不一樣的敘述,但英法鐵器時代晚期的部落大多無文字。書寫不在他們的文化中,因此少了他們的敘述,我們無從平衡凱撒的敘述。
有些敘述非常坦誠,但事實遠非如此。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自己打開圖坦卡門(Tutankhamun)陵寢的敘述中,高度杜撰了內容,卻沒有顯露出任何的跡象和線索。他的敘述讀來似乎是真的,但事實上並不是。有時偏見使目擊者敘述變得更為有趣,因為證人成功擺脫偏見。普里斯庫斯(Priscus)對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Hun)的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具有強烈偏見的觀察者,他到達現場,最後跳脫偏見。和羅馬帝國其他居民一樣,普里斯庫斯先入為主認為阿提拉是個野蠻人。但現實生活中,他是一位舉止得體、謙恭溫和的男人,有十分細膩、正式的餐桌禮儀。事實上,就和羅馬帝王一樣。
這樣的敘述,當旁觀者的原則、信仰、偏見真的面臨考驗,跳脫出偏見,我們就應該好好評價──甚至珍惜。因為我們能確信,他們鐵定是真實的敘述。
評價第一手敘述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以現代的眼光觀看特殊的細節。究竟蘇格蘭瑪麗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的處決有多麼人道?西元1963年那天,在達拉斯市(Dallas)迪利廣場(DealeyPlaza)上的群眾耳中,槍聲究竟是從哪傳來?
甘迺迪(J.F.Kennedy)刺殺事件有許多平民百姓目擊,也全都識字,他們的證詞也全都適時由沃倫委員會(WarrenCommission)記錄下來。最後集中了這些證詞,包括引人入勝的說詞,和時而神祕矛盾與不一致的說詞,最後成為了歷史的原始資料。少了目擊者敘述就寫不出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倖存的德國領導者接受審判。著名記者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是美國合眾社(UnitedPress)西元1940年代中期的首席記者,他評述說:「我們這群見證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s)的人,彷彿和參與、組織審判的人一般,都意識到歷史正被寫下的事實。」
本書中許多目擊者都是旁觀者或非歷史事件中的要角。普理斯庫斯、愛德華.格林、比提醫師(Dr. Beatty)、瑪麗.露易絲.奧斯蒙(Marie-Louise Osmont)、文森.西恩(Vincent Sheean)和珍.希爾(Jean Hill)都屬於這一類。他們是走入重大事件的平凡人。他們的敘述對我們有特別的共嗚,因為他們是站在我們的角度。有時候平凡人會剛好在對的時間站在對的地點,目睹歷史事件的發展。也有些目擊者絕不只是旁觀者;在他們敘述的事件中,他們是要角,有時是主角,他們不同的觀點更是迷人。這一類的像是柏拉圖(Plato)、哥倫布(Co l umb u s ) 、蓋伊. 福克斯(Guy Fawkes)、奧維爾.萊特(OrvilleWright)、史考特上校(Captain Scott)和霍華德.卡特。這些人不只是目擊者,他們自己寫下了歷史。
遠古時代,鮮少有歷史事件的目擊者是識字的,除了一些高知名度的人如凱撒外,即使是識字的目擊者也不會寫下他們回憶錄。寫錄的工作都是交給抄寫員、記事者、修道士。古老的敘述通常都是授人代書,由別人寫下的回憶錄。蘇格拉底(Socrates)之死的敘述是柏拉圖在詳細訪問目擊者之後所寫下的。這段敘述中有一股特別的哀痛,因為柏拉圖自覺身為蘇格拉底的朋友,他應該要親自在場,他應該要是目擊者。但當時候到了,他卻沒有勇氣。
書中所有的敘述都不違背原文:也就是說,敘述是逐字引用,沒有經過解釋。唯一編輯干預的部份是把拼字改成符合現代用法,因為古代的拼字通常會造成理解困難,還有標點符號也重新現代化,增加可讀性和釐清意思。許多敘述有所編輯,使文長不至於太長,但是處理時十分謹慎,避免改變原文強調的部份或風格。
我在此必須提到,在三K黨的敘述中,「黑鬼」(nigger)一詞的使用。這個詞在現代語境中通常會造成羞辱,但各位一定要記得,這個詞是由班.強森(Ben Johnson)所用,他本身是一位前黑人奴隸,在西元1868年他使用了這個詞來形容和自己有相同膚色的人。時間和政治正確的思想都會改變;一百年後,這個詞通常視為種族歧視用語,因此十分令人反感。閱讀本書的各項敘述時,要視敘述為反映各個時代和文化的產物,這點是十分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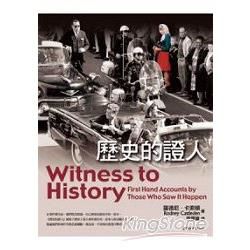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