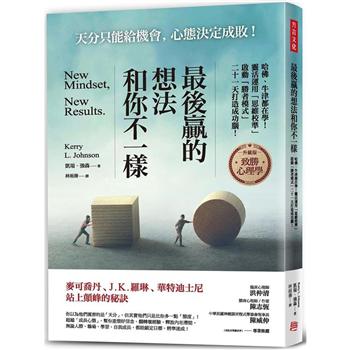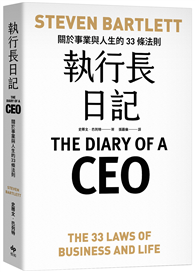第一章文明和社會控制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據說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年),美國實用主義首創人之一。——譯者注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問題的最大敵人就是這一問題的教授們。他這樣說,是指的像醫藥和法律這類實際活動。在這些實際活動中,從事實際業務的人不斷地與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實保持接觸。他從經驗裡得出他的觀念,而且必須經常加以改變,並改造他的理論,使其適合於必須應用這些理論的事實。另一方面, 教授卻從其他人的關係中去認識那些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實,並且假定這些東西都是別人給予他的。他從這些事實中進行概括並整理出各種概念和理論來,然後再從中推論出更多的概念和理論;根據這些事實,他建立起一套頑強的、違反生活和自然界事實的和非常固執的教義,並企圖使生活和自然界符合他的理論模型。對於我們從事各門社會科學的人,這種看法包含著一個警告。僅拿我自己的專門領域來說,當我們回顧過去時,我們見到五十年以前的法官和律師在關於法律的業經證明具有重要意義的運動裡,完全走在法學家和法學教師前面,這肯定是真確的事實。那時法律科學到處落後于立法和司法判決的實際進程。當法律科學一有實際影響時,它就起阻礙作用。我們今天對於上一代涉及社會立法的司法判決感到不滿的大部分東西,就代表了當時所教授的最時新的法理學科學。來自各種未被承認的、部分被承認的、未被保障的或未被充分保障的利益的壓力,往往使十九世紀的真正法律完全走在當時法學理論的前面。
組成一個法律體系的那部分法令(precept),包含兩種成分,一種是命令性成分,一種是傳統性成分。前者是立法者的創作。哲學家通常對立法者提供指導。但是他多半認為自己賦有一種支配的權力。傳統性成分是經驗的產物。在古羅馬,它是從法學家在解答關於法庭上實際爭訟的各項問題的經驗中產生的。在我們的法律中,它是從法院判決案件的經驗中和法官們從有記錄的司法經驗中努力去尋找對具體爭端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判決的原則中產生的。因而,我們就有作為命令的法律,還有在經驗的基礎上作為對正義的確定和陳述的法律。它們各自謀求建立正義的法令。所以,它們各自都受某種理想的支配。在十八世紀以及在我國的十九世紀前期,自然法理論曾為立法機關和法官提供這種理想。這是對一切民族、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都具有普遍效力的一整套理想法令的理論,這批理想法令來自關於一個理想的人打算做和不打算做、打算主張和打算承認別人主張的觀念,並且是基於純粹理性而得出來的。
在羅馬法的古典時代以及在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和美國的法律中,哲學作為在自然法支配下的法律的指導處於全盛時期。每一本法律著作都有一篇哲學性的導言,而重大的法案往往有一段哲理性的序言。但是除開這個理論所遇到的哲學上的困難以外,自然法不能使自己成為制定和發現法律的一個有用的工具。當自然法自稱是理想的和普遍的並來自普遍理性的東西時,正像我一向慣於說的,它事實上是一種實在的自然法,而不是自然的自然法。它是對一定時間和地點的實在法的一種理想化翻版,所以在實際上,這就使法律提供對它本身的批判。例如,當英國人在檳榔嶼建立了一個法院,而且必須對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執行司法時,有人認為這個法院應受自然法的支配。可是當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的韋斯特伯裡勳爵韋斯特伯裡勳爵(Lord Westbury,1800-1873年),英國大法官。——譯者注就這個法院的一起上訴案件適用自然法時,其結果是,普遍的自然法甚至在細節上都是和英國法律一模一樣的。5
在十九世紀後期,隨著自然法的崩潰,特別在英語世界裡,我們曾企圖不要哲學。事實是,某些法令雖為法院所適用,但其後盾則是法院院長和他的下級部屬。這些法令蓋有國家的金制印章,並為政治組織社會的強力所支援。這就是我們能夠依靠的東西了。這些法令乃是純粹的法律事實。科學的法學家對於凡是沒有這種金制印章和不為強力所支持的任何東西,一概不加以考慮。但是法院和律師一定會告訴我們,這種純粹的法律事實是一種幻想。他們不能忽視法律中的一種理想成分,即使法學家業已將它丟開不管。當人們要求法院就各種具有同等權威的論證作出發點進行選擇時,當人們要求法院解釋一項法令的本文時,當人們要求法院將一個標準適用于行為時,法院就離開法學家的純粹法律事實,而使他們的決定去適應一個理想。因此在本世紀開始時,自然法就必然恢復,雖然並不是始終用這一名稱,而且這一次也並沒有給我們一個關於理想法令的普遍法典。現在自然法的任務不是給我們一批理想的普遍立法,而是給我們一種對實在法中的理想成分的鑒定。即使絕對的理想不能被證實,這種鑒定可以確定和陳述出一定時間和地點的社會理想,並且使它成為對各種論證、解釋和適用標準的出發點進行選擇的尺度。就像有人講過的,我們可以有一種內容正在起著變化或形成著的自然法。
因此,在本世紀前期,就出現了法律哲學的復興。大約在同時,孔德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創始人。——譯者注在百年前所創立的社會學,即關於社會的科學,已在各門社會科學中取得了它的地位,而法律社會學也同各種社會法律哲學一起出現。但是學者們在這方面進行工作時,同樣太缺乏對司法所必須處理的各種問題的知識,而且往往對各種法律體系傳統成分中所陳述的、由理性所發展的經驗缺乏掌握。因而,我們就不得不發展一種哲學的法律科學,即哲理法學,和一種社會學法學。我們求助於哲學、倫理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但只是在那些被認為是法學的問題上求助。我們研究一切意義上的法律,把它當作廣義的關於社會的科學的一個很專門的方面。
哲理法學理論曾被視為解決一定時期的特殊問題的辦法,然後給以普遍的形式並使其用在任何地方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問題上。我們所要的並不是一種企圖削足適履地強使法律適合於它的體系的法律哲學,也不是一種陷於方法論之中的、企圖通過證明它具有自己的可以測定一切社會生活現象的專門方法,來為一門關於社會的科學進行辯護的法律社會學,我們所要的不過是一種知道如何利用哲學的社會學和一種知道如何利用社會哲學和哲學社會學的社會學法學。
回顧一下這一世紀的四十多年以前,我們見到已經有了很多成就。施塔姆勒*復活了法國人的所謂法律上的唯心主義。如果說他並沒有為我們解決8問題,他卻向我們指出了問題所在。他力圖使我們意識到實在法中的理想成分並力圖建立關於它的理論,而十九世紀的自然法曾力圖加以批判;這正像在施塔姆勒以前康得曾力圖建立一些立法的原則,而康得的先輩卻力圖找出一部普遍的法典一樣。狄驥**給了我們一種關於這一世紀初城市工業社會的理論,作為今天法律的理想成分的理論。他的理論是一種社會學的自然法。他設想法律中的每樣東西都是從一個“權利和法律”的基本原則獲得效力,並根據同一基本原則來加以判斷。他繼孔德之後力求通過觀察得出上述原則,並通過進一步的觀察來加以證明。事實上,他是按照塗爾幹***關於社會分工的著作來進行他的觀察。今天狄驥並不像過去那樣時髦了。但他曾起了有益的影響。惹尼****向我們表明了實在法中技術成分的重要性,並給了我們一種關於理想成分的新經院主義哲學理論。他的《私法
*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年),德國法學家,新康得主義法學首創人。——譯者注
**狄驥(L訜on Duguit,1859-1928年),法國法學家,社會連帶主義法學首創人。——譯者注
***塗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法國早期社會學家,曾在其主要著作之一《社會分工論》中宣揚社會連帶主義學說。——譯者注
****惹尼(Fran㜢ois G訜ny,1861-1944年),法國法學家。——譯者注實在法中的科學和技術》一書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本書論述到我認為是法學的一個根本問題,即評價利益的尺度,它還論述到為前一世紀的分析法學所忽視的法律的兩種成分,而且他都以一種嶄新的和啟發的方式來對待它們。奧裡烏*給了我們一種關於組織的理論,這些組織是今天社會中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在我看來,他的理論,一種新經院主義哲學的團體主義,歸根結底在試圖解釋和建立起一種關於成為今天社會中最活躍的集團,即勞工組織的理論,而在英語世界裡,
這些勞工組織無論在使用法律外的強力(當國家被認為具有對強力的壟斷)時,還是控制政治組織社會的強力來達到它們的目的時,都正在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要素。他所稱的各種各樣團體——即一些與某一時候的人物無關而一直存在的事物,它們的某些活動是不包括它們的人物在內而組織起來的,並且它們還設立了自己的權力機關和程式——這些每一個都在實現著自己的觀念的各種各樣的團體將代替一大群個人,其中每一個人都在一種永不終止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衝突或競爭中運用他的意志,康得曾力圖對這種衝突或競爭加以安排。重要的是,我們在這裡有了一種從個人以外去尋找單位的理論,同樣重要的是,當這一問題正擠滿在私法中時(甚至在公法具有私法觀點傳統的英語世界中也是如此),上述理論已很廣泛地為公法作者們所接受。在這以前,埃利希**已向我們證明了作為法律秩序基礎的各種關係、集團、聯合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秩序在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羅斯科·龐德的圖書 |
 |
$ 165 ~ 209 | 透過法律的社會控制【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羅斯科·龐德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2-28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龐德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透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美國社會學法學必讀著作
本書是作者在擔任哈佛法學院院長期間所作的一篇專題講座的講義,在1942年發表,全書共分四章:文明和社會控制、什麼是法律、法律的任務、價值問題。龐德在該書中指出,為保障文明的正常發展,必須借助外部的社會控制,使人類的合作性社會本能對擴張性自我主張加以限制。龐德認為,由於人具有擴張性自我主張的傾向,因而,世界上充滿了各種利益的衝突。法律的社會控制職能,就是要調整各種相互衝突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正義。
通過講述文明、社會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間的關係,強調法律已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邏輯嚴密、層層推進,從各章的論述中瞭解到現代西方社會學法學的基本觀點和框架。集中闡釋龐德社會學法學的精髓——社會控制理論與利益學說,為博大的法學思想提供了簡明的範本。
作者簡介: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1870年10月27日—1964年6月30日),美國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法學家之一,20世紀西方法學界的權威人物之一。曾於1916年至1936年長期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院長。龐德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包括詹姆斯(W.James)的實用主義哲學和霍姆斯(Oiiver W. Holmes)的實用主義法律思想。他的法學思想對當代法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社會學法學」運動的奠基人。
譯者簡介:
沈宗靈 (1923年-2012年2月20日),北京大學教授。曾任北大法律系法學理論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比較法—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會法理學研家會總幹事,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總幹事,國際法律哲學與社會哲學學會中國分會第一任主席。主要從事法理學和比較法學研究。
章節試閱
第一章文明和社會控制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據說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年),美國實用主義首創人之一。——譯者注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問題的最大敵人就是這一問題的教授們。他這樣說,是指的像醫藥和法律這類實際活動。在這些實際活動中,從事實際業務的人不斷地與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實保持接觸。他從經驗裡得出他的觀念,而且必須經常加以改變,並改造他的理論,使其適合於必須應用這些理論的事實。另一方面, 教授卻從其他人的關係中去認識那些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實,並且假定這些東西都是別人給予他的。他從這些事實中進行...
據說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年),美國實用主義首創人之一。——譯者注曾經說過,任何一個問題的最大敵人就是這一問題的教授們。他這樣說,是指的像醫藥和法律這類實際活動。在這些實際活動中,從事實際業務的人不斷地與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實保持接觸。他從經驗裡得出他的觀念,而且必須經常加以改變,並改造他的理論,使其適合於必須應用這些理論的事實。另一方面, 教授卻從其他人的關係中去認識那些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實,並且假定這些東西都是別人給予他的。他從這些事實中進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導讀/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特約講座教授 王寶輝
第一章 文明和社會控制
第二章 什麼是法律?
第三章 法律的任務
第四章 價值問題
索引
羅斯科·龐德年表
第一章 文明和社會控制
第二章 什麼是法律?
第三章 法律的任務
第四章 價值問題
索引
羅斯科·龐德年表
|
 龐德,亦作龐悳,字令明,涼州南安狟道人;東漢末年名將,武藝出眾、膽烈過人,原屬馬超父子,後於建安二十年隨張魯歸順曹操。官至立義將軍、關門亭侯,死後曹丕諡曰壯候。
龐德,亦作龐悳,字令明,涼州南安狟道人;東漢末年名將,武藝出眾、膽烈過人,原屬馬超父子,後於建安二十年隨張魯歸順曹操。官至立義將軍、關門亭侯,死後曹丕諡曰壯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