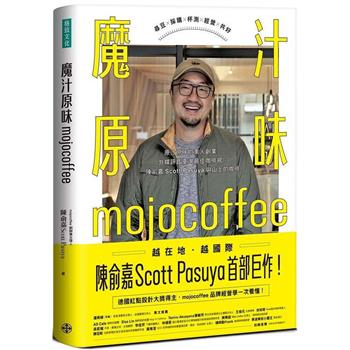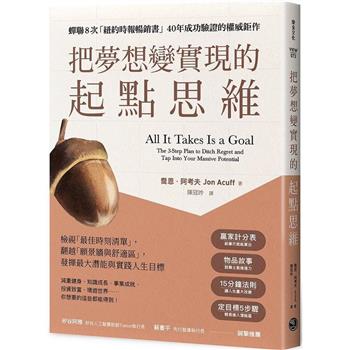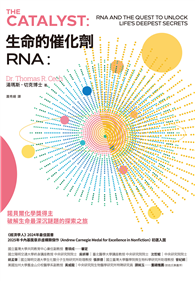《狂野追尋》被書評譽為「這是一本波赫士會寫的書」,具有自傳色彩,在書中凝結浪跡天涯的心路歷程。小說描述阿圖羅.貝拉諾(與作者姓發音相近)和烏里塞斯‧利馬兩人,有著若干相同且奇特的背景─販毒、寫詩、喜好居無定所的漂泊之旅─兩人屬於墨西哥一個─反權威、反傳統、反崇拜,標榜以真心肺腑發聲創作的前衛詩派,稱之為「內在寫實主義」(real visceralista)的團體,兩人邁向無目的地之旅,要去尋找「內在寫實主義」詩社的前輩─在墨西哥革命中失蹤的女作家蒂納赫羅。
這個「尋找失蹤者」的目的卻是要讓自己成為另一個失蹤者的企圖,這是一個「歷程」重於「目的尋找」的永恆之旅,也是一個無止境的隱遁之遊。兩人的行蹤透過六、七十位與兩人偶遇的經歷的人物敘述交待,因此,每一次的偶遇都是一段獨立開放的故事,儼然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大全。伴隨著主要敘述者(一位十七歲、愛好文學的大學生)對世界、對情慾的狂野探索,鋪陳了一段文學與暴力的華麗探戈。
作者簡介:
羅貝托.博拉紐
Roberto Bolano, 1953-2003
生於智利首都聖地牙哥,父親是卡車司機兼業餘拳擊手,母親則在學校教數學和統計學。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從學校中輟後,開始在墨西哥擔任記者。1973年,回智利響應左派社會主義阿言德政權,在皮諾契政變之後被捕,短暫入獄。出獄之後轉往薩爾瓦多、墨西哥,1977年前往歐洲,浪跡法國等地,四處打零工,包括洗碗、清潔、收垃圾等,最後在西班牙巴賽隆納落腳。
博拉紐以詩人自居,也以身為詩人為傲,但在結婚生子之後,他體認到流浪詩人的生活無法給家人較安適的未來,40歲開始寫小說。第一部長篇小說《狂野追尋》在拉美文壇引起的轟動,榮獲1998年羅慕洛.加列哥斯國際小說大獎(Premio internacional de novela Romulo Gallegos)、賀雅德獎(Herralde Prize)、智利國家圖書協會大獎(Chilean National Council of Books Prize),不亞於當年《百年孤獨》出版時的盛況。
2003年,博拉紐因肝病去世,享年五十歲,身後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三部詩集,包括《護身符》(Amuleto)、《遙遠的星辰》(Estrella distante)、《打電話》(Llamadas telefonicas)、《智利夜曲》(Nocturno de Chile),以及長篇小說遺稿《2666》等。
博拉紐過世之後,作品仍陸續被西方國家發掘出版,佳評如潮,蘇珊‧桑塔格推崇他是「那一代西班牙語世界中最值得欽佩的小說家」,《明鏡周刊》則稱他為「當代西班牙語文學中最大膽的作家」。
譯者簡介:
楊向榮
現居北京。曾在《收穫》、《天涯》、《人民文學》、《作家》、《青年文學》等刊物發表小說。著有短篇小說集《果園之火》,譯有《鱷魚街》、《天使與昆蟲》、《孩子們的書》等。
非爾
現居台北。譯有《被子》。讀書為業,譯事偶一為之,路見不平拔劍相助耳。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狂野追尋》,簡體版譯為「荒野偵探」,但小說中既無荒野,也無偵探。這是一趟追尋,但是在看似錯落的敘述中,如鑽石般耀目又直白得好似不見風采的文字隨著不同角度的轉動變換著面貌,那追尋的對象也彷彿隱晦了起來;它擺脫了拉美文學「魔幻寫實」的刻板標籤,也是一張指涉了拉美文學傳統與恩怨的地圖。在這本博拉紐自稱為「寫給我輩的情書」中,青春襲來,如此狂暴又如此混亂,如此有血有肉、刺痛又如此悲傷而溫柔,就連麻痺而世故的心,也不免被攪動。
「拉丁美洲文學經典裡極為重要的一部作品,但其中並無艱澀高深之處。《狂野追尋》是一部邋遢的史詩,部份是公路電影,部份是逸趣橫生又充滿鄉愁的告白。……一部渾然天成的文學巨作。博拉紐讓自己成為小說的核心,重新創造了凱魯雅克,卻少了自我膨脹……。小說中的幾位主角最後並沒有好下場,但是對於讀者來說,結局卻是壯麗精彩。」──《每日電訊報》
「博拉紐營造出一個已成追憶的迷人世界,充滿青春和烏托邦的理想,既獨特而生動,又悲傷而無法遏抑。」──《出版人週刊》
博拉紐盤據在許多拉丁美洲作家的心頭(四十多歲的那一代也不例外),就如當年馬奎斯盤據著同輩與後輩作家一般。──《紐約時報》
「博拉紐是第一個真正突破拉美文學大爆炸(Latin American Boom)的作家。許多跟他同一輩的作家,還有更年輕的作家,都試過,也還在試著找到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但沒有人可以真正擺脫馬奎斯、尤薩和在一九六○年代讓全世界驚艷的拉丁美洲文學所投下長長的影子。博拉紐卻似乎是毫不費力地就與之切割開來。大爆炸的那批作家讓拉美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佔有一席之地。而博拉紐透過無根、不舍、不妥協的文學態度,則創造了一個心智的拉丁美洲,一個後國家主義的拉丁美洲。」──薇莫(Natasha Wimmer),《狂野追尋》與《2666》英文版譯者
「稱博拉紐為天才絕非過譽。光是一本《狂野追尋》就足以讓他永世不朽。」──《華盛頓郵報》
「對於書中所描繪的這群人來說,文學是麵包和水,性和死亡。有一個訊息是博拉紐的小說不斷傳遞、也或許是得自他自身的生命,那就是:書至關重要。」──GQ
「我最喜愛的作家……《狂野追尋》是一艘方舟,載著詩歌與青春所有的奇特救贖,不受過往與未來的浩劫所破壞。」──《愛的歷史》作者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
「讀了博拉紐之後,會讓你覺得自己變了。他會改變你看待世界的角度。」──《衛報》
「狂放逗趣,但也同樣溫柔。……這本小說是寫給一個世代的悲歌。」──《獨立報》
「波赫士會想寫這種小說的。一本極有原創性、極為美妙的書:有趣、感人、重要。」──《國家報》(El Pais)
「博拉紐被譽為後馬奎斯時代的文學巨人之一。毫不費力就將彼此不相關的幽默與輕柔的悲劇感交融在一起。」──《週日電訊報》
「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推崇博拉紐為他那一輩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他的小說力道立見。激動人心。」──《展望雜誌》
「《狂野追尋》讓人別無所求……。一部極好的小說。」──《洛杉磯時報》
「他那一輩最受推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古怪有趣,同時又隱隱令人害怕。」──《國家》雜誌
「一本勃然蔓生、政治意味十足的流浪漢小說。」──《Elle》雜誌
「趣味狂野……。博拉紐巧妙融匯了他的喜感與感傷。」──《紐約時報》書評
《狂野追尋》給了我們第一個真正的徵兆,那一條自負好鬥的南美作家的行列終於走完了:它標示著那些拉美文學大爆炸的大作家已開始終結……。這本書也讓我們認識了一位驚人的作家,他提醒了我們,在閱讀的熱情之中有多少深刻的樂趣,而他卻是在無人察覺到的深淵邊緣度日。他在那裡做什麼?在俯視一片虛空的岩壁上,他寫作。於今回顧,《狂野追尋》以及在他死後出版的巨作《2666》必須被視為博拉紐非凡、傳奇作品的兩條主幹。──《文學雜誌》(Le Magazine Litteraire)
「《狂野追尋》是對過去三十年粗暴又抒情的紀錄。」──《世界書刊》
「一位罕見而多產的才子。」──《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博拉紐是當今拉丁美洲世界中最閃亮的文學巨星。」──《國家報》
「博拉紐的兩部長篇小說──《狂野追尋》和《2666》」──對拉丁美洲的小說創作(以及對美洲的英語創作)有著無可估量的衝擊。」──亞馬遜書店
「這部小說……可能是你今年讀到最有創意的小說。」──《泰晤士報》
「能讀到一本禮讚生命與文學的書,令人雀躍無比。」──《每日電訊報》
「書中不乏極為美麗而詭異的片段。」──《金融時報》
「一部龐大、線索四處的公路電影式小說……熠熠生輝。」──《前鋒報》
「未來南美洲文學最閃亮的希望。」──《新蘇黎世報》
「有些書很快就從眼前掠過。我們希望這種書能更厚一點,於是算著頁數,並不是因為書太無聊,而是因為想到要跟書中角色道別,就感到焦慮。《狂野追尋》就是這麼一本書……。《狂野追尋》成功地捕捉到過往的狂熱,還有追回過往的可怕又不可能的渴念。」──《法國搖滾怪客》
「強烈又毫無章法。……博拉紐的作品都是幽默四溢,生猛卻精緻。」──《金融時報》
「博拉紐有說故事的天分,與湯瑪斯.品瓊(Thomas Pynchon)、唐.德里羅(Don DeLillo)等人同級。」——《加泰隆尼亞報》(El Periodico)
「崇高與邪惡交替並陳,《狂野追尋》是一個時代——同時也是任何一個熱情體驗文學和人生的時代──的壯闊肖像。」──《先鋒報》(La Vanguardia)
「很可能是現今西班牙語世界中最大膽的作家。」──《明鏡週刊》(Der Spiegel)
「當今拉丁美洲文學最重要的小說之一。」──《薩克森時報》(Sachsischen Zeitung)
「博拉紐的作品時而美麗非凡,(至少對我來說)也是全新的經驗……。閱讀博拉紐就像是在聽祕密故事,個別事件的脈絡展現眼見,得見藝術和人生的軌跡在地平線共一色,在彼處如夢一般縈繞,當我們醒來之後一定會更仔細端詳這個世界。」──《紐約時報》書評
「他那一代之中最優秀的拉丁美洲作家……,博拉紐的聲譽和傳奇扶搖直上。」──《紐約時報》拉丁美洲特派
「博拉紐提醒了我們,在閱讀的熱情之中有多少深刻的樂趣。」──《文學雜誌》(Le Magazine Litteraire)
媒體推薦:《狂野追尋》,簡體版譯為「荒野偵探」,但小說中既無荒野,也無偵探。這是一趟追尋,但是在看似錯落的敘述中,如鑽石般耀目又直白得好似不見風采的文字隨著不同角度的轉動變換著面貌,那追尋的對象也彷彿隱晦了起來;它擺脫了拉美文學「魔幻寫實」的刻板標籤,也是一張指涉了拉美文學傳統與恩怨的地圖。在這本博拉紐自稱為「寫給我輩的情書」中,青春襲來,如此狂暴又如此混亂,如此有血有肉、刺痛又如此悲傷而溫柔,就連麻痺而世故的心,也不免被攪動。
「拉丁美洲文學經典裡極為重要的一部作品,但其中並無艱澀高深之處。...
章節試閱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一九七五年
十一月二日
他們盛情邀我加入內在寫實派。我當然也就答應了。沒有什麼入會儀式。那樣還更好。
十一月三日
其實我都還沒搞清楚什麼是內在寫實派。我今年十七歲,名叫胡安.加西亞.馬德羅,是法學院一年級的新生。本來我是想讀文學,但叔叔堅持要我學法律,最後我只好讓步。我沒有爸媽,有朝一日會成為律師,我就是這麼告訴叔叔嬸嬸的,然後關在房裡哭了一整夜,就算沒一整夜至少也哭了很久。之後,彷彿是下定了決心,我開始到法學院那幾棟令人肅然起敬的大樓裡上起課來。然而才過了一個月,又跑去選修文學系胡里歐.塞薩爾.阿拉莫開的詩歌研習班。就是在這個班上結識了那幫內在寫實主義者,也可稱之為內在的實現主義者,甚至他們有時也喜歡自稱是一肚子壞水的實現者。到今天為止,我已經去詩研班上了四堂課,什麼事也沒發生,當然說是這麼說,總還是有點什麼事發生:我們在班上朗讀自己寫的詩,阿拉莫要嘛就大加讚賞,不然就當場撕爛,視他心情而定。一個人上來讀詩,阿拉莫就評論一番,另一個人再讀一首,阿拉莫又評論一番。偶爾阿拉莫不耐煩了,就叫我們(當時還沒輪到朗讀的)也來互相品評,我們一邊評,他自己就看起報紙。
這倒不失為防止我們這些學員結為朋友的一種絕佳手段,就算勉強做了朋友,友誼基礎構築在積怨之上,總有嫌隙。
我也不覺得阿拉莫真懂得什麼評論,儘管他口口聲聲都在談文學評論。其實,我想他純粹只是說說嘴罷了。他可能還懂得什麼是迂迴修飾法。雖然談不上精通,但畢竟懂點吧。不過五音步詩(人人皆知這是古詩格律中有五個抑揚音步的詩體)他可就不懂了,他也不懂什麼是nicharchean(類似phalaecean的詩句)、什麼是tetrastich。我怎麼知道他不懂的呢?因為在第一堂課上我開口提問就造次了。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是怎麼想的。在墨西哥只有一個詩人對這些格律爛熟於心,他就是奧塔維奧.帕茲(我們偉大的對手),其他人全都不甚了了,至少當我加入內在寫實派,他們把我當自己人擁抱後,沒過幾分鐘烏里塞斯.利馬就是這樣告訴我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向阿拉莫提這些問題顯示我何其魯莽。最初我以為他是微笑稱許。後來才明白那其實是輕蔑。墨西哥詩人(我想詩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無知。可是我不為所動,他在第二次討論課上撕了我幾首詩之後,我問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 。阿拉莫以為我是在幫自己的詩壯聲勢,開始滔滔不絕地大談客觀批評(算是換個話題),說這是每個年輕詩人都必須跨越的雷區,但我打斷他,聲明有生以來這短短幾年還從來沒要求別人,得把我那些還很粗淺的作品當一回事,然後重提剛剛的疑問,這回竭盡我所能把問題表達得清清楚楚。
「不要向我提這種垃圾問題。」阿拉莫說。
「教授,rispetto是一種抒情詩,既要顯得浪漫又必須精確,有點像詩樂曲,共有六行或八行含十一個音節的詩句,前四行採用serventesio的形式,後幾行由押韻的聯句構成。例如……」我打算給他舉一兩個例子,阿拉莫跳起來打斷我的話。後來發生的事情有些模糊(雖然我記憶力不錯):我記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個學員放聲大笑,我想他們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換了別人大概從此就會不再來上課了,雖然記憶如此令人不快(或許是心情不好造成的失憶,這至少跟把發生過的事悉數記住同樣悲慘),過了一星期,我照常準時出現在詩歌班的課堂上。
我認為是命運帶我回去。這是我第五堂上阿拉莫的課(不過也很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課,因為近來我發覺時間可以隨意伸縮),班上氣氛肅殺,那種悲劇的交流電,在空氣中伸手可觸,可是誰也說不上來這是怎麼回事。從一開始,我們全體學員,最初選修這門課的七個學徒詩人都出席了。這種情況在其他任何討論課上都不曾有過。我們都感到有點緊張。連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麼氣定神閑。那一刻,我想到也許大學出什麼大事了,也許發生了一場我暫時還沒有聽到的校園槍擊案,也許發起了意外的罷課運動,也許系主任被暗殺了,也許他們綁架了某位哲學教授。當然,這些都屬於不實的臆測,壓根就沒什麼好緊張的。沒有任何客觀上的理由。不過詩歌(真正的詩歌)恰恰就像這樣:你能感覺到它,你能感覺到它就在空氣中,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某些高度敏感的動物(如蛇、蠕蟲、老鼠和某些種鳥)能覺察出地震的兆頭。後來發生的事情一團模糊,不過我不怕人笑我陳腔濫調,想說那有點妙不可言。兩個內在寫實主義詩人走進教室,阿拉莫不太情願地做了番介紹,其實他跟其中一位只是泛泛之交,對另外一位僅僅知道點名氣,或者僅僅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或者只是聽別人說起過,但他仍然向我們做了介紹。
我不清楚他們怎麼會上這兒來。這次拜會顯然滿懷敵意,但又不乏宣傳和招降的意味。起初這兩位內在寫實主義者還很矜持,阿拉莫試圖裝得彬彬有禮同時略帶諷刺,要等著瞧下面的戲。兩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慫恿他開始鬆懈下來,半小時後課堂氛圍恢復常態,就在這時戰鬥開打了。內在寫實主義者對阿拉莫的批評體系發出質疑,他回應指責兩位內在寫實主義者是半吊子的超現實主義者和偽馬克思主義者。班上居然有五個學員支持他,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支持他,除了我和一個瘦骨嶙峋的孩子,這個孩子總是抱著一本路易斯.卡羅爾 的書,從不發言。說真的我頗感驚訝,因為那幾個毅然決然支持阿拉莫的學生被他批評得最嚴厲了,現在卻紛紛現身成了最大的支持者。這時我決定給批評聲浪加點力道,指責阿拉莫連rispetto都不懂,兩位內在寫實主義者極其大度地坦承他們也不懂,不過我的意見讓他們覺得非常切中要害。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其中一個問我多大了,我說十七歲,然後又試圖從頭再解釋一遍什麼是rispetto。阿拉莫惱羞成怒,同學也都說我太愛掉書袋了(其中一個還管我叫書呆子);有了兩位內在寫實主義者替我幫腔,我一時衝動追問阿拉莫和全班同學,有誰還記得什麼是nicharchean和tetrastich。沒有人答得出來。
出乎我的預期,這場爭執並沒有導致全面圍剿。我得承認,我倒是很想被圍剿看看。雖然有學員揚言有朝一日要揍烏里塞斯.利馬,最後也不了了之,我是說,沒有挑起什麼暴力事端,儘管為了回應他們的威脅(我再次重申,這個威脅並非衝著我來)我把話放出去說要是誰想單挑,校園裡隨便什麼地方、哪一天、任何時間我都奉陪。
那堂課結束得出乎意料。阿拉莫向烏里塞斯.利馬發出挑戰,要求他讀一首自己寫的詩。這可正中利馬下懷。他從夾克口袋掏出幾張髒兮兮、皺巴巴的紙來。噢,別這樣,我心想,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們設好的陷阱。我想,為了不想目睹這傷心至極的尷尬,我應該閉上雙眼才是。這裡時而吟詩賦詞,時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見,這回應該是後者了。不過正如我說過的,我閉上了雙眼,這時聽到利馬清了清嗓子,然後又聽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有沒有辦法真的聽到這種東西,我表示懷疑)落在他四周,我終於聽到他的聲音了,開始朗讀我平生聽過最好的詩歌。後來,阿圖羅.貝拉諾站起來說他們正在找志願為內在寫實主義者辦的雜誌做點事的詩人。本來在座的個個都巴不得想做這份志願差使,經歷了這場衝突後這幫人都乖得像綿羊似的,誰都隻字不提了。上完課後(比平常晚點結束),我跟利馬和貝拉諾一起走到公共汽車站。時間已經太晚。街上車輛寥寥無幾,我們決定搭一輛叫客小巴去雷福馬大街,到了那兒後我們又走進位於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裡暢談詩歌,坐到很晚。
我還是沒搞清楚。這幫人給自己的流派這樣命名有點像在開玩笑。但同時,這麼自稱又是全然的真誠。我想到多年前,墨西哥有個前衛團體也叫內在寫實主義者,但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作家、畫家、記者還是革命家。他們活躍於二○年代,或者也可能是三○年代,我不很確定。很顯然我以前沒有聽說過這群人,但這可能得怪我自己文學知識太貧乏(這個世界上出版的每本書都還有待我去一一閱讀)。據阿圖羅.貝拉諾說,那幫內在寫實主義者後來去了索諾拉大沙漠之後,便不知所終了。貝拉諾和利馬還提到西莎莉亞.蒂納赫羅或蒂納哈的詩人,我記不清楚了(我想那時我正衝著服務員喊,給我們端些啤酒來),還談到洛特雷阿蒙伯爵 的《詩集》,以及書裡跟那個叫蒂納赫羅的女人有關的東西。後來,利馬提出一個頗為費解的講法。他說,當代內在寫實主義者只是在倒退走。你所謂的倒退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倒退走就是盯住一段距離之外的某個點,可是離它愈走愈遠,筆直朝著不知道哪裡而去。」
我說這種走法聽上去似乎挺不錯。其實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你要是停下來仔細想想,這根本就沒辦法走。
後來又有幾個詩人現身。有些是內在寫實主義者,有些不是。大夥兒盡情放浪形骸。我開始還擔心貝拉諾和利馬跟每個湊到我們這桌的怪胎說話,忙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時候,他們邀請我入夥。他們沒有說什麼「圈子」或「運動」,而是說「入夥」。我喜歡這點。我說,那好吧。一切就這麼簡單。貝拉諾握著我的手說,從現在起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了,然後我們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個過程就是這樣。這首歌的內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鎮和一個女人的眼睛有關。我在出去嘔吐之前問他們,歌裡說的眼睛是不是西莎莉亞的眼睛。貝拉諾和利馬盯著我說,看來我已經不折不扣是個內在寫實主義者了,我們幾個聯合起來勢將改變拉丁美洲的詩壇現狀。早晨六點鐘我又上了一輛叫客小巴,這次是我一人坐了,回到林達韋斯塔區的住處。今天沒去上課。一整天都待在房裡寫詩。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一九七五年
十一月二日
他們盛情邀我加入內在寫實派。我當然也就答應了。沒有什麼入會儀式。那樣還更好。
十一月三日
其實我都還沒搞清楚什麼是內在寫實派。我今年十七歲,名叫胡安.加西亞.馬德羅,是法學院一年級的新生。本來我是想讀文學,但叔叔堅持要我學法律,最後我只好讓步。我沒有爸媽,有朝一日會成為律師,我就是這麼告訴叔叔嬸嬸的,然後關在房裡哭了一整夜,就算沒一整夜至少也哭了很久。之後,彷彿是下定了決心,我開始到法學院那幾棟令人肅然起敬的大樓裡上起課來。然而才過了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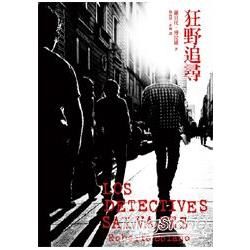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