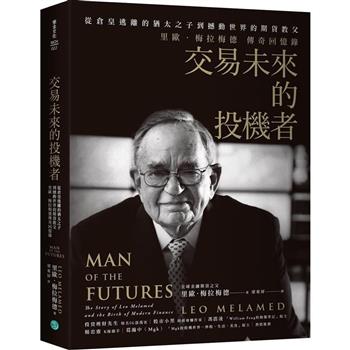序
該怎麼談人類遷徙這個複雜又充滿爭議的議題?以前對此感興趣的大多是學術界的人,例如古生物學家、人口統計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但這個議題現在成了目光焦點,經常成為政治激辯和論爭怒火的中心。
本書包含四十四個子題,意在提供對於這個主題的總覽(overview),法語稱作「tour d’horizon」。很多子題是我選材時自然浮現的:人類從什麼地方開始遷徙?什麼時候遍布全球?為什麼有些人選擇移動,另一些人卻決定留在原地?遷徙有哪些種類?移民潮擋得住嗎?由於本書在空間上涵蓋全球、在時間上縱貫人類史,我會用實際而明顯的例子說明,勾勒出這整個宏大的故事。
為這個領域書寫任何總論式作品,都很難迴避強制遷徙的重大案例(如大西洋奴隸貿易、亞洲契約勞工與難民潮),也必須寫下戲劇化的自願遷徙故事(例如歐洲人從一八七○年代到一次大戰之間大量移民美洲、殖民澳洲,以及其他屯墾案例)。由於政治衝突也是引發遷徙的重要因素,本書有專章敘述印巴分治、流亡與離散(diasporic)族群、以色列首次成為「聚集」(ingathering)猶太人的家園的過程,以及逃往加薩(Gaza)和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巴勒斯坦人的流亡處境。我們也會看到冷戰移民的政治。
移民經常是為了尋找工作機會。很多國家在大規模開礦和工業化之後,常常需要從更遠的地方徵募勞工,以填補本地勞工的不足。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美國有很多不同案例、英國工廠與南非的鑽石與黃金礦場也有大量人力需求,中國的製造業重鎮更吸納了數以百萬的農民。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各國為了快速重建經濟,急需徵募外地勞工:英國在大英國協(Commonwealth)廣徵工人,從加勒比海、印度和巴基斯坦引進當地的剩餘勞力;西德的主要移工供應國則是土耳其。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波灣產油國舉凡醫院、大學、博物館、購物中心等大型基礎建設,幾乎全都出自東南亞勞工之手。
除了企業和國家徵募的勞工輸入之外,也有由國家支持的移民發展。菲律賓是這種大規模勞工輸出的先鋒,他們在訓練船員和醫療照護人員出國工作上極具長才,而且發展得相當成功。現在,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船員是菲律賓人。這種策略的核心概念是:在外國或海上工作的國民匯回來的錢,能超過在國內訓練他們的費用。印度也是如此,他們訓練大量工程師和資訊人才以供「出口」,不但額外得到促進國際企業發展的下游效益,也吸引投資回流。不過,儘管勞力輸出有菲律賓和印度這樣的正面案例,失去受過教育和技術訓練的勞工常常讓更小、更窮的國家陷入困境。本書也會談到這類人才外流的負面案例。
在許多移民國家的民眾和政治人物眼中,不受控制的移民是危險的。他們不但會與本地人競爭工作、住房和其他服務,也會對既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風俗造成威脅。雖然這些威脅往往被過度誇大,但本地人往往對此相當敏感,並因此試圖控制移民的動向,尤其是不受規範的流動。
除前述主題外,本書也會談到一些影響遷徙研究的重要特定議題。看待人類遷徙的一項重大改變是:我們不再把遷徙本身看做獨特的現象,而是將它視為整體「移動典範」(mobilities paradigm)的一部分。1這種看法認為:人類在世界上的流動,相當於貨品、資源、金錢、圖像、污染、毒品、音樂、資訊(data)和許多其他當代生活面向的流動,也與這些流動關係密切。對遷徙研究者來說,把視角轉往移動(mobility)的諸多面向,意謂著關注移動本身,同時放棄對於「移民」較為嚴格的定義(人為工作而移動,並定居一段時間)。本書在選材上也強烈反映了這種轉變,除了其他主題外,我也會談到音樂、游牧民、傳教者、朝聖者、軍人、探險家、留學生、孩童、退休者和觀光客等等。
這種理解遷徙的方式比以前寬廣,我盼望讀者不致因此困惑,反而能從中發現嶄新而有趣的面向,進而刺激思考。我在選材過程中得到許多樂趣,也盡力讓這些例子在清楚易懂之餘,也不錯失其錯綜複雜的一面。
羅賓.柯恩(Robin Cohen)
牛津,二○一九年六月
【圖:移民離船登岸,在紐約開始新的人生。】
*****
第十九章
越南船民
一九七五年四月,隨著越共取得軍事勝利,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崩潰,越南人大舉出逃。越南人口裡的很多華人被認為是可恥的資本主義政權共犯,他們的商店被關閉、財產被沒收。面臨必須下放農村的命運,新統治者要求想離開的人留下買路錢,許多人決定破財消災,選擇買下出國許可,遠走他鄉。1
【圖:在海上漂流八天之後,擠在一艘小漁船上的三十五名越南船民等候救援。】
從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五年,二十年間,選擇離開越南的人約在兩百萬之譜,其中約有八十萬人是「船民」。雖然船民占不到移出者的一半,但因為他們經常搭乘超載又不適合遠航的船隻,一路險象環生,所以往往成為大眾目光焦點。
船民的第一站是四周的亞洲國家(香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新加坡和泰國)。抵達之後,他們會先被安置在難民營或拘留所。有些人會留在當地,但很多人會繼續前往英國、美國、法國、澳洲或其他國家,在那裡定居下來。這段時期進入尾聲時,由於越南政府從國家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當年離開的難民中有幾萬人自願返回越南。
香港
每個地方接收、協助、支持越南船民的動機各異。因為最早離開越南的是華人,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大眾普遍同情他們的遭遇。由於他們多半反共,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對他們尤其心有戚戚(但香港也在一九九七年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陳國賁指出,儘管香港人口非常稠密,可是在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五年這段期間,港府為照顧船民的開支是港幣六十六億三千八百萬元。相較之下,英國在這個部分的開支是港幣八億四千九百萬元,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則是港幣十二億五千三百萬元。2
【跨頁圖:一九七五年峴港淪陷兩天前,最後一艘載滿著驚慌失措的難民貨輪,從這裡離開。】
法國
在越南船民最後定居的國家裡,有三個與中南半島具有千絲萬縷的牽連,以致它們對船民負有一定的道德責任。法國就是如此。在一九五四年被共黨逐出越南之前,法國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和柬埔寨)一直設有殖民地總督。在法國殖民末期,約有三十萬名越南人移民法國。一九七五年西貢淪陷後,前來法國投靠親友的越南人迅速暴增。現在林立法國的美味越南餐廳,十分具體地提醒我們這批越南人的故事。
美國
越南難民之所以會在美國落腳,與越戰對美國帶來的創傷有關。為了抑制共產主義在亞洲崛起,美國在越戰中失去了五萬八千兩百二十名子弟兵。美國不但為此長期陷入政治對立,也留下沉痛的心理傷痕。於是,接收越南船民多少成了他們止痛療傷的方式。雖然美國接收越南人的動機一開始是政治性的,但有研究指出:這種作法長期來看也為美國帶來經濟利益。
【圖:河粉(phở),這種著名的小吃結合了越南米粉,經常搭配法國牛肉薄片,以及用大骨和牛尾熬煮的湯頭。】
一般說來,移民有助於促進移入國和他們故鄉之間的貿易,因為他們語言溝通無礙,也熟知檯面上和檯面下的「遊戲規則」,而且有可以信賴的網絡能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克里斯多福.帕森斯(Christopher Parsons)和皮耶─路易.維其納(Pierre-Louis Vézina)從這個角度出發,做了一個「自然實驗」:他們觀察越南船民及其後裔在美國的分布情形,以此比對一九九五年解除制裁之後的對越貿易。結果發現:越南人網絡每增加百分之十,美國對越南的出口貿易額就增加百分之四點五到十四;在美國如果越南人口增加一倍,出口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到一百三十八。3
英國
越南船民子弟為美國經濟帶來正面貢獻,在許多他們生根的國家,學業表現也比當地人和其他民族優異,在英國也是如此。英國從殖民地香港接收了一些越南人。根據二○○二年在倫敦南華克(Southwark)所做的調查,越南裔學生有四成七左右拿到五門A*到C的成績,白人英國學生則只有三成四。不過,雖然越南裔學生整體來說表現較好,可是性別差異不容小覷:越南裔女生的成績明顯優於越南裔男生,後者似乎擔心要是被當成「書呆子」,就無法和同儕「當哥兒們」,所以畫地自限。4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羅賓.寇恩的圖書 |
 |
$ 338 ~ 495 | 看得見的人類大遷徙:44個代表性主題,透過影像與資訊圖表,勾勒出人類移動的複雜歷史與多元樣貌
作者:羅賓.寇恩(Robin Cohen) / 譯者:朱怡康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1-09-02 規格:穿線膠裝 / 全彩 / 264頁 / 17cm×22cm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看得見的人類大遷徙:44個代表性主題,透過影像與資訊圖表,勾勒出人類移動的複雜歷史與多元樣貌
若人類遷徙的歷史如此古老,為何這個議題在今日變得如此敏感與棘手?
牛津大學羅賓•寇恩教授在「移民研究」居執牛耳地位,
本書橫跨歷史,悠遊世界,豐富「遷徙」的意義,
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急迫的議題之一提供清楚的脈絡、賦予色彩。
▋ 內容簡介
深入淺出的敘述 x 鏡頭攝影歷史瞬間 x 精實的數據資料 x 生動的圖表 x 真實人物小故事
人類的歷史,就是由無數的遷移匯聚而成。但近年來移民議題占滿媒體標題的現象,誠屬前所未見。移民為什麼離開,將到何處?移民會威脅到社會和政治秩序嗎?他們提供的一定是勞力嗎?移民是否有助於母國發展?移民能提高消費需求和創造財富嗎?移民潮可能擋下嗎?這本書記錄人類遷徙的豐富樣貌,蘊含這些重重疑問的解答。
雖然我們難以直接替「遷徙」畫出明確的分類界線,但書中仍盡可能涵蓋各種類別的移民,包括探險家、奴隸、朝聖者、礦工、勞工、流放者、難民、性工作者、國際學生、觀光客、退休人士和僑民等,並深入特定主題(例如:難民問題的可能解方、兒童與遷徙);也嘗試帶入較新的學術視角,包含物質史(音樂傳播的歷史)、離散研究(diaspora),觀光產業等。
▋ 打開眼界 • 共同推薦 (依姓氏筆畫排列)
周維毅|公民教師
林立青|作家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張 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創辦人
曾嬿芬|台大社會學系教授
楊博安|臺中二中 公民科教師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蕭唯善|文華高中 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蕭宇辰|「臺灣吧 Taiwan Bar」執行長
▋ 三大必讀原因:
一、【主題廣博,選材經典】
#本書是社會的、歷史的、地理的、也是當代公民須知。跨領域且深入淺出的書寫方式,帶出後續思考餘韻。
全書分四大主題(詳見目錄):
A.人類早期重要的遷移模式:
如早期宗教、帝國、太平洋島民
B.歷史中的遷徙:
如愛爾蘭大飢荒、澳「十磅內地人」、以巴問題、德國土耳其移民、後蘇聯移民、納粹難民、海外華人
C.當代遷徙:
如中國戶口制度、專門發展移工的國家、流亡、性工作者、冷戰政治移民、地中海難民、全球公衛工作者
D.遷徙的困境與爭議:
如音樂隨移民的傳播路徑、婚姻移民、氣候變遷導致的遷徙、兒童與移民問題、難民政策的可能解方
二、【知性與感性並陳】
包含經典攝影照片、資訊圖表、真實人物現身小故事等。
#照片授權費用昂貴,此書蒐羅圖片包羅萬象。一書在手,讓您心靈富有!
#眾多資訊圖表,透過地圖與數據呈現,不僅一目了然,複雜的圖表還能練習識讀與解讀能力!
#除了正文敘述,還有更多補充BOX故事欄位,不論是多一些反思、提供額外資訊,或是讓大遷徙時代下的小人物親自現身說法!
三、【遷徙,原來離我們那麼近】
「遷徙」不僅包含難民議題或移民政策(築牆或其他地區的移民政策與現狀,或討論台灣是否提案建立《難民法》等),其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近。
包括新聞播報(還記得2017年中國政府在冬天驅離北京「低端人口」),電視節目(像緯來日本台「移居世界秘境日本好吃驚」),只要打開遷徙之眼,就會看見日常生活處處充滿移動的軌跡——通勤火車、「小緬甸」、出國念書的隔壁鄰居、港式燒臘店、以往金門人的南洋商業、並肩等紅綠燈時騎著電動腳踏車的移工、巷子口早餐店、充滿爭議的亞洲鬼才黃明志 namewee創作歌曲、到台灣本島或北部升學求職的國小同學、美味越南河粉……說到遷移就想起了彼方的朋友、家人,或者,就是看到最後這句話的你/妳自己。
作者簡介:
羅賓.寇恩Robin Cohen
牛津大學國際移民研究所前任所長及榮譽教授。曾在奈及利亞、加勒比海地區、美國、加拿大、南非和英國擔任學術職務,也在其他多國做過研究。柯恩教授專精於國際移民及其文化與社會影響,是英國該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先前著作包括《身分認同的前線:英國人與他者》(Frontiers of Identity: The British and the Others)、《全球離散導論》(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和《移民及其敵人》(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等書,現在也為部落格The Conversation寫文章。
譯者簡介:
朱怡康
專職譯者。譯有《為神而辯》、《塔木德精要》、《二十一世紀生死課》、《自閉群像》、《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也許你該找人聊聊》等書。
臉書專頁「靈感總在交稿後」:www.facebook.com/helpmemuse
章節試閱
序
該怎麼談人類遷徙這個複雜又充滿爭議的議題?以前對此感興趣的大多是學術界的人,例如古生物學家、人口統計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但這個議題現在成了目光焦點,經常成為政治激辯和論爭怒火的中心。
本書包含四十四個子題,意在提供對於這個主題的總覽(overview),法語稱作「tour d’horizon」。很多子題是我選材時自然浮現的:人類從什麼地方開始遷徙?什麼時候遍布全球?為什麼有些人選擇移動,另一些人卻決定留在原地?遷徙有哪些種類?移民潮擋得住嗎?由於本書在空間上涵蓋全球、在時間上縱貫人類史,我會用實際而明顯的例...
該怎麼談人類遷徙這個複雜又充滿爭議的議題?以前對此感興趣的大多是學術界的人,例如古生物學家、人口統計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但這個議題現在成了目光焦點,經常成為政治激辯和論爭怒火的中心。
本書包含四十四個子題,意在提供對於這個主題的總覽(overview),法語稱作「tour d’horizon」。很多子題是我選材時自然浮現的:人類從什麼地方開始遷徙?什麼時候遍布全球?為什麼有些人選擇移動,另一些人卻決定留在原地?遷徙有哪些種類?移民潮擋得住嗎?由於本書在空間上涵蓋全球、在時間上縱貫人類史,我會用實際而明顯的例...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致謝
序
第一部 遷徙模式
第一章 遠離非洲:早期人類
第二章 探險家:阿拉伯人、中國人和歐洲人
第三章 古代宗教與遷徙
第四章 游牧:從無首領型社會到帝國
第五章 羅姆人與遊居者
第六章 液態大陸:太平洋群島的住民
第七章 大西洋奴隸貿易
第八章 印度契約勞工
第九章 帝國:勞力來源與軍事政權
第十章 朝覲:伊斯蘭「五功」之一
第二部 近代歷史中的遷徙
第十一章 愛爾蘭外移潮與「饑荒大出逃」
第十二章 南非礦工
第十三章 從罪犯到「十鎊內地人」:澳洲的英國移民
第十四章 湧向美國的「大西洋...
序
第一部 遷徙模式
第一章 遠離非洲:早期人類
第二章 探險家:阿拉伯人、中國人和歐洲人
第三章 古代宗教與遷徙
第四章 游牧:從無首領型社會到帝國
第五章 羅姆人與遊居者
第六章 液態大陸:太平洋群島的住民
第七章 大西洋奴隸貿易
第八章 印度契約勞工
第九章 帝國:勞力來源與軍事政權
第十章 朝覲:伊斯蘭「五功」之一
第二部 近代歷史中的遷徙
第十一章 愛爾蘭外移潮與「饑荒大出逃」
第十二章 南非礦工
第十三章 從罪犯到「十鎊內地人」:澳洲的英國移民
第十四章 湧向美國的「大西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