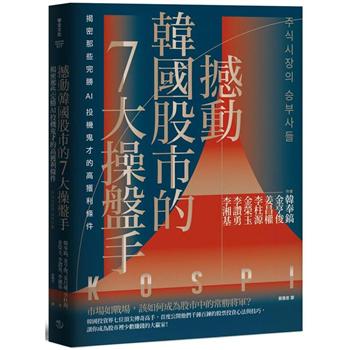序一:當年確信今猶信歲月蹉跎且梭巡/許迪鏘
一九八七年十月,肯肯給一位朋友在她剛出版的《當年確信》扉頁上寫了幾句話:「婚姻與孩子揭開你的新一頁,我也預備好了,因為大家幫我把過去灰暗的日子都釘裝起來,揭揭都過去了。」揭開婚姻與孩子新一頁的,正是我的妻子,我們的兒子剛在五月出生。「我也預備好了」,預備好了甚麼?至少我並不十分明白,後來自然知道,她也將踏上婚姻之路,這條路很長,由香港一直延伸到英國倫敦。
那時大家仍為《大拇指》憚精竭力,儘管財政上捉襟見肘,精神上早已透支,但已沒有像初期那樣,隔不多久便討論能不能、應不應繼續出下去,都準備了有一期出一期,直到有一期在我手上遲遲沒印出來,大家都不催不追,彷彿都有一個默契,不出就是沒有了。那是一九八七年二月。我常安慰自己,不想有停刊一日的來臨,卻又期待已久,隔了幾個月再出,不但大大脫期,也好像有違大家的期待。那真是充滿所有可能的矛盾的年輕歲月,回頭再看,不得不有點驚心。
我很善忘,但在這段年輕歲月中有一件事我倒印象深刻。大拇指同人都很木訥,去老大、肯肯或夏潤琴家「聯誼聚會」,往往是在書架和報紙刊物堆摷一會,便各自佔領一角,埋頭翻書揭報,悶蛋得很。有一段時期在也斯家當編輯部,在那兒開會、排版、摺報紙寄訂戶。都是有必要的話便說,否則無言相對,自顧自做事。有一天下午,應是一個周末或周日,大家在排版呀甚麼的,肯肯遲來,身旁卻有一位男士,說是出海回來,順道來看看。姓名也許介紹過,但沒怎麼說話。大家繼續工作,也沒說甚麼,頂多是偷眼望,心裡有某種不宣的言說。那以後,大家(也許應該說我)若有所待而終歸消寂。好些日子後,肯肯的故事翻過了新的一頁。
這些往事,本來無須重提,但肯肯寫了,我便釋然,雖然並不肯定,《綠苔》裡所寫的「你」,跟當天我們所見是不是同一個人。流水光陰,年輕時我們都有過不同的追尋,we chose it, win or lose it,恐怕是失落的多,能握在手中的,自當珍惜,努力於茲。我很高興讀到這篇文章。
一九九一年肯肯寄給我們一張她初生女兒的照片,照片上的日期是Aug 13 ‘91,照片背後這麼寫:「爸爸媽媽說他們仍掛著『L』牌揍女無暇寫信,因為手忙腳亂,烏眉瞌睡,所以我來向叔叔姨姨請安!鍾晴」。鍾晴的晴字,我們不難聯想到「道是無晴卻有情」的「情」,這個初掛學字牌的母親,當是個有情的人。小晴的英文名Julia又如何?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星期日大拇指電影籌款(感謝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庫的存檔,要不,我哪來記性記得這麼精確),放映的就是《Julia》(在凱聲戲院,樓上二十元,樓下十二元、十五元)。反納粹分子茱莉亞,由雲妮莎列格芙飾演,一個獨立而堅強的女子,她的好朋友莉莉安(珍芳達飾)是個作家,一天向她哭訴,說寫不出東西,怎辦?茱莉亞說,寫不出東西沒甚麼大不了,去餐廳捧餐,一樣可以生活。一齣電影,我記得的就是這句話。Julia會不會來自這電影?我常懷疑。肯肯提醒我,原來我曾寫電郵問過她,還自作聰明的解釋,是英國惡劣的天氣,需要陽光照亮你們的生命?Julia其實也就是July,她生於七月。
幾年前肯肯回港,和她喝了一頓茶,那時我和江瓊珠在已結束的數碼電台有個讀書節目,想請她做訪問,江問:認識肯肯的有沒有一百個人?我說恐怕沒有。江又問:咁佢有冇故仔。當然有,我說。那次和肯肯的會面,我卻完全沒有提訪問的事。會面後,我有一段簡短的紀事:
「見了肯肯,談了半個下午,對連打個電話也怕的人(我何嘗不一樣),我決定放過她。我們談的主要還是兒女和家人。肯肯說,女兒在大學讀音樂,小提琴每次拉完聽眾都讚好,可她不喜歡獨奏,說不習慣under the limelight(太像她的母親),只想加入樂團,或小組演奏,又因喜歡寫作,畢業後想做個music journalist。That’s fine,母親說。可有一次,她看到有人做出一個哈里波特城堡蛋糕,就立志整餅,做一個artist baker。That’s fine,母親說。她的女兒,現在自稱為the aspiring baker(立志做個烘焙師的人),有一個博客:theaspiringbaker.wordpress.com,記錄了她在整餅路上的每一步。我這個叔叔必須弄好身體,希望有一天,能吃盡她餅店裡的所有蛋糕。」
本書的讀者應該知道,茱莉亞刻下在一家五星酒店當大廚副手(肯肯補充:已於去年中辭任,話要離開 fine dining 一陣。現在任 icer 替 bespoke handmade biscuits 畫花樣,在公司內專責design and development)。她的博客,不再叫「立志當烘焙師的人」了,改稱A Life Imperfect(未完成的人生:ofnotesandsilence.wordpress.com),文藝氣息應承襲自母親吧。最新(寫此文時)的帖文寫她在海德公園聽Carole King的情景和感受:
「The evening has grown dusky and the air is cooling after the day’s scorching sunshine when Carole King looks out at the vast crowd gathered in Hyde Park and begins to play You’ve Got A Friend.
All around me, people sway in time to the music, putting their arms around friends and loved ones, holding hands and revelling in the wonder of this moment. More than a few are crying too, tears of joy rolling down their cheeks, mopped up with sleeves even as they laugh and grin.
“I like it when you sing,” Carole says, and it is a heady, magical moment as fifty thousand people raise their voices up to join hers.」(暮色四合,日間熾熱的陽光隱退,空氣漸涼。此時,Carole King望向簇擁在海德公園的人群,開始唱《你有一個朋友》。四周的人隨著音樂擺動,手臂纏著手臂,與朋友和相愛的人,手牽手沉醉在這一刻中。許多人也在哭,歡欣的眼淚流下臉頰,用衫袖揩乾,臉上掛著笑容和開懷露齒。卡露京說:『我喜歡你們一起唱。』五萬人那就吊高嗓子跟她一起唱,真是振奮人心的美妙一刻。)
茱莉亞肯定也會是個稱職的music journalist。
我和肯肯其實不算很熟(套用我在《我們都在讀西西》裡劈頭第一句話:我同西西唔係好熟),不熟的意思是我對她的個人生平所知其實不多,只是通過作品認識、感受她的心路、情路。情在這裡是個泛指,包括對親人、愛人、女兒、朋友、鄉土、鄰里,以至日常生活事事物物的情。她的文字很輕巧,情卻是濃重的。說她的文字輕巧,是她愛用短句,如:
「十五年前,還在倫敦西部,生活上遇挫折,失業,也失去自信。不肯就此屈服,尋尋覓覓,東北行九十四哩,另找駐腳處。」(《這十五年》)
「從前方圓卅哩只有一超級市場,時移世易,今時今日,總有一間喺左近,薑蔥蒜都有,不過,九十便士一粒蒜頭,來了廿四年,我仍要折算,嘩十蚊粒。」(《難為無米炊》)
「今夜月明,千里迢遙,但願,人長久。」(《今夜月明》)
「問路,竟然感到為難。有人寧願團團轉繞圈也不肯停下來,開口,問取指引。是羞怯性格內向拘謹,怕與陌生人,打交道;還是不願,示弱呢?不去問,得不著。不是嗎。」(《問路》)
這些短句各有作用,或表示一步一足印的生活困境,或生活逼人的氣急敗壞,或一字一頓的至誠祝禱,或怯怯懦懦的怕生。不純粹是以獨特的句式「吸引眼球」,而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這種句法,用得不好,會顯得造作生硬,肯肯用得純熟自然,且自一九八七年的《當年確信》,二○○四年的《眉間歲月》以來,便如是,是她的signature,之一。
我們也自然會注意到,文字中粵語的運用,以及粵語流行曲(很「老餅」的那些)曲詞的無縫鑲嵌。我認為立意很清晰:鄉音無改鬢毛催。示不忘本的意思。
卡爾維諾說,空的水桶才能盛水,因其輕,才能載重。肯肯的文字輕盈,底裡卻莫不是厚重的情意。她的記事是片段式的,中間留有不少空白,讀者若能用同情、同理心予以填補,自然有更深的體會。
也許,我還是以對肯肯有限的認識,補充一點她的生平事實,這樣,或有助讀者串連書中的細節,對她的time line能有較具體的理解。
肯肯,在港時任職銀行,由櫃員開始至 Start up ATM Service 至放款部至培訓至 Credit Analyst。年輕時已在《年輕人世界》寫專欄,主編海滴,同期「欄友」據說還有阿屈(Edward Lam,林奕華)云云。後加入《大拇指》當文藝版編輯,一九八○年代末婚後移居英國,歷年時有回港探視親友。所居為一小鎮,曾有一段時期只能用電話線上網,因資訊科技公司要求一地至少有二百戶人家才鋪設網絡,而該鎮不足此數。育有一女,丈夫外出工作養家,她在家工作持家。間中寫作,偶爾發表散文,曾把其中幾篇自譯成英文在一份中英並行的利物浦社區刊物《聚言集》發表,又曾參加創作坊,寫過一兩篇英文小說。博客和社交網站盛行,她再勤於揮(電子)筆,有網誌《歲月期期艾艾》,帖文都在大拇指面書轉載。現因工作離家獨居的女兒,無疑是她最大牽掛。
書名《昨日蹉跎》,我起初覺得有點灰,但細想,即使少數的那些名公鉅卿,活於名繮利鎖中,此我非我,又何嘗不在蹉跎歲月?自言蹉跎的,卻倒有幾分看透了人生。陸游《自嗟》:「勛業蹉跎空許國,文詞淺俗不名家。」以勛業自許,蹉跎就不全是自己的責任;文詞淺俗,是自取的,不名家,其實有點自成一家的沾沾自喜。我比較喜歡劉長卿的《北歸入至德州界,偶逢洛陽鄰家李光宰》:
生涯心事已蹉跎,舊路依然此重過。
近北始知黃葉落,向南空見白雲多。
炎州日日人將老,寒渚年年水自波。
華髮相逢俱若是,故園秋草復如何。
我們都是天地逆旅的過客,歲月蹉跎,無妨再梭巡一會,何須悵望故園,秋草可不是春風吹又生?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肯肯的圖書 |
 |
$ 288 ~ 320 | 昨日蹉跎
作者:肯肯 出版社:點出版(文化工房) 出版日期:2017-01-23 語言:繁體/中文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昨日蹉跎
生涯心事已蹉跎,舊路依然此重過
肯肯三部散文集,書名中「年」、「月」、「日」都有了。歲月如流,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就掌握當下日子好了。承接前兩部散文集,《昨日蹉跎》一貫以「情」牽繫年、月、日間的種種人和事,主要環繞初到異地所遇到生活上和心理上的衝擊,以至建立社區關係的糾葛,再下來自然是初為人母,並伴隨女兒成長的憂喜。輕盈的文字背後,隱見一顆仍然年輕的心,隨情緒的起伏而卜卜跳動,時而噓出一陣歎息,或一聲歡呼。粵語和粵語歌詞的穿插,無疑也是對故土的致意。
作者簡介:
肯肯
香港出生,中學畢業,任職銀行十六年。一九八八年婚後旅居英倫。曾任《大拇指》編輯。著有《當年確信》(一九八七年,大拇指出版社)、《眉間歲月》(二○○四年,素葉出版社)。
TOP
推薦序
序一:當年確信今猶信歲月蹉跎且梭巡/許迪鏘
一九八七年十月,肯肯給一位朋友在她剛出版的《當年確信》扉頁上寫了幾句話:「婚姻與孩子揭開你的新一頁,我也預備好了,因為大家幫我把過去灰暗的日子都釘裝起來,揭揭都過去了。」揭開婚姻與孩子新一頁的,正是我的妻子,我們的兒子剛在五月出生。「我也預備好了」,預備好了甚麼?至少我並不十分明白,後來自然知道,她也將踏上婚姻之路,這條路很長,由香港一直延伸到英國倫敦。
那時大家仍為《大拇指》憚精竭力,儘管財政上捉襟見肘,精神上早已透支,但已沒有像初期那樣,隔不多久便...
一九八七年十月,肯肯給一位朋友在她剛出版的《當年確信》扉頁上寫了幾句話:「婚姻與孩子揭開你的新一頁,我也預備好了,因為大家幫我把過去灰暗的日子都釘裝起來,揭揭都過去了。」揭開婚姻與孩子新一頁的,正是我的妻子,我們的兒子剛在五月出生。「我也預備好了」,預備好了甚麼?至少我並不十分明白,後來自然知道,她也將踏上婚姻之路,這條路很長,由香港一直延伸到英國倫敦。
那時大家仍為《大拇指》憚精竭力,儘管財政上捉襟見肘,精神上早已透支,但已沒有像初期那樣,隔不多久便...
»看全部
TOP
目錄
前言 序 / 許迪鏘
散文
‧筆影
(一)此心安處:常在心頭 /這一天/這十五年/綠苔/難為無米炊/三生有幸/夜月明/珍惜眼前/仁心,仁術/醫事/且慢/又到聖誕/記住也斯的笑臉/問路/活在當下/青雲有路自為梯/歲月無聲/昨日之路/今天又相見/外婆橋/想當年/人生路上/行行重行行/這樣便長大/吃虧就是便宜/時光苒荏/長憂九十九/點點樓頭細雨/焦慮/聖誕禮物/只要有日是好日/來,抱一抱/年又過年/歇腳處/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我其後來,有另一番風景/采之欲遺誰/愛是,親力親為/書卷多情似故人/花開的聲音...
散文
‧筆影
(一)此心安處:常在心頭 /這一天/這十五年/綠苔/難為無米炊/三生有幸/夜月明/珍惜眼前/仁心,仁術/醫事/且慢/又到聖誕/記住也斯的笑臉/問路/活在當下/青雲有路自為梯/歲月無聲/昨日之路/今天又相見/外婆橋/想當年/人生路上/行行重行行/這樣便長大/吃虧就是便宜/時光苒荏/長憂九十九/點點樓頭細雨/焦慮/聖誕禮物/只要有日是好日/來,抱一抱/年又過年/歇腳處/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我其後來,有另一番風景/采之欲遺誰/愛是,親力親為/書卷多情似故人/花開的聲音...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肯肯
- 出版社: 點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1-23 ISBN/ISSN:978988778453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開數:寬13 X高19(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