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
關於旅行與旅行文學,我們似乎談得太多又太少。
近十多年來,經濟力的提昇、全球化的願景、對異國的想像與緊張沉重的生活壓力,使旅行爆炸性地成為臺灣全民生活的「必要」,一種持續進行的集體儀式。而旅行所激發出來的全民書寫能量與敘述欲望在旅行寫作中找到了最鍾情的消耗空間,進而轉換為書店中琳瑯滿目的旅遊書籍、報章雜誌上目不暇給的旅遊資訊,形成巨大超強的旅行體系符號。
但是,「旅行文學」的定義是什麼?我們是否已經建構對「旅行文學」的認知?「旅行文學」是否可以無限上綱,涵蓋各種書寫?──觀光、出走、考古、田野調查、自傳、回憶錄、返鄉、流放、流浪、流離與移居遷徙、親身的實証經驗與憑空的想像遨遊?對於定義、認知、結構、主題與文類等種種問題,我們則談得太少又太淺。與這些問題直接密切關聯的便是寫作形式的問題,自覺性高的作家便發覺「我一直找不到適合我的遊記或旅行文學」,並慨嘆自己的旅行寫作「是令人困窘的書寫姿勢」(註一)。
我個人主張旅行是跨越疆界的行為,旅行寫作者在離開旅行地點的「直接現場」後,來到寫作的「間接現場」(註二),以文字再現旅行行為,表達跨越疆界的「行動」。而旅行寫作文本如何透過「行動」來彰顯「旅行」的旨意?衡量旅行者是否在旅行行為中跨越疆界,就必須以結構的觀點來看。旅行之所以與「流放」(exile)、「流浪」(wanderings)、「流離」(diaspora) 或「移居遷徙」(migration) 不同便在於旅行者終究將回到原先所出發離去的「家」。「家」的存在與回歸是旅行的觀念得以成立的前提;「家」也是旅行者得以衡量整個旅行過程的「得」與「失」的秤頭。旅行因此形成一往一返的圓形結構 (circular structure)。旅行的回歸點即出發點,兩者既相同重複,又在相同重複中產生差異。旅行的最高境界便是旅行者跨越「自我」(the self) 與(在旅行中相遇的)「異己」(the other) 之間的疆界,將封閉固著的空間轉化為自由開放,帶著「差異」回返家鄉。
然而就在旅行文學定義莫衷一是的同時,臺灣的旅行寫作者已經以一己的修辭、觀點與敘事主體書寫旅行經驗,呈現旅行文學多樣的內涵與多種可能的寫作形式。這本文選中所收錄的便是近一、二十年來臺灣旅行文學寫作的試驗與成果。
以焦桐〈遠足〉開啟旅行文選是因為「遠足」隱喻我們最初始的越界出走經驗,有如「汽笛離開港口/鐘聲離開教室/花穗離開鳳凰木/眼睛離開課本/皮鞋離開家」。在離家旅行的過程中,張曉風〈戈壁行腳〉的旅行者也離開自己,忘記自己,有如「我睡去,無異於一隻羊,一匹馬,一頭駱駝,一株草。我睡去,沒有角色,沒有頭銜,沒有愛憎,只是某種簡易的沙漠生物,一時尚未命名」。又因為放心自在,隨機隨緣,在蔣勳〈柯比意與貓〉中,旅行者發現一隻無事閒臥在教堂前的貓是建築師柯比意設計信念的一個 「轉喻」(metonymy),而去來之間,旅行則是生命歷程的「隱喻」(metaphor)。
但是,離開家,跨越邊界,離開自己,旅行者無所負擔地「輕鬆旅行」(travel light)(註三)的初衷往往產生變化。空間與文化的轉換使個人/集體的歷史、記憶反而無所不在地君臨現場,與異地的時空情境交互指涉,取而代之成為隨身行李。在張復〈西安〉中,到中國大陸探親造訪的經驗並不是印證了一個閱讀、想像的國度,而是以時空距離差異,詮釋個人過去與現在所處的多種隔閡文化 (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s),並進而建構新的情感結構。陳宛茜〈雙城記〉同樣以過去與現在、故鄉與異鄉 (臺灣與上海) 的對照為架構,發現是「記憶」重組了時間與空間、文字與情感、一切的一切,她於是「只能不斷地書寫書寫書寫,無法停止也不願停止」。許正平〈The Big Blue──在聖托里尼〉也在質疑「一切無非記憶……又有些什麼藉以保存我們之間那些獨一無二的記憶」之後,將答案歸於書寫:「讓我再度打開《憂鬱的熱帶》,在記憶之城的黃昏裡朗誦這段文字給你聽吧:『……那時我手拿筆記本,一秒一秒的記下我所看見的景象,期望能夠有助於把那些變易不居、一再更新的外觀形態凝住並記載下來』」。王天心〈倫敦‧在日落下的帝國本土〉觀察英國建築、暢銷書籍與百貨商品,發現跨國企業逐漸拭除在地的差異,日不落國首府倫敦逐漸失去一己的獨特場景。而旅行者最後籲請女王「庇護受倫敦文學澤被的外國子民」,正因為我們透過文本來暸解旅行,暸解世界,正因為「世界萬物終究在書本中落腳,體現其存在」(Stéphane Mallarmé)。
帶著「水壺和巧克力糖」(〈遠足〉)與生命潛在動能,旅行者進入世界,便「(故意)迷路了」,不願意被自己或他人限制,走得遠遠地,不願意停滯於任何一個定點方位:「你要去的地方,你一直故意找不到」(〈銀河鐵道〉)。「迷路」是偏離既有的「固著路線」 (rigid lines);「迷路」是在開放的空間中移動,開創有彈性的「可彎路線」(supple lines);「迷路」才能使回歸點與出發點之間產生「差異」,最後終於帶著「差異」回返家鄉,進而在家鄉的社會文化中驗證「差異」。「迷路回家」因此無疑是旅行文學重要的一章。這本文選中,旅行寫作者所寫就的「回家敘事」讓我們對臺灣旅行文學的發展充滿期待。例如愛亞的〈夢歸家〉以夢反襯家在旅行中的角色份量。席慕蓉的〈篝火〉所瞭悟的是:旅行並未結束於回程的終點,臺灣的淡水與蒙古高原其實相連成一張更完整更真實的心靈地圖。在〈回家〉中,師瓊瑜則寫臺灣的女兒自愛爾蘭與柬埔寨回來後,把她在異國所目睹的殺伐悲劇與臺灣社會的種種亂象加以比較,發現了自己的改變,發現差異,周遊各國的經歷使她在迷路回家後對「家」與自己的社會文化產生困惑。迷路回家之後,她回家迷路,必然還要再度離家出走。旅行者在回家後如何處理所發現的差異與自己的改變,是無法迴避的挑戰,也應該被包含在旅行敘事之內。郭力昕〈東非帝國主義觀光客〉就發現到自己做為一個外來者的觀看方式可議,他反思旅行行為,問道:「旅行,是有效地消除人們偏見、無知的一種學習經驗,還是強化了原來自覺或不自覺之文化本位心態的買賣行為?」但是郭力昕說他沒有答案。
「出發—離開—回家」的旅行結構在吳明益〈行書〉中代換成為旅行「三動」:「移動—互動—運動」。旅行者從臺北出發,騎自行車「移動」,離開自己,離開既有的框架:「這是一次嘲弄自己浮誇性格、削減自大體積、認清衰弱體能、蔑視意志、重審知識、都市、學院經驗的行旅」。在騎車環島移動的過程中,旅行者除了與臺灣單帶蛺蝶、山脈、海浪、梅山居民等異己「互動」以外,更以攝影與寫作的方式寄存記憶,記載差異與改變,進行無止盡的「運動」:「所謂行走已成一種幻夢、一種誘惑、一種癮,所謂行書是一種生命的韻律,停下即死亡」。吳明益回家後運動的成果之一便是〈行書〉。〈行書〉之後,吳明益仍然持續再出發,把圓形的旅行結構延伸為不斷向外拓展的螺旋結構 (spiral structure) 。
旅行寫作創造了旅行的記憶、或甚旅行的意義,但旅行寫作絕不只是旅行行為所成就的一項副作用產品而已。這本文選中所收錄的旅行文學作品本身自有其美學素質,十八位作家各自呈現其別緻風貌,令人欣賞,愛不釋手。例如舒國治〈香港獨遊〉是臺灣當代旅行文學中的驚豔之作。劉克襄〈支線火車的邂逅〉寫生命旅程中的片段偶遇,素樸的筆觸把讀者帶到真誠感人的生命現場。……讀者閱讀的美感經驗將使這些旅行寫作成為永久的珍藏品。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胡錦媛主編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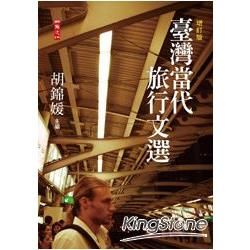 |
$ 234 ~ 288 | 臺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
作者:胡錦媛主編 出版社: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25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臺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
遠足出發—離開自己—迷路回家
旅行寫作創造了旅行的記憶、或甚旅行的意義,但旅行寫作絕不只是旅行行為的副作用產品而已。這本文選所收錄的作品自有其美學素質,十八位作家各自呈現其別緻風貌……讀者閱讀的美感經驗將使這些旅行寫作成為永久的珍藏。
「旅行文學」的定義是什麼?我們是否已經建構對「旅行文學」的認知?「旅行文學」是否可以無限上綱,涵蓋各種書寫?──觀光、出走、考古、田野調查、自傳、回憶錄、返鄉、流放、流浪、流離與移居遷徙、親身的實証經驗與憑空的想像遨遊?對於定義、認知、結構、主題與文類等種種問題,我們則談得太少又太淺。旅行寫作創造了旅行的記憶、或甚旅行的意義,但旅行寫作絕不只是旅行行為所成就的一項副作用產品而已。
關於旅行與旅行文學,我們似乎談得太多又太少。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胡錦媛,美國密西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任教於政治大學英文系。研究旅行文學與書信文學。
作者序
序論
關於旅行與旅行文學,我們似乎談得太多又太少。
近十多年來,經濟力的提昇、全球化的願景、對異國的想像與緊張沉重的生活壓力,使旅行爆炸性地成為臺灣全民生活的「必要」,一種持續進行的集體儀式。而旅行所激發出來的全民書寫能量與敘述欲望在旅行寫作中找到了最鍾情的消耗空間,進而轉換為書店中琳瑯滿目的旅遊書籍、報章雜誌上目不暇給的旅遊資訊,形成巨大超強的旅行體系符號。
但是,「旅行文學」的定義是什麼?我們是否已經建構對「旅行文學」的認知?「旅行文學」是否可以無限上綱,涵蓋各種書寫?──觀光、出走、考古、...
關於旅行與旅行文學,我們似乎談得太多又太少。
近十多年來,經濟力的提昇、全球化的願景、對異國的想像與緊張沉重的生活壓力,使旅行爆炸性地成為臺灣全民生活的「必要」,一種持續進行的集體儀式。而旅行所激發出來的全民書寫能量與敘述欲望在旅行寫作中找到了最鍾情的消耗空間,進而轉換為書店中琳瑯滿目的旅遊書籍、報章雜誌上目不暇給的旅遊資訊,形成巨大超強的旅行體系符號。
但是,「旅行文學」的定義是什麼?我們是否已經建構對「旅行文學」的認知?「旅行文學」是否可以無限上綱,涵蓋各種書寫?──觀光、出走、考古、...
»看全部
目錄
序論 遠足離家—迷路回家 胡錦媛
遠足出發
焦 桐 遠足
劉克襄 支線火車的邂逅
離開自己
楊 照 跨越邊界
張曉風 戈壁行腳
張 復 在西安
孫瑋芒 西湖‧長城
蔣 勳 柯比意與貓
閻鴻亞 春天是一個女生在夜晚的街角
許正平 The Big Blue──在聖托里尼
陳宛茜 雙城記
舒國治 香港獨遊
迷路回家
席慕蓉 篝火
泰姬瑪哈
愛 亞 夢歸家
廢樓之窺
師瓊瑜 回家
郭力昕 東非‧帝國主義‧觀光客
朱天心 銀河鐵道
王天心 倫敦‧在日落下的帝國本土
吳明益 行...
遠足出發
焦 桐 遠足
劉克襄 支線火車的邂逅
離開自己
楊 照 跨越邊界
張曉風 戈壁行腳
張 復 在西安
孫瑋芒 西湖‧長城
蔣 勳 柯比意與貓
閻鴻亞 春天是一個女生在夜晚的街角
許正平 The Big Blue──在聖托里尼
陳宛茜 雙城記
舒國治 香港獨遊
迷路回家
席慕蓉 篝火
泰姬瑪哈
愛 亞 夢歸家
廢樓之窺
師瓊瑜 回家
郭力昕 東非‧帝國主義‧觀光客
朱天心 銀河鐵道
王天心 倫敦‧在日落下的帝國本土
吳明益 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胡錦媛主編
- 出版社: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25 ISBN/ISSN:978986649095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旅遊> 主題旅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