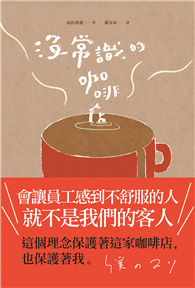導言(摘錄)
我的出發點可以視為是一個康德式的問題,即:超越(transcendence)如何可能?在此,我並不在「超越」的通常意義上使用它,例如,對正統基督教神學而言,超越是上帝不同且高於其創造物的屬性。本書的「超越」毋寧要在更為基本,也就是它的拉丁詞根「transcendere」的意義──攀越(climb over)、超越(beyond)或越過(surmount)──來理解;因此,在《牛津英語詞典》(OED),「超越」(transcend)最古老的意思便包括了超過或跨越某種物理或非物質的限制。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超越特別含有在社會、政治和知識(intellectual)領域裡的創新的意義。我們要如何超越現有的慣例、信念所設定的限制而創新呢?
藉由提升創新的地位,忽視上述問題重要性的主流文化中,找到答案並不困難。於是,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想就斷言:自由資本主義是唯一適合釋放人類的特殊能力──尤其是創造能力──的制度。因此,一旦正確的制度和政策—這些制度和政策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看重的結構調整計畫,以及由這些機構和其他與之同性質的國際機構所草擬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法典來詳細規定──被確立起來,那麼人們就可以預見,反映人類創造力解放的大量創新(和生產力與產出增長率的提高)會接踵而至。然而,事實上,二十多年來,儘管將這些措施運用在開發中國家(global South),它所帶來的卻是經濟的不景氣;與此同時,顯著的例外則是在中國大陸施行著名的資本主義的非自由主義變體卻得到了發展。這個事實被前述思想的宣導者視為異於常理,因此通常忽略不計,因為這些人關心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占優勢的控制關係。
與新自由主義類似,當代知識圖景中那種粗俗的後現代主義,即新自由主義的晚輩,也貶低超越,在20世紀最後二十年,後現代主義已經制度性地深植於英語國家與地區的學術界。例如,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後現代主義的奠基著作中聲稱:現代性作為社會關係「『原子化』的一個結果已經被超過了,這種關係進入語言遊戲的彈性網路」,對語言遊戲網路的理解需要一種「作為奠基原則的競技遊戲」,因為「在遊戲的意義上,言說即是戰鬥」。這樣,語言遊戲之間的關係就是衝突性的;於是利奧塔拒斥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依照哈伯瑪斯的理論,理解預設了一種達成一致的隱含趨向。利奧塔說:「這樣的共識與語言遊戲的多樣性有衝突。發明通常產生自異議。」利奧塔對後現代性的著名界定如下:它是啟蒙主義、黑格爾(G. W. F. Hegel)和馬克思(Karl Marx)的宏大敘事的崩潰:這種宏大敘事對於整個人類歷史過程進行了總體化解釋。代替這種宏大敘事的是「微小敘事」(petits récits)、碎片話語。這種敘事與話語顯示了語言遊戲的內在多相性和衝突性。在這裡,超越是語言本身天生的潛能,一種由後現代性的碎片化、流動的社會結構所解放出來的潛能。
當然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有重要的差別。其中最明顯的是,前者把主體視為一種能動的統一體:資本主義所解放的正是內在於人類個體身上的創造力。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後現代主義者傾向於批判這種自主的、連貫的主體。這種批判是在法國「1968年思想」中發展出來的,其中著名的人物有路易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但是在這兩種思想模式之間有許多有意思的相似之處。首先,創新(利奧塔傾向於使用「發明」一詞)取決於個體之間的衝突,不論這種衝突是,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所做的那樣,概括在市場競爭這個概念中,還是像利奧塔所辯稱的,被概括在更加抽象的「競技」遊戲中,這種競技遊戲內在於語言遊戲中和存在於語言遊戲之間。其次,當代社會結構被系統性地視為一種進步的創新,不是由於這種社會結構被當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性,就是因為人們聲稱人類社會已進入後現代的不確定性和碎片化的狀態之中。
在我看來,這兩種方法都是讓超越常態化從而貶低超越。它們把創新視為占優勢的社會關係的常規結果。這產生了如下後果,即超越只是等同於我們社會所存在的一種慢性病徵的某種變化,等同於技術的改進或(更少見的)發明、生活風格上的變化,這些技術改進與生活風格的變化反過來得到由市場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範圍變化所帶來的物質上的支援。毋庸置疑,我們的生活經驗被這些變化所改變,但是這些變化不僅沒有觸動社會與經濟權力的分配,而且也沒有觸動我們這個社會廣泛流行的思想風格、感受形式。於是,在廣泛流行的而又常常表面的變化(variations)與隱藏著的穩定性之間有一種顯著的對比,前者是無邊無際而又過眼雲煙似的媒體炒作的主題(subject),而後者則是穩如泰山的──如果不是靜止的話。
無論對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對後現代主義者來說,這種對比都不是問題。對新自由主義者而言,技術的改進和生活風格的變化就是社會的創新之所在,這種社會的制度框架廣泛地與人性的要求相符,這個社會已經達到歷史的終結,亦即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將會帶來歷史終結的結果。同樣地,對後現代主義者而言,微觀的變化恰恰就是我們所應期待的東西,只要利奧塔所謂的「語言遊戲的多樣性」得到了恰當的承認和特定的社會表達。它們標誌著我們從宏大敘事的恐怖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後果中逃離出來,而這種宏大敘事在追求總體的改變時,也努力把生存的多樣性關進強制一律的牢籠之中。雖然這兩種立場似乎都是首尾一貫的,但是它們不可能滿足那些敏感於占優勢的社會經濟結構──這是(占主導地位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即一種為利奧塔忽視的、但呈現為他為之歡呼的多樣性與發明的理論視域(horizon)的總體性──所設定的那些界限,並渴望超越之的人。
如上所述,超越既是政治問題也是哲學問題。後現代主義的一個次要主題是社會批判──這樣的批判取決於超越的可能性,由於它以現存社會關係的界限為主題,因此只是含蓄地談到超越這些關係的必然性──不再可能。於是,讓.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認為:在一個由模擬(simulation)構成的社會裡,異化概念不再有任何針對性,因為在這個社會中,主流的意象標誌著再現(representations)和真實(the real)之間的差別的消除。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傳統中,當一個主體失去其部分或全部本質力量時,就是異化的。診斷異化就是要在現狀和反事實的本真狀況之間做一對比:在現狀中,主體為現象所誤導以至於認識不到其本質力量的丟失;而在後一種狀況中,其擁有屬於自己的全部力量。然而,一旦再現和真實、現象和本質之間的差別消除了,這樣的對比便失去了意義。於是,布希亞辯稱:「作為文明的存有物,今天我們的一切問題不是⋯⋯發源於過度的異化,而是異化的消失而引發的主體間最大程度的透明性。」而對異化所引起的批判和反叛,我們普遍地毫無興趣:「這不再是一個相信或不相信從我們眼前通過的意象的問題。我們曲折地反映這些實在和符號,但不相信它們。」這種漠視形而上學的做法映襯著「一個更一般的問題:制度或政治性的東西等對它們本身的漠視。」
與布希亞不同,千禧年的轉變並不表現為進一步陷入這種漠視的黑洞之中,而表現為大眾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九一一之後)對抗帝國戰爭的新國際性運動。此外,社會批判經歷著一場令人矚目的復興,因為有大規模的讀者群體閱讀瓦爾登.貝羅(Walden Bello)、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蘇珊.喬治(Susan George)、麥可.哈德(Michael Hardt)、娜歐蜜.克萊茵(Naomi Klein)、喬治.蒙比爾特(George Monbiot)、內格里、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這樣的人物的作品,即他們對有關布迪厄所說的不幸世界(la misère du monde)──新自由主義和英美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所譴責的那些現存悲劇──的診斷的作品。這些運動不是簡單重複過去的基進運動。一方面,自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古典左派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大概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微弱。另一方面,由於西雅圖(1999年)和熱那亞(2001年)等地的抗議,世界社會論壇及其分支如歐洲社會論壇所進行的辯論和相互感染等非常事件,新的史無前例的國際動員和合作形式得到極大發展。
就法國來說,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娃.夏佩羅(Eve Chiapello)所謂的「社會批判的復興」是對新自由主義攻擊的回應,而這種社會批判的復興構成了我希望在其中處理超越問題的脈絡。本書不是一篇研究創新──即一項大規模的、也許不可能的、甚至有些瘋狂的事業──條件的一般性論文。我所特別關切的是:我尋求處理今天的社會批判在其中得以可能的條件,在此,社會批判被理解為一種理論類型(a theoretical genre),它既以占優勢的社會關係所設定的界限為主題,又尋求超越這些界限。「今天」是指一種特定的歷史形勢,即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在這種形勢下,自由資本主義在全球取得了統治地位,美國建立了不受挑戰的霸權,這又引發了新的危機和新的論爭形式。「今天」也意指一種特定的知識群體,在其中,出現了新的社會批判樣式(styles),它不僅要揭示特定制度或政策,而且要為他們自己的實存提供哲學論證等等。
於是,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要努力批判性地評估這些在我看來最重要的理論樣式。在第一章,我討論了形式主義的現代性理論,其最具影響的當代版本是由哈伯瑪斯發展出來的,同時我也考察了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所發展的有趣變體。第二章則致力於法國批判社會學──不僅包括布迪厄的作品,還包括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所發展的更具相對主義色彩的版本。在第三章,我討論了與此有關的兩位當代哲學家: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和斯拉維.紀傑克(Slavoj Žižek)。最後在第四章,我轉而處理他們的對立面,即內格里的生機論(the vitalism)。
正如此處概要明確指出,第一部分聚焦於討論當代法國思想。這裡所評論的思想家並非都是法國人:哈伯瑪斯是德國人,內格里是義大利人,紀傑克是斯洛文尼亞人。不過,後兩位是法國哲學文化的積極參與者,而儘管人們會毫不猶豫地認同哈伯瑪斯是德國人,但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現代性的哲學論述》(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卻是一部關於法國後結構主義的批判性系譜學的論著。我關注於一系列以巴黎為核心的理論介入,其理由不是法國人在某種意義上獨占了當代批判思想的鰲頭。恰恰相反,在政治經濟學的關鍵領域,英語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做出更重要的貢獻。但是在我看來,當代超越問題卻必須由20世紀法國思想定義的術語來加以界定。當然,我不是要對社會批判理論的當代樣式進行一般性審視,我選擇了一組可視為相互對話的思想家,他們正試圖回應超越問題。
思考這一問題可以按照如下方式來進行。我前面對新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指責是,這兩者都沒有考慮到社會經濟結構對創新所設定的界限。更廣泛地講,人們可以把這種限制視為物質性負擔:支撐想像和行動的物質結構(自然的以及社會的結構,對我來說,尤其是社會的結構)也給這種想像和行動劃定了範圍。假若如此,那麼這種負擔如何與超越的可能性一致起來呢?當代法國思想界主流的答案是:透過對存有(Being)的否定達到超越。巴迪烏在他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s)觀中最系統地陳述了這個答案:在其中,他把真理—事件看做是對存有做減法,從虛空中凸顯,從虛無擺脫。但是有證據表明,各色思想家曾經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此一思想的最強有力、最優雅的版本。例如,在《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第一卷中,沙特(Jean-Paul Sartre)構想了融合集體(a group-in-fusion)的形成,這是一種突然發生的、簡直就是天啟的事件,它結束了「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即社會經濟結構的堅固性,其本身就是實踐的一種沉澱;只有實踐本身才最終屈服於制度化過程,並回過頭又沉浸在實踐惰性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類似的還有,科內利烏斯.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在《社會的想像性建制》(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中設定了一種迴圈的過程,在其中,創造性從想像那裡翻湧而起,並最終引發一套新的、限制進一步革新的制度。
甚至德希達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也帶有同樣的意思。不像粗俗的後現代主義者,德希達不是簡單地歡呼差異。差異包含著缺席和在場的遊戲:換言之,內在於指稱中的分化過程設定了在場這個環節,即設定了直接進入真實的環節,然而這個環節卻從來沒有完成,相反地,這個環節只是作為先驗所指而被持續地延遲了。「延異」這個新構成的詞彙就是要涵蓋缺席和在場必然同時存在這一特性:在場是必然要被設定的東西,但是它卻總是被延遲。在此意義上,利奧塔所歡呼的差異性、多元性和異質性無法卸下德希達所謂的「在場形而上學」的負擔,換言之,在場形而上學的理念是西方哲學傳統的基本構成,它認為思想能夠直接地、未經中介地進入真實。最後,傅柯在其「中期」(《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和《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所遭遇的著名的難題是,(根據傅柯)如果權力關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實際上,比如透過規訓的機制,這些關係建構的恰恰是這樣一些個人──這些人是潛在的反抗主體,那麼我們該如何說明反抗能夠內在於這些權力關係呢。這個問題也同樣蘊含著一種作為限制的存有(Being as confinement)的觀念。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舒年春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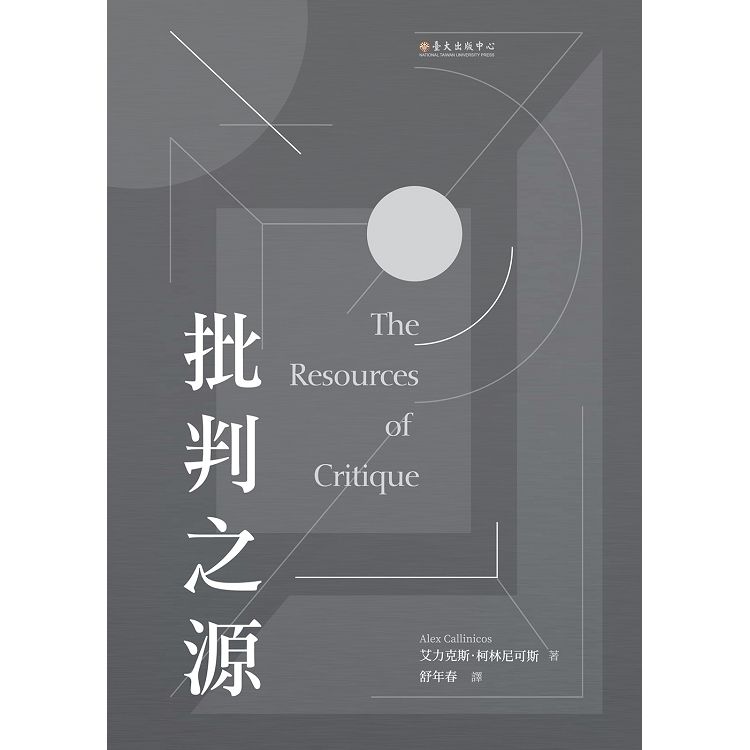 |
$ 245 ~ 468 | 批判之源
作者: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 / 譯者:舒年春 出版社:國立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10-04 語言:繁體/中文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批判之源
我的出發點可以視為是一個康德式的問題,即:「超越」如何可能?
社會批判在最近幾年已然如火如荼。西雅圖和熱那亞的反全球化抗議以及伊拉克的偉大反戰征程,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相關爭論,放回到政治與智識議程之中。但是在一個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深受後現代思潮影響的時代,社會批判如何在哲學上定位自己呢?在《批判之源》中,作者尋求系統性地處理這個問題。在第一部分,他考察了當代幾位極具影響力的批判理論家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如巴迪烏、比岱、博爾坦斯基、布迪厄、夏佩羅、哈伯瑪斯、內格里和紀傑克等人。
這些理論家視角中的局限,促使作者在本書第二部分勾勒出一個替代進路,批判實在論的本體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矛盾理論和平等主義的正義觀,是這個替代進路的主要元素。作者論證的主要推動力是要展示:對於任何試圖挑戰現存世界秩序的人而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仍然是無法忽視的。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只有在跟其他批判視角保持一種開放而有力度的對話時,才能具有當代價值。《批判之源》就是致力於這種對話的一次努力。
作者簡介: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牛津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歐洲研究系。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種族和種族主義等。主要著作有Althusser's Marxism、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Karl Marx、Making History、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The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Deciphering Capital: Marx's Capital and Its Destiny等。
譯者簡介:
舒年春
湖北武穴人,哲學博士,先後在華中師範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哲學,現任教於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研究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價值哲學、政治哲學。出版專著《正義的主體性建構——羅爾斯正義理論解讀》等。
章節試閱
導言(摘錄)
我的出發點可以視為是一個康德式的問題,即:超越(transcendence)如何可能?在此,我並不在「超越」的通常意義上使用它,例如,對正統基督教神學而言,超越是上帝不同且高於其創造物的屬性。本書的「超越」毋寧要在更為基本,也就是它的拉丁詞根「transcendere」的意義──攀越(climb over)、超越(beyond)或越過(surmount)──來理解;因此,在《牛津英語詞典》(OED),「超越」(transcend)最古老的意思便包括了超過或跨越某種物理或非物質的限制。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超越特別含有在社會、政治和知識(intel...
我的出發點可以視為是一個康德式的問題,即:超越(transcendence)如何可能?在此,我並不在「超越」的通常意義上使用它,例如,對正統基督教神學而言,超越是上帝不同且高於其創造物的屬性。本書的「超越」毋寧要在更為基本,也就是它的拉丁詞根「transcendere」的意義──攀越(climb over)、超越(beyond)或越過(surmount)──來理解;因此,在《牛津英語詞典》(OED),「超越」(transcend)最古老的意思便包括了超過或跨越某種物理或非物質的限制。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超越特別含有在社會、政治和知識(intel...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與致謝
導言
第一部分 四條死路
第一章 現代性及其承諾:哈伯瑪斯和比岱
第一節 在社會學式的懷疑與法治之間:哈伯瑪斯
第二節 對馬克思和羅爾斯的支持與反對:比岱
第二章 在相對主義與普遍主義之間:法國批判社會學
第一節 資本主義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
第二節 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布迪厄
第三章 觸摸虛空:巴迪烏和紀傑克
第一節 例外即規範
第二節 奇蹟確在發生:巴迪烏的本體論
第三節 非真實:紀傑克與無產階級
第四章 存有的慷慨:內格里
第一節 一切都是神恩
第二節 內...
導言
第一部分 四條死路
第一章 現代性及其承諾:哈伯瑪斯和比岱
第一節 在社會學式的懷疑與法治之間:哈伯瑪斯
第二節 對馬克思和羅爾斯的支持與反對:比岱
第二章 在相對主義與普遍主義之間:法國批判社會學
第一節 資本主義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
第二節 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布迪厄
第三章 觸摸虛空:巴迪烏和紀傑克
第一節 例外即規範
第二節 奇蹟確在發生:巴迪烏的本體論
第三節 非真實:紀傑克與無產階級
第四章 存有的慷慨:內格里
第一節 一切都是神恩
第二節 內...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