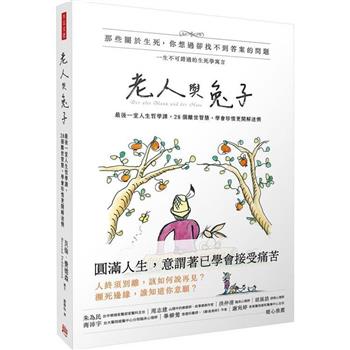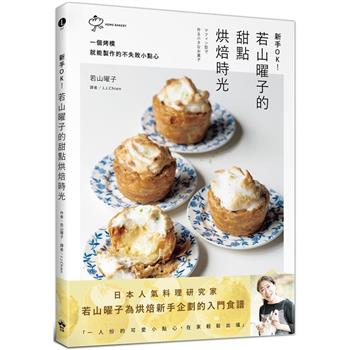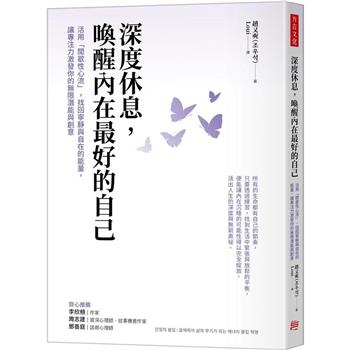第一部 在蛇的懷抱裡
第一章 失聲的森林
當檀香山機場的接駁車司機聽見我的目的地,他禁不住笑了:「小心蛇噢!」
九英里寬、三十英里長的關島,自夏威夷跨越國際換日線約需七個鐘頭的飛行時間。關島目前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化熔爐之一。它是馬里亞納群島最南方的島嶼。馬里亞納群島是四百萬年前因海床噴發所形成的一串島鏈,連綿五百英里長;若非此處海水深達七英里,它將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脈峰鏈。最早居住於關島的人種為南亞譜系的查莫洛人(Chamorro),自三千五百年前起便極其繁盛,直至十六世紀初期,西班牙人、天主教徒、感冒病毒與天花等,不約而同地來到這裡。
現在,他們的後裔集中於關島南邊的三分之一土地,說著西班牙語和古查莫洛語混合的語言,駛著小貨車徘徊於靜謐、列綴著美麗棕櫚樹的村落與村落間,舉辦歡騰熱鬧的週日嘉年華,榮耀他們的守護神,一切宛若東洛杉磯延長的熱帶假期。一八九八年,西班牙依巴黎條約將關島、波多黎各與菲律賓割讓給美國。其間,美國曾一度喪失對關島的主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國際換日線的另一頭爆發珍珠港事件,日本以鄰近的塞班島為跳板,入侵關島。
三十一個月之後,在歷經太平洋戰役中最為腥風血雨的一場苦戰後,關島又重回美國懷抱。自一九四四年起,美國軍方獨占關島北邊三分之一、宛若叢林的石灰岩高原,作為空軍基地要塞;直至十數年前,甚至設置有數百顆的核子彈頭。儘管如此,卻未曾聽聞任何怨言。想是對關島總共十五萬的人口而言,軍方與關島政府提供了半數以上居民的就業機會。關島是美國的領土,是一塊當地國會議員非經票選、打著「通往密克羅尼西亞的大門」和「美國一天開始的地方」旅遊旗幟的特區。
那是個多麼特殊的島嶼呀!將關島三等分,串連北部與南部的中段略作狹長,充斥著購物商場、速食連鎖店、高聳的休閒度假旅館、一座國際機場,以及熙來攘往、日夜不曾稍作停歇的車流。究竟哪一個紅綠燈交叉口是杜夢(Tumon)與塔慕寧(Tamuning)的模糊交界?哪裡是塔慕寧的盡頭,哪裡又是亞加納(Agana)的起點?對於大多數美國本土的旅人來說,關島不過是他們前往帛琉、波納佩(Pohnpei)等更靜謐、宛若天堂的島嶼時,短暫停留的中繼點。但對於世界各地的旅人,尤其是人數急遽增長的日本新婚夫妻、商人、度假者和血拼購物者而言,關島是他們旅程的終點。在這裡,你能以便宜的價格在射擊場裡選擇喜愛的槍枝盡情射擊(於日本非法);或是打扮得像牛仔,騎著馬在場子裡繞圈兒。
只要找得到停車位,你可以在世界上最大的 KMart(美國連鎖大型賣場)以免稅的價格恣意血拼;在晚上九點營業時間結束前,這裡的停車位可是無時無刻停得滿滿的呢。你也可以挑選專為日本人所設計與服務的旅館休憩。一九七二年,當日本軍官橫井庄一終於離開了躲藏二十八年的隱密洞穴,完全不知戰爭早已結束的他看著滿街的日文廣告招牌,不由得要困惑:究竟戰爭是誰勝誰敗呢?
有蛇!
在這樣非比尋常的奇特世界,棕樹蛇依然找得到屬於牠的位置。關島流傳著這樣的理論:美國大兵為了消滅大鼠,放出棕樹蛇。「不,」另一個居民這麼反駁著,「那蛇,是由一千五百英里外的菲律賓游過來的。」而大多數生物學家則擁護與貨物進出有關的論點:棕樹蛇於一九四九年前後,來自新幾內亞附近、阿德默勒爾蒂群島(Admiralty Islands)上的軍事基地,牠蜷曲在吉普車的擋泥板或是其他戰時留下的廢棄物品裡頭。那時的關島還沒有蛇。 蛇,是個多麼新鮮的玩意兒。一則頭條新聞的標題這麼寫道:「七英尺長的蛇於此被殺。」另一則是,「空軍雜誌記者尋得至今最長的蛇,八•五英尺長」;或,簡潔的,「活生生的蛇!」。《關島日報》(Guam Daily News)於一九六五年十月曾報導道:「因為牠們吃掉惹人厭的小動物,對人類又不具危險性,」旁邊附圖為一條七英尺長的蛇於航海員協會(United Seamen’s Service Center)被殺死的照片,「牠們被認為對關島或許是有益而無害。」接下來的幾年間,數條體型相當的蛇成為當地的新聞話題;包括一九九六年六月清晨四點鐘,滑過艾蒂絲•史密斯太太頸邊的那條蛇。
最初,棕樹蛇的活動範圍只局限在亞加納南方數英里外的軍事海港阿普拉港(Apra Harbor)周遭,到了一九七○年,棕樹蛇的蹤跡已遍布整座島嶼。而且,不只是「小型的有害動物」,其他動物也逐漸消失無蹤。在一九八九年某份民調裡,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示大鼠的數量無疑是減少了,可是雞與雞蛋、鴿子、雉、鴨、鵪鶉、鵝、鸚鵡、雀鳥、小豬、貓,也跟著減少了。今天,籠子裡頭是一隻雞;明天,則是一隻吃得飽飽肥肥、逃不出籠子的蛇。蛇逐漸將目標鎖定在體型更大的獵物。在一九八九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九月間,關島紀念醫院(Guam Memorial Hospital)有七十九件為棕樹蛇所咬傷的病例;其中有六十三件(八○%)的受害者是在家中睡覺時被咬,而且裡頭有一半的受害者是五歲以下的孩子,包括兩名睡在父母之間的嬰兒!伊凡•梅森(Yvonne Matson)的經歷最可顯露所有母親的恐懼:某個清晨,尚是嬰孩的兒子的尖叫聲喚醒了她。她衝進房門,只見五英尺長的棕樹蛇將寶寶由腳至脖子團團纏繞著,獠牙正咬住寶寶的左手臂。數個月後,梅森的媽媽也慘遭蛇吻,於是,她請來了一名驅邪的法師。
棕樹蛇擴展的速度很快,但關於牠的耳語散播得更是迅速,到夏威夷、到加州,甚至遠到紐約。《華爾街日報》某篇文章描述,那蛇「彷彿一條條煮熟的棕色義大利麵條,自樹梢垂掛而下。」但我卻未曾看見過半條蛇。沒有蛇從我旅館房間的水槽鑽出來,也沒有蛇藏匿在塔可鐘(Taco Bell)墨西哥餅速食店停車場的茵綠草坪裡。抵達關島的頭兩天,我開著車四下詢問關於蛇的行蹤。
「我記得數年前似乎曾經在馬路上看見過一條,當時我正在開車,但那時是晚間。」
「我的朋友曾於數年前看見過一條,當時他正在開車。」
「我在德州看過更多蛇!」
一個農夫更繪聲繪影地形容著某條蛇怎麼鑽入他心愛寵物山羊的鼻孔裡,隔天,他的山羊便死了。他說:「你知道嗎?那顏色不是棕的,而是藍的!」
簡而言之,在關島,關於蛇的傳說是眾口紛紜,且耳聞和眼見之間存有相當的落差,足夠讓人懷疑事情的真相究竟為何。某個午後,我出席關島的希爾頓飯店為顧客舉辦的雞尾酒會。自德國移居此地的總經理態度溫和地擔保道,在該旅館任職六年以來,他只遇見過一條蛇,「願牠得到安息,」他說道。他的態度是那麼誠懇,以至於數週後當我閱讀一篇來自《洛杉磯時報》的文章時,內心驚訝萬分。它寫道,某匿名的希爾頓飯店場地管理員坦承,在短短一個月內,他以彎刀砍掉二十條棕樹蛇的頭。我立即撥電話過去確認真假。「我沒有公開討論這件事的權限,」一陣轉接過後,旅館的某職員對我如此說道,隨即掛了電話。我不死心地再打了一遍。這次轉接到管理階層,他對著話筒吼道:「你們是不是打算讓旅遊業統統完蛋?盡是些危言聳聽,亂捏造棕樹蛇怎麼吞噬掉關島的人!我在這裡住了三年半,只看見過兩條蛇:一條在瓶子裡,被人給捉起來的;另一條是在路上,被壓扁了的。我告訴你,我住在偏僻的郊區,要是我真認為棕樹蛇會像義大利麵條一樣從樹上垂下來,我怎麼可能還讓我的孩子在外頭玩耍!你們這些傢伙,擺明是唯恐天下不亂,小題大作!」
棕樹蛇的新天堂樂園
因此,今天我來到這裡是為了尋找一條蛇。一條顯然不急著、也不打算現身的蛇。也確實,那麼多個世紀以來,棕樹蛇之所以能夠在演化的巨浪裡尋得生機,仰賴的正是牠善於隱匿的本事。
「蛇極度畏光,」一個午後,厄爾•坎貝爾(Earl Campbell)對我解釋道,「白天,牠們藏匿於不易為人所覺察的暗處,所以儘管我的許多朋友在關島住了這麼多年,卻一條蛇也不曾見過。」
坎貝爾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年輕爬蟲學家。他提議,或許在他的陪伴與嚮導之下,我有見到蛇的好運氣。坎貝爾是棕樹蛇研究計畫的其中一員。美國聯邦政府於一九八八年啟動、資援一系列的研究計畫,目的在削減棕樹蛇的數量,或者更切合實際地說,是預防棕樹蛇繼續擴散至夏威夷,或是關島以外的任何其他地域。坎貝爾對於設置防蛇屏障有著濃厚的興趣:那包括真實的屏障,意即具形體的物理藩籬,可將蛇局限於某塊特定區域,或阻絕牠遊走至其他領域;以及不具形體的屏障,意即由人類智慧所設計的象徵性藩籬或普遍策略,以局限其活動範圍、削減其數量、緩和其擴張速度,讓棕樹蛇無所遁形。要殲滅敵人,首先得熟悉牠的生存模式。然而在棕樹蛇大舉入侵關島以前,我們卻對牠的基本生活樣態一無所知。因此,為了解牠,科學家首先得找到一條棕樹蛇。
體格強壯、卻頂著早白灰髮的坎貝爾,有張屬於研究生慣有的滄桑面容。他從事研究的地點位於關島極北端的西北軍事基地(Northwest Field)內,突出海面上的石灰岩高原灌木叢生。二次大戰期間,那裡有許多軍方的兵營、籃球場、跑道與彈藥庫;而後,它轉變為一座荒蕪雜亂的叢林,迅速長滿天剛天剛樹(tangantangan tree),這種原產於中美洲、生長快速的多節瘤樹木,為避免土地侵蝕而在戰後廣為種植,如今則成為棕樹蛇豐饒的棲地。蛇是夜行性動物,坎貝爾也因而改變他的作息。一個傍晚,天色轉暗,坎貝爾一身T恤、短褲、涼鞋,來到他即將待上數小時的研究地點。一彎新月低懸樹梢,熱帶區域特有的潮濕悶熱使蝗蟲的唧唧聲產生共鳴。坎貝爾戴上一頂有頭燈的頭盔。點亮頭燈後,我們朝著一條腳底鋪滿厚實落葉、頭頂盡是藤蔓垂懸,狹窄且窘迫的林間小徑走去。
「在一座森林裡找尋一條蛇,彷彿在《瓦多在哪裡?》【譯注1】一書的圖片裡尋找瓦多那般不易,」坎貝爾說,一邊繼續躡手躡腳地前進,不時左右轉動著頭,讓頭盔上的燈光照射在前方與四周盤根錯節的粗壯樹枝上。「我在這裡平均一個小時可以找到一條蛇。」他坦承,這數目聽起來似乎不怎麼讓人印象深刻。不過,他說,森林裡的這塊土地可是世界上棕樹蛇密度最高的地點呢。幾個月以前,坎貝爾與兩名同事一道前往澳洲,研究生活於原棲地的棕樹蛇。
他們總共花了十八個晚上的時間,才找到三條蛇,其中只有一條是棕樹蛇,另外兩條則是別種的蛇。「棕樹蛇在關島生存的情形,真是好得不可思議,」坎貝爾不覺帶著一絲讚賞的語氣說道。棕樹蛇有多適應關島,以及為什麼牠們在此能如魚得水,都是坎貝爾與同事們想要解開的疑惑。那晚的「做記號與再捕捉」任務是坎貝爾所負責的工作之一,被他捉住的蛇得先稱重、測量體長、標記供日後辨識,最後放走,期望在數日、數周,或數月後,能夠再次捕捉到牠。累積的數據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段時間以來,棕樹蛇的成長及其移動的習性。「我們發現這些蛇遷移的頻率非常高,」他說,「唯有架起屏障,才能阻止牠們到處遷移。」
歷經數年,外來種在地球上的膨脹速度,已讓牠們在科學界自成一門學問,稱作「入侵生物學」(invasion biology)。它的起源可回溯至一九五八年,由英國生態學家查理斯•艾爾頓(Charles Elton)所發表的《動植物之入侵生態學》(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 and Plants)一書。
儘管在那以前也有關於引入或入侵物種的個案散見於各科學期刊,但艾爾頓是第一個主張這些個案並非獨立事件,而是一個影響深遠且不斷進展的現象之片段:「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別犯下任何的錯誤:我們正在目睹一樁對於世界動植物史有著重大衝擊的事件。」艾爾頓於書中涵蓋了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歷史與地域——序論自一八九○年引入美國的椋鳥談起(這筆帳得算在布魯克林的尤金•施弗林〔Eugene Schieffelin〕頭上。異想天開的他,想將莎士比亞劇作中提及的鳥類,悉數放養到中央公園裡),也論及板栗疫病菌,一種導致近七十五%的美國栗樹枯萎死亡的亞洲真菌。此書出版當時,即便是生態學本身,都還算是個新穎的觀念,冀望能擺脫以捕捉與採集為主、充滿紳士色彩的博物學,從而成為一門獨立的現代科學。
因此,艾爾頓致力於分辨侵入物種的模式與類型,潛心於生態系潛藏的架構,以及如何解讀的方法論。他的另一部著作《入侵生態學》(The Ecology of Invasions)帶給他科學家同僚的衝擊與震撼,並不亞於一般大眾。艾爾頓寫道,「我們可以仿傚柯南•道爾(Conan Doyle)筆下的主人翁查林傑教授(Professor Challenger),站在「失落的世界」揚聲說道:『我們何其幸運,可以身處於歷史上關鍵性的戰役之中,這可是一場足以改變全世界命運的重要戰役呀。』但,最後結局會是如何?地球會成為失落的世界嗎?生態學家應該嘗試追尋這些疑惑的答案。」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艾倫.柏狄克的圖書 |
 |
$ 160 ~ 400 | 回不去的伊甸園--直擊生物多樣性的危機
作者:艾倫.柏狄克 / 譯者:林伶俐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8-04-14 語言:繁體/中文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回不去的伊甸園--直擊生物多樣性的危機
作者從關島的棕樹蛇傳說起始,實地走訪關島,希望能夠找到棕樹蛇對於本地生態的影響。全書涵蓋各個區域的生態景象,著眼於人類遷入此地之後造成的生態影響。
人類的生活需求,不論是畜牧、放養、打獵,都和自然的資產息息相關。除了吃食,人類還有著和大自然全然不同的生活型態,我們飼養寵物,我們基於各種需求讓外來種侵入原本的生態。更甚者,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發達,將各個地區間的藩籬消弭;人類的便利,使物種的遷徙速度也爆炸似的快速散布。
達爾文的天擇概念對現代來說,可能必須要有另一層的省思。如果物競天擇的概念是對的,那麼是否有一些絕對強勢的物種,將會佔據世界上的各個地區?島嶼的生態單純,對於外來種的侵襲毫無招架之力,人類該如何有所作為?又當我們實行保育政策的同時,其實也正在改變週遭環境,大自然億萬年來的平衡已遭破壞,人類必須學習找到和大自然相處的平衡,不論是放任地破壞,或是一味地復育,都是值得再三省思的做法。
章節試閱
第一部 在蛇的懷抱裡第一章 失聲的森林當檀香山機場的接駁車司機聽見我的目的地,他禁不住笑了:「小心蛇噢!」九英里寬、三十英里長的關島,自夏威夷跨越國際換日線約需七個鐘頭的飛行時間。關島目前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化熔爐之一。它是馬里亞納群島最南方的島嶼。馬里亞納群島是四百萬年前因海床噴發所形成的一串島鏈,連綿五百英里長;若非此處海水深達七英里,它將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脈峰鏈。最早居住於關島的人種為南亞譜系的查莫洛人(Chamorro),自三千五百年前起便極其繁盛,直至十六世紀初期,西班牙人、天主教徒、感冒病毒與天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艾倫.柏狄克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8-04-14 ISBN/ISSN:9789866662485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424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天文/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