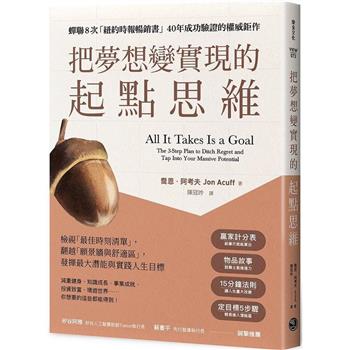推薦序
困境中的抉擇
我今年剛接到醫師公會頒給我服務四十週年紀念獎。作為婦產科醫師,尤其是我從年輕的產科接生,到中年以後專注在婦女癌症醫療,我有更近接觸生命起落的機會。
穿越他人的新生與寂滅,我也走過自己罹患重病瀕臨終點而後的重生,我更確認在獻身醫療最初的發心之處,落實醫者最初的熱情和任務,是我自己最初也是最終的渴望。二○○七年我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十字架:一位醫師談臨終、悲傷與生死〉的文章,我開始深思生命終點的嚴肅議題。次年三月,一位法國婦女施碧兒(Chantal Sebire)罹患「嗅神經母細胞瘤」受盡病痛折磨,她上書法國總統尋求安樂死不可得,最終以自殺收場。我也聽過這樣哀哀求告的聲音。我照顧了六、七年的永貞,在卵巢癌復發的疾病末期,腸子阻塞,腹脹如鼓,呼吸也因此窘迫不堪。在她除了痛苦別無指望的時候,她一再哀求我協助她「縮短死亡的過程」,然而我卻無能為力,因為於法不容!她的希望我無法完成,她的痛苦直到今天仍是我的哀傷。
我們當然應該尊重生命,這不僅是為人的基本信條,更是身為醫師的我入此白袍之門的誓言:「我將盡一切可能維護人的生命!」然而當生命已不再美好,如果一切的努力只是延續「痛苦的過程」,甚至只是延長「死亡的過程」,我們到底可以做何等選擇?
Pro-life尊重生命?還是Pro-choice尊重選擇?
多年前有一部日本深澤七郎小說改編的電影《楢山節考》,劇中窮困的鄉民垂老時,就由兒子背到深山等死,以使不足的糧食可以給家裡小孩吃。為了讓孫子多一口飯吃,劇中阿玲婆婆忍痛拿起石頭敲掉自己牙齒,讓自己更顯出衰老,好能「早日離去」。選擇死亡也可以是為了把愛留給生者。
《天堂計劃—─陪父親走向安樂死的一段路》是由今年五十九歲的法國當代著名劇作家艾曼紐.貝爾南依據親身經歷寫就,在法國引起熱烈迴響。
貝爾南的父親八十八歲,是同性戀者,曾經做過心臟血管繞道手術、脾臟切除、肺栓塞,也曾被打破頭棄置街頭,垂死又被救起。此次的故事則起源於他又罹患缺血性中風及嚴重頸內動脈瘤。就貝爾南的父親一向樂觀而自我意識強烈的個性,他顯然面對身心強烈不得安適的窘境,卻不是到達一般所謂疾病無法控制或生活痛苦不堪的境地。
書中一再顯現貝爾南的父親在他自覺生活不堪、沒有尊嚴,因而追求「結束」的堅持。我們也看到我常在自己臨床服務中提醒的,那生病的當事者常常使用他「不幸者的權利」,對周圍最親近的人多方的需求。貝爾南的父親就是如此把許多困境拋給他女兒。而他的女兒也正應了生病者的家屬其實也是一起受苦的人。
我們在這本書中一再看到生病者追求終點「結束」的路上,一味忽視家人因此的困境,而貝爾南姊妹倆就在一路的心境衝突中,陪著她們並不「完美」、卻是她們所深愛著的父親,走完這條尋求「安樂」的路。
如果我們也面臨貝爾南姊妹的窘境,我們要如何抉擇?
生命如果只剩下不堪承受的痛苦,我們要如何維護我們最後的尊嚴?如果我們不要使用那已經被定型化的文字「安樂死」,而使用「善終」,或更卑微的,我們只要求「最後的尊嚴」,你會同意哪些做法?
如果可以做選擇,當你我自己面對時,你會同意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不實施心肺復甦術?或者你也同意可以撤除氧氣供應、營養供應及其他維生醫療作為?還是你也願如貝爾南的父親般擁有「結束」的選擇?這是我們在闔上這本書《天堂計劃──陪父親走向安樂死的一段路》後,仍然不能停止的困惑和思緒。
然而,「今天」仍是我們確定擁有的時光,在「結束」以前,我願再次提醒大家Carpe Diem,把握當下。
馬偕紀念醫院總院院長 楊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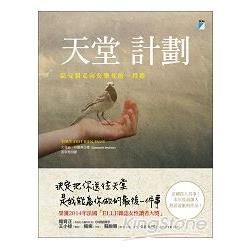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