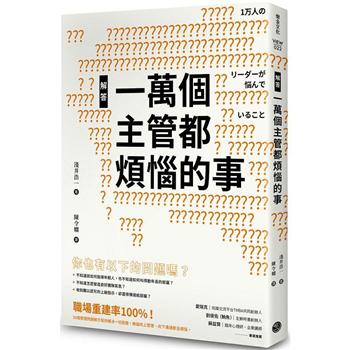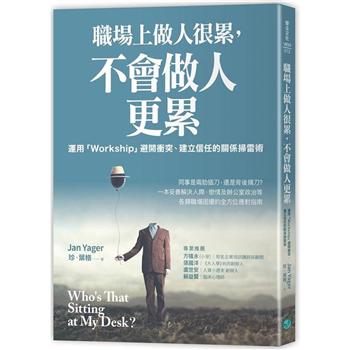當生命被淚水淹沒,放手,需要愛和對自己誠實
失去並非生命的責罰,而是重新活過的一次機會
真人實事!柯林法洛備受爭議前女友,
用自身經歷寫出唯美而心碎的現代童話故事
★文壇無法忽視的獨特新女聲,後青春期療傷的生命輓歌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作者伊莉莎白.吉兒伯特盛讚為天才作家
★改編電影拍攝中,由《哈利波特》艾瑪華森驚豔主演
★媒體譽為「鴻孕當頭(Juno)」+「女生向前走(Girl, Interrupted)
時間會治療所有的傷。
如果沒癒合,就幫傷換一個名字,然後同意讓它們留下。
艾瑪.佛瑞斯特,二十二歲,旅居曼哈頓,喜歡蛋糕和詩。身上滿是自殘的傷口。她感覺自己留在這個世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床墊上到處都是書、報紙,搖滾樂,還有藥丸。藥開始發揮作用時候她心想,死亡就像踏進一座溫暖的海洋。醒來,浪潮還在繼續衝擊著海岸。
第一次去見心理醫師的時候她邊流著血、邊掉眼淚──生命的殘破,一個接一個爛男人,一道又一道自殘的傷疤──R醫生,一個能夠了解而接納她的人,就像快滅頂時來自岸上的淡定召喚。於是她終究不至於沉沒。繼續工作、繼續生活、繼續寫作,繼續讓自己戀愛。
某天,約診時間到了,R醫生再也沒有出現。他無聲無息離開這個世界,死時僅四十三歲。再一次墜落,只剩下自己。無法克制地寫作,不知道還能撐多久。她把房子漆成紅色。就像剖開破碎的心臟一樣。心碎的人之所以如此悲慘,是因為從沒有人來拯救他們。
本書為作者個人的回憶錄,她用自己獨特的文字和R醫生道別,就像他的聲音一直在她腦海裡。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人,讓你能夠不再傷害你自己。在自我懲罰的騷亂過後,在那遙遠、並肩走過的另一世界,生命的最後一個念頭將會是愛。
作者簡介:
艾瑪.佛瑞斯特(Emma Forrest)
在英國的猶太家庭中長大,十五歲就開始寫作,著有小說《攀親帶故者》(Namedropper)、《薄臉皮》(Thin Skin)、《雪中櫻桃》(Cherries in the Snow)等,曾任非文學類選輯《損害控管》(Damage Control)一書的編輯,也曾任職Vogue、Vanity Fair、Harper’s Bazaar、Time Out、The Guardian、NME等知名雜誌。狂街傳教士(Manic Street Preacher)失蹤的團員理查‧愛德華茲(Richey Edwards)是她訪問的第一位名人,也曾訪問過饒舌歌手史奴比狗狗和布萊德‧彼特。她後來轉戰編劇工作,曾被美國Variety雜誌選為2009年十大電影編劇。2014年,她選擇重回記者崗位,開始為ELLE雜誌撰文。現居洛杉磯。
作者網站:emmaforrest.blogspot.tw
作者推特:twitter.com/GirlInterrupter
譯者簡介:
殷麗君
輔大法文系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英、法文專職譯者,譯有《味覺樂園》、《藝術創意365天》、《巴黎人的巴黎》、《超奢華愛情》、《少年邁爾斯的海》、《五歲時,我殺了自己》等書。
Email:yinli@mail2000.com.tw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艾瑪.佛瑞斯特是一位天才作家,在這本書令人難以忘懷的回憶錄當中,字裡行間都是作者巧心安排的生命之光。書寫心碎、執著,還有緩慢又棘手的療癒過程,我已經忘記我有多久沒有看過一本書這麼令我強烈震撼了。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作者伊莉莎白.吉兒伯特
作者的風格比真正的心痛還要誠實,同時也聰明太多了。寫憂鬱要寫得有說服力很困難,同時還要兼顧娛樂性和可讀性,不過作者辦到了。
—星期日泰晤士報
作者的文筆當中有一種不刻意的美感。即便她的回憶錄是一個嚴重扭曲靈魂的寫照,卻也是一本真心、真誠、關於愛的生命書寫。
—作家比莉‧李文斯頓
聰明,且非常慧黠。這本書像一次充滿抒情羽飾的獨舞,這本回憶錄坦承而直接。
—觀察家報
雖然這本書的開頭寫的是她自殺瀕死的經驗,但主要說的卻是關於生命本身。這是一本關於心理問題和心碎歷程的傑出回憶錄。
—全國郵報
相當驚人,我有股衝動想將這本回憶錄描述為一本大師鉅作,然而它又不只是這樣而已。
—艾德蒙頓紀事報
作者是一位很有自己風格,而且很能讓人共鳴的作家。無論是她在紐約那種帶有一種病態、倦怠的風格,或者是後來在洛杉磯那種性沉淪和最後煥然一新的幸福。她都寫得很酷、很聰明,也很崩壞。
—環球郵報
相當私密的寫作,作者那驚人又有趣的觀察力是她寫作中一個強而有力的部分。
—Maclean's雜誌
作者有趣又充滿智慧。我有說過她很無私嗎?跟別的回憶錄不一樣,這本書不只唱作者的獨角戲,而是在償還她對一個偉大男人的情感。這本書非常感人、有趣,也非常真實。
—《荒誕國度》作者蓋瑞.史坦恩加特(Gary Shteyngart)
名人推薦:艾瑪.佛瑞斯特是一位天才作家,在這本書令人難以忘懷的回憶錄當中,字裡行間都是作者巧心安排的生命之光。書寫心碎、執著,還有緩慢又棘手的療癒過程,我已經忘記我有多久沒有看過一本書這麼令我強烈震撼了。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作者伊莉莎白.吉兒伯特
作者的風格比真正的心痛還要誠實,同時也聰明太多了。寫憂鬱要寫得有說服力很困難,同時還要兼顧娛樂性和可讀性,不過作者辦到了。
—星期日泰晤士報
作者的文筆當中有一種不刻意的美感。即便她的回憶錄是一個嚴重扭曲靈魂的寫照,卻也是一本真心、真誠、關於愛...
章節試閱
往泰特現代美術館接近的途中,我已經知道接下來有什麼在等著我。我將看到奧菲莉亞黃褐色的頭髮,她浮在河面上的雪白身體,以及圍繞在她身邊的花。有時候,我到達那裡時,她已經死了。有時候,她還在垂死邊緣,有可能被岸邊某個我從未見過的人救起。米雷在畫草稿時曾畫上這個人,但後來就被蓋掉了,他藏在顏料底下,為了不被看見只能輕輕地呼吸。那是個男人,會任她自生自滅的一個男人,不過換作任何人,誰會不讓她淹死呢?
雖然當時我還從未有過性經驗,但有時奧菲莉亞看起來就像正在做愛的樣子,她的手臂微微探出身體上方,雙唇微啟,像被壓在隱形的愛人身體底下。很久之後—在我戀愛過之後—我才知道,她是無法捨棄他做愛後的氣味,那氣味甚至要比沿岸的花香還要來得濃烈。花兒們哀求她留在當下,但他的氣味將她鎖在過去。
在那段日子的下午時光裡,泰特現代美術館的觀賞人群混合了衣著明亮繽紛的老人、還有穿著一身黑、趕時髦的年輕人(前者總是躲雨,後者則是迫不及待想衝入雨中)。展覽廳裡總是至少有一組人正在搭訕調情。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是坐在大展覽廳正中央的皮面長椅上,正對著米雷的畫,一邊偷吃洋芋片,一邊哭。酸鹹口味是我的致命弱點。在那年還沒結束前,我因為連續吃下二十三包洋芋片,被緊急送往醫院。即便到了今天,重鹹的食物—酸鹹口味的洋芋片、啤酒酵母醬—嚐起來還是有悔恨的味道。
我知道那幅畫會讓我哭,但我還是不斷回去看。我用空心字體在筆記本上塗寫她的名字:奧菲莉亞。我想和她一直在一起,因此星期六一早醒來,就會再過去美術館,再哭上幾次。當時我總是分不清,我是為了她而哭,還是為我自己。事後想來非常清楚:我相信她的確感染了我。十三歲的我,恐怕就已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運。
***
我第一次去見R醫生是在二○○○年,一個適合扭轉生命的年份。我是在急診室待了一整晚後,直接從醫院搭六號線過去的。我對生活變得十分麻木,麻木到連性愛都沒有感覺,除非做愛時有疼痛感,我才會清楚知道躺在床上的人是自己。自殘和暴食,都還不足以達到我自我傷害的目的,因此我這個男朋友算是幫了大忙。那天晚上他做得太過火了。地鐵車廂裡小學生鬧轟轟的,但我感覺自己像是沉在一片陰鬱的海裡。等我坐到R醫生的候診室裡,隨手翻著一本過期《紐約客》雜誌的時候,仍然感覺到血還在流個不停。印染在我棉內褲上的紅色血漬,讓我聯想到某個血流不止的人垂死走在覆滿白雪的迷宮裡,那時我終於開始有了感覺。《紐約客》雜誌裡有一則不合邏輯的漫畫,讓處在那個狀態下的我突然感覺非常寂寞、失落和疏離,於是我開始哭了起來。這就是R醫生第一次見到我時我的模樣,邊流著血、邊掉眼淚,終於做了早在好幾個月前就該有的行動。
R醫生以一種像是在社交界初登場的姿態,將門打開,他是個瘦削的禿頭男人,身上的套頭毛衣紮進燈芯絨長褲裡,皮帶繫得高高的,因此當他過世時,他的妻子芭芭拉告訴我他只有五十三歲,我真的很驚訝。他的智慧和繫皮帶的風格,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很多。
我的目光在他的診間裡四處飄移。他所著作的關於濫用古柯鹼的書。三盞蒂芬妮鑲嵌玻璃檯燈。一張他兩個小兒子(安迪和山姆,我是後來才從訃聞上得知的)的裝框照片。一片庭院(除非對街小學傳來的聲音真的太吵,否則在夏天時門通常都是敞開的)。整個診間裡最棒的東西,是一件藝術品:一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木製藥櫃,裡面甚至還有砒霜。
R醫生往後穩穩靠在旋轉椅背上,像是一隻在沙發上找定位子安置好自己的貓。
「妳一直在哭。」他說。
「地鐵路程很遠。」我解釋說,想把我的眼淚歸罪在六號線上,但其實除了撲面而來的麥當勞氣味之外,這個路線的地鐵沒什麼讓我不舒服的地方。
六號線也叫做萊辛頓大道線,每天載客量高達一百三十萬人次,是曼哈頓唯一直接行駛上東城的路線,從布魯克林市中心經過下曼哈頓區,往北最終到達東哈林區的一百二十五街。這條路線始於一九○四年的十月二十七日,在我最黑暗的那段日子裡,每當我搭車去R醫生辦公室時,心裡總想:「在一個世紀後,這車還會繼續跑下去。」整條路線共有二十七站,其中只有二十三站可以使用,這讓整條路線感覺多了一些人性。當車子毫不留情地從十八街站黑暗的月台疾駛而過時,我總感覺那個站像是個遁世隱居的人,因為過於敏感而無法面對現實人生。但事實真相是,新的十節車廂對那個站的月台來說太長了。不過,當時的我在所有事情上都感覺到痛苦悲傷,而且就像品嚐上等葡萄酒一樣讓悲苦在唇齒之間流轉迴盪。
在R醫生過世後,我發現他曾經救過很多人。這種感覺很奇怪,就好像長大後發現原來其他人也都看過《麥田捕手》,不是只有你。在《紐約時報》訃聞的留言版上,大部分病患都見證說:「他救了我一命。」
他總是活潑開朗。他是個極度的樂觀主義者。不管我說任何事,他總是告訴我,事情沒有我認為的那麼糟。「是嗎,那如果我殺了一個流浪漢呢,我往他身上刺了二十二刀。」
「只刺了二十二刀嗎?那還不到二十三刀囉。」
我對他百分之百信任。我喜歡他看待我的方式。就是這麼簡單。
在外人看來,我和母親太過親密,我們有時甚至會做同樣的惡夢。對她我什麼話都能說。至於老爸,他對於太過私人的重要事情,不太聽得進去。他們一個愛我,但不聽我說話;另一個也愛我,但聽得太認真。根據R醫生的歸納總結,身為精神病醫生最重要的,就是當一個置身事外的觀察者。你可以向他傾訴所有的祕密,因為你永遠不必在晚餐桌上和他面對面。
像是從巨石底端往上攀爬,我開始每週固定向R醫生報到。然後每兩週。再來是每個月。接著是有需要才去。我用藥的劑量減半。後來我搬到了洛杉磯,我們開始利用電話進行治療。我每年會回紐約三到四次,進行面對面的諮商。
今年三月,當我確知自己即將有一趟紐約之行後,便打電話去預約。我那次到紐約的目的是要和一個男人碰面,我們才交往了短短幾個月,便已經難以想像要是兩人沒有在一起的話該怎麼辦。(他稱呼自己是我的「吉普賽老公」,因此我叫他老吉。)我準備告訴R醫生我戀愛了,而且碰上了一個好男人,善良又溫柔,他也曾經經歷過黑暗,但我們變成了彼此的光。你讓我好得足以成為另一個人的光了!
電話那頭傳來的是R醫生電話答錄機的聲音,不過是新錄的。
「由於健康因素,本診所已經關閉,請勿留言。」
R醫生過世後,我打電話給那台不受理留言的答錄機,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打,就像反覆打開又關上冰箱的門,搜尋裡面本來就沒有的食物一樣。彷彿只要我打得夠多次,他就會在那裡似的。我不停地打,直到有一天,線路被切斷了,電話無法接通,話筒裡只剩我自己的呼吸聲。
***
瘋狂就像一條逐漸接近瀑布的河流。沮喪則是一池停滯的湖水。有些已經死亡的東西在水面上載浮載沉,湖水和你的嘴唇一樣呈現藍紫色。你會完全停滯不動,因為你很害怕,不知道什麼東西正掃過你的腿(即使可能根本什麼東西都沒有,因為你已經完全失神了。)所以你會躺在床上(我躺在床的正中央,躺在深藍色的床單上。銀色的窗簾是對瘋狂的致意,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我的胸罩掛在床後方的牆上,代替我的罪惡被釘上十字架。我算過,我有三十六件胸罩。我每天、每星期、每個月躺在床上,總用手臂緊緊護在胸前,彷彿怕被人偷走似的。
在我自殺之前,還有一段前自殺期,可以稱之為開胃酒。我寄給老爸一串我在快照亭拍的頭像,裡面塞了一張紙條,寫著:「艾瑪愛爹地。」我完全不記得自己寄過這些。他的回信在我出院後才到,是他還不曉得我被送到醫院之前就寄的。他把那些照片影印下來後,把照片倒過來,在我的臉上畫了他自己—有他的鬍子和禿頭—然後在旁邊寫著:「爹地也愛艾瑪。」
***
文質彬彬的自殺念頭,幫我打開公寓樓下的大門。在溫暖的公寓中,我們拿起刀片一起割,如同在酒吧裡熱情痛飲同歡一般。乾杯,敬生命!再一回神,自殺念頭又像是一個經理人,帶領我簽閱各種重要文件,讓我拿著刀片一點點將血從皮膚上引出。「在這裡簽名。還有這裡。然後,這邊再一個。」自殺念頭是個甜言蜜語的高手。「妳好美。」它說。我臉紅了,但我相信它說的話,在它的光輝下我的不完美被淡化了。接下來自殺念頭會說:「妳的汗毛又多又漂亮,但妳才不在乎這種事。」而我會在心裡笑個不停,因為我知道自殺念頭最賣力討好的是我的虛榮心。
我躺到床上。我的大床墊上到處都是紙張,有書、報紙、一瓶水,還有藥丸。藥丸已經塞進來嘴裡,一顆不夠,還要更多一點。藥開始發揮作用。「感覺好舒服。」我心想,就像踏進溫暖的浴缸,或是當他第一次滑進妳身體的那一刻。
這時潮水開始往後退,海底布滿了好多我原先不知道的東西:生鏽的鐵罐、可樂瓶、被塑膠噎死的海鳥。感覺不再那麼舒服了。
不知從哪裡出現一個鈴聲,或許是有個小孩在敲三角鐵。我手伸向那個三角鐵,想讓它停止。是電話鈴聲。「喂。」我從海裡說。
是媽媽。「艾瑪?艾瑪?艾瑪!妳做了什麼。」
***
在上一次諮商後,R醫生和我持續往下深談。我告訴他我的初戀。對那個男人來說,我絕對不是他的初戀,事實上,根本不算他的戀人。那是從舊金山回來幾個月後發生的。他是某個搖滾樂團的人,我則是未成年的音樂線記者。他偶爾會在巡迴演出途中寄一些明信片給我,不算很經常。他還寄過一些書給我。他寄來的維多.舍其的《一個革命家的回憶錄》贈詞中有一種刻意的冷淡。
當我向他獻身之後,他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太像了,艾瑪。在同一個房間裡,我們永遠是最不互相吸引的兩個人。」這算是做愛後的某種蔑視吧。我們做愛之後,他告訴我為什麼我不漂亮,是他太特別了才會想要我。我自殘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每當我知道自己要去見他,就會習慣性自殘,這樣我就不能脫衣服。這樣我才不會愛上他。不過,當然啦,我已經愛上他了。」
R醫生的表情非常,非常悲傷。「那樣做有用嗎?」
「沒用。我很想要他,無論如何我還是會跟他回家的。而且他沒看到我的割痕。他從來沒注意過。就算他注意到了,也沒說什麼。反正他只是幹我。」我開始哭了起來,很訝異這個消失了十年的男人,竟然對我還有這麼大的影響。我不喜歡在R醫生面前說「幹」這個字。我很討厭這樣。我覺得自己好像玷污了這個房間。
但說實在的,我玷污了什麼呢?在我之前或之後的病人發生過什麼故事,我一點都不知道。突然間,我害怕自己吸進精神病的細菌,我很想掩住嘴巴,離開這個房間,將因失戀而心碎的青春期的我,將跪在那個無法忍受我的男人面前的我,拋在倫敦。
***
在某場電影的映後晚宴上,有人介紹了一個男人給我認識。他有著一頭飄逸的長髮,戴著阿拉伯頭巾,看起來像是全世界最娘的恐怖份子,但事實上他是一位電影明星,而他的種種事蹟,在馬蒙特莊園飯店這裡可說是赫赫有名。我們在點著燭光的花園裡促膝長談,後來他承認當晚他說的每一件事,用意都是想告訴我:「我不是妳聽說的那種男人。」
他的策略奏效了。因為他真的不是那種人。這男人就是老吉。
老吉應該是長得非常帥。(「當然了,」我老爸會這樣說:「他本來就長
得非常帥。」)但我看見的不是這一點,我看見的是他身上有種……柔軟的傷口,像是傷痕累累的天鵝絨。他身上有種可以碰觸得到的悲傷。
後來我跟他說:「那天晚上你沒有企圖想釣我。」
「我太尊敬妳了。」
「我的天啊,」我一副被冒犯的表情回道:「你只對我的內在感興趣。」
「別傻了!」他回道:「我只想和妳上床而已!」他是我所認識最悲傷的男人,卻能讓我無可抑制地大笑。
他從一個遙遠的小島打電話來,他正在那裡為一個電影角色做準備。他已經發來了無數通簡訊,將詩句截成三十個片段傳送過來。他打電話過來時是清晨五點,原因是他渴望想聽瑞奇.李.瓊斯的「骨骸」(Skeletons)。
我挑出那首歌,在電話線上播給他聽,他深吸了一口氣。
「我恐怕就要毀了這一切了。我最好還是快點掛電話,嗯,在妳不喜歡我之前掛上吧。」
這件事我沒有讓R醫生知道。我相信自己的直覺,並且打算在老吉再傳簡訊來時告訴他。他傳來訊息:「我不打算和妳在情感上有牽扯,我覺得妳會傷害我的感情。」
我立刻回覆:「啊,一想到可能傷害你可愛的感情,我立刻感到一陣反胃。」
他下一步就是飛回洛杉磯,朝我家衝來。
雨下得很大,他冒著生命危險,一邊開車一邊傳簡訊告訴我他的想法。
「別再傳簡訊。」我倉促說:「快來就是了!」
「我只是覺得,繼續用簡訊向妳求愛會比較安全。」
他走進門,低著頭,害羞得一動不敢動。他很不好意思,他因為角色要求必須減重,所以帶了自己的晚餐—一盒史多福牌的冷凍低脂千層麵—過來。他將千層麵放到我的冰箱冷凍庫裡,後來也忘了吃。
我泡茶。我們看了部老電影,然後一起看雨,看了好長一段時間。接著裘尼爬到床上來,老吉向牠打了招呼。(「哈囉,小可愛。」)然後我拿了一些詹姆士.卡格尼的未曝光照片給他看,接下來就實在沒什麼可看的,而且時間也已經半夜,所以我們決定試著睡睡看。我們在一片寂靜中躺著,就連裘尼也屏住了呼吸。
接著,在貫窗而入的透藍夜色中,他邊用飽含情慾的手指撫摸過我滿懷期待的純淨臉龐,邊說:「如果我吻妳,那就全完了。」語氣中混雜著樂觀與懊悔。
然後他吻了我。然後就是這樣了。
往泰特現代美術館接近的途中,我已經知道接下來有什麼在等著我。我將看到奧菲莉亞黃褐色的頭髮,她浮在河面上的雪白身體,以及圍繞在她身邊的花。有時候,我到達那裡時,她已經死了。有時候,她還在垂死邊緣,有可能被岸邊某個我從未見過的人救起。米雷在畫草稿時曾畫上這個人,但後來就被蓋掉了,他藏在顏料底下,為了不被看見只能輕輕地呼吸。那是個男人,會任她自生自滅的一個男人,不過換作任何人,誰會不讓她淹死呢?
雖然當時我還從未有過性經驗,但有時奧菲莉亞看起來就像正在做愛的樣子,她的手臂微微探出身體上方,雙唇微啟,像...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