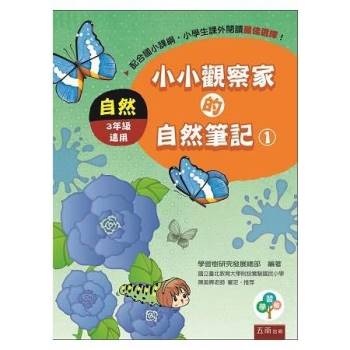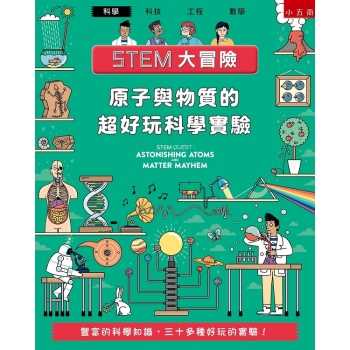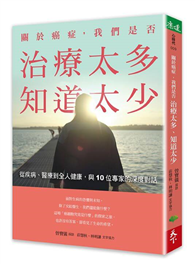在荊棘叢中下足,於月明簾下轉身 蔡昌雄
巧妙結合了印度冥思無限的瑜珈功夫,以及中國「平常心是道」之精神的禪宗傳統,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經由印度、中國、韓國、日本的一脈相承,而及於現代的西方;禪的「直指人心」,予人明快簡潔之感,回歸生命自身的號召所展露的創造張力,不僅曾在人類宗教、文學、藝術的精神文明中,綻放出耀眼的光芒,更吸引了無數熱愛生命的世代,不斷地加入這個窮究真理、體證心性的行列。著名的德國禪宗史學者杜莫林(Heinrich Dumoulin)所寫的兩部禪史鉅著(1),就為這段在印度、中國與日本的禪宗傳統,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然而論及禪法在現代世界的開展,則要首推日本鈴木大拙禪師於20世紀中期在美國的傳播之功。這股西漸的東風,一方面在學術上與西方精神分析的傳統展開對話,形成美國學術界在宗教、哲學、心理學及亞洲研究等領域中的禪學研究風潮;另一方面在實踐層次上,則與西藏密教、印度教、日蓮宗等其他東方宗教傳統的分支宗派合流,提供了新時代(The New Age)運動的外來資糧,並填補了美國社會因社會宗教世俗化而呈現的心靈空虛狀態。例如瓦茲(Alan Watts)和凱普勒(Phillip Kapleau)等人,便是從日本習禪後教導美國大眾禪法的第一代美國禪師中的代表人物。
禪的這兩股影響力經過半世紀的分進合擊與沈澱累積,已經以禪修中心的次團體形態,在美國各地隱然形成了獨特的禪修社群。把禪坐冥思的修行看成是一種社會現象的普瑞斯頓(David L. Preston)教授,針對南加州兩個禪修社群所進行的宗教社會學研究,便提供了這個社會現象層次的管窺。(2)本書作者艾茲拉?貝達禪師所承繼的平常心禪學宗派及其禪修活動,也應該被放在這個禪法西傳演變的時代脈絡中來看待,而本書的教法與內容也可以被看成是表達美國社會習禪體悟最新進境的具體縮影。
全書結構從介紹禪法修持的基本要點出發,繼之以禪法如何對治心念、轉化煩惱為抒發主題,最後以覺醒慈悲之心成就圓滿修行之功作結,層次井然地盤旋鋪疊而上。譯文的流暢貼切,為我們領會禪師的點滴經驗去除不少障礙。貝達禪師以三十年實修之功為基礎,於本書字?行間所傳達的,悉是禪宗心法的要義。他不落傳統名相窠臼,在吾人日用平常的具體情境中,雲淡風清地刻劃出禪者綿密的心地功夫,突顯了他對「至道無痕」的生動體悟。書末所載貝達禪師個人參與臨終照顧的個案紀實,尤其可圈可點,使讀者清楚認識到不假修飾地直下承接自己種種不完美的起心動念,才是禪修的真正精神,讀來令人歡喜動容。我以為這份「在荊棘叢中下足」的道心,正是貝達禪師通篇禪話的要旨所在,也是吾人對有心向禪的讀者寄予厚望之處。
依據作者的說法,生命像是在危脆薄冰上的滑行,不僅顛簸異常,而且隨時可能戳破腳下的冰層,跌落到寒冷的無盡深淵中沒頂;生命又像是瑞士乳酪或起士一樣滿佈坑洞,眼中所見到處都是荊棘與問題;當我們試圖想解決問題時,竭盡所能去做的就是極力迴避生命薄冰之下即是深淵的事實,只想要努力操控生命使其符應我們自己的幻想,而從來未能如實知見,觀照到那代表生命全體自身的整塊乳酪起士的存在。找到問題所在和看清問題本質是一切禪修或精神鍛鍊的起點,如果欠缺了這一層「見地」的把握,再多的付出也只是盲修瞎練而已,是無法使我們走上正道的。就一般的情況而言,修禪行道之所以困難,也正顯現出這層省察功夫的不易。泰戈爾有言:「我們對世界判斷錯了,所以說它欺騙了我們。」如果此言屬實,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們不能好好「照顧腳下」,如實面對生命的根本問題,而竟一再耽戀於自己編織的幻象世界中呢?
答案是:「我們迫切需要自我帶來的那份安全感。」於是我們窮畢生之力打造一座以自我為中心的王國,陷入因自他矛盾而致業網千纏的「葛藤世界」中,無力超拔解脫;我們或許會覺得奇怪,鍾愛自我並依此原則而活,又有何不妥呢?這就牽涉到我們對自我這個經驗的覺察了。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自我的結構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堅實。佛洛伊德理論中的自我(ego)是夾在本我(id)與超我(super ego)之間的可憐蟲,榮格(C. G. Jung)認為自我只是多重人格中相對穩定的情結(complex),皮亞傑(Jean Piaget)與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眼中的自我,則各自依循著某種既定的發展歷程而形變。即使從個人的日常經驗出發,我們對於自我在生命中引發的迷惑與煩惱,一定也不會感到陌生。只是多數人寧願擁抱那份環繞著自我建立的安全感,而絕少有人願意持續認真地去檢視我們立足的基石,一探生命的究竟。臨濟禪師就告訴我們,要想在動盪不安的生命之流中打造自我,猶如「虛空釘橛」(在虛空中釘釘子)一般的荒謬可笑,但這卻也是世間一切言說學問背後隱藏的動機。
因此,從禪的觀點來看,要走出自我纏繞集成的「葛藤世界」,就必須徹底擺脫自我形構世界的束縛力量,也就是要跳出從觀察者立場看待生命的慣性,以回歸生命之自身。禪理有謂「水不能濕水,火不能燒火,劍不能斬劍」,消融於生命自身中的生命,乃是無限豐盈的自足,其真如情境已非任何二元對立的外在觀點所能描寫於萬一;就像說水把水弄濕的講法,從水自身的觀點來看,實在是一件無聊透頂的事,因為水就是濕,濕就是水。這個回歸生命自身的取向是禪者一生修行的挑戰目標,關鍵之鑰則在於朗朗燭照覺性的開發,其入手處在潛入生命覺知中心的身體,其完成處則歸止於生活世界中日用平常的禪行。貝達禪師以其親身體證的功夫,在書中的每個角落都見證表達了以上的禪觀。
然而我們也必須進一步指出,雖然「在荊棘叢中下足」是起始點上邁向悟覺禪心的必要態度,但是隨著功夫日深、禪悟境界次第開展之時,禪者更要警惕到「於月明簾下轉身」的艱難。這是說隨著禪功積漸體現出舒適美好的進境時,正如同皎潔月色當空之美對簾下賞月者的誘惑一般,令禪者耽戀得舉步維艱、難以自拔,其轉圜的困難程度猶勝昔日初發心時的荊棘遍佈。任何愛美成癡的藝術家會對美藝成就境界的愛不釋手,乃是我們十分熟悉的人性經驗。此所以禪宗曰「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佛魔俱打」之真義。這個觀點在貝達禪師的禪教中,雖然可以引申推論得出,並卻沒有明確提到或強調,因此特別在此補充以提醒有志向禪的讀者。
生命的本質是愛,生命的煩惱因此也是愛,禪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去愛而又沒有煩惱的智慧。但是智慧的擷取,捨棄參與生命的苦難,即別無他途,我個人深信本書的出版即是作者生命苦難參與的分享,也是邀約讀者共同參與生命苦難、透顯生命新機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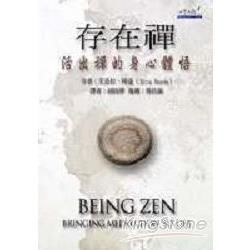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