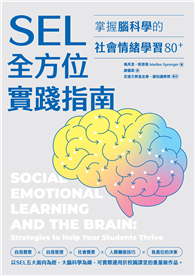第一章 概要
根據我所關注的問題,以及對我產生了影響的人物,「我的哲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唯一貫穿始終的,就是我急於發現我們到底知道多少東西,我們對它們的了解又有幾成把握。在我的哲學歷程中,存在一個主要的分界嶺,在1899到1990年間,我採納了邏輯原子主義哲學(logical atomism)以及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中的皮亞諾技術。這次天翻地覆的改變,令我之後的研究,除了像純數學這樣的方面之外,幾乎與之前毫無關聯。這兩年之間的變化是革命性的,之後的變化則是改良性的。
我對哲學的最初興趣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我非常想知道,哲學是否支持任何宗教信仰,即便這種支持非常含糊不清;另一方面,我想讓自己相信,有些東西是可以被了解的,就算在別的領域裡不行,至少在純數學中是可以的。在青春期期間,我曾孤獨地思考過這兩個問題,未曾借助書籍的幫助。結果在宗教方面,我先是不相信自由意志了,然後又不再相信永生了,最後終於不相信上帝了。而在數學基礎方面,我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儘管我非常偏愛經驗主義,但卻不相信「二加二等於四」是經驗的歸納概括。除了這個毫無益處的結論之外,我仍然對所有東西心存懷疑。
劍橋大學灌輸給我的是康德和黑格爾哲學,但是喬治·愛德華·摩爾(G.E.Moore)和我後來都拋棄了這兩種哲學。雖然我和摩爾都是叛離者,但我們各自強調的重點卻大不相同。最初吸引摩爾的,是事實脫離於知識的獨立性,以及否定康德那一套塑造體驗而非外部世界的先驗直覺和範疇。在這個方面,我非常贊同他,但是我比他更加關心一些純邏輯方面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稱之為 「外在關係學說」,它在我後來的哲學研究中占有首要地位。一元論者認為,兩項之間的關係由兩項各自的性質,以及兩項所構成的整體的性質構成,甚至嚴格說來就是整體的性質;而我認為這種觀點無法用數學解釋。我的結論是,關聯性並不意味著相關項中存在著相應的複雜性,並且一般而言,關聯性也不會等於這些項構成的整體的任何性質。我在《論萊布尼茨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一書中提出這個觀點後不久,就接觸到皮亞諾(Peano)在數理邏輯方面的研究,讓這我有了新的數學技術和數理哲學。黑格爾和他的信徒們慣于「證明」 時間、空間、事物,以及常人所相信的一切東西的不可能性,我認為他們的這些論辯都不能成立,而且我還走向了與其相反的極端,認為凡不能被證偽的東西都為真,例如點、瞬、粒子和柏拉圖的共相。
但是,我在1910年完成了我想做的純數學研究之後,就開始考慮研究物理學。主要是在懷特海(Whitehead)的影響下,我進入了這個又可以應用奧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的新領域;由於奧卡姆剃刀在算術哲學中的妙用,我早就成了它的擁躉。懷特海告訴我說,人們無需假設點、瞬是世界的構成要素,就可以研究物理學。他認為物質世界可以由可事件構成,每個事件占據有限的時空,在這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凡是在運用奧卡姆剃刀的時候,我們都不必去否定我們不需用到的存在體的存在,也無需去查明它們是否存在。無論在解釋哪個門類的知識時,都需要進行一些假定,而這樣做有助於減少假定。在物質世界中,要證明點、瞬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證明,物理學沒有任何理由來假定點、瞬的存在。
與此同時,即從1910年到1914年,我對物質世界是什麼,我們如何認識它很感興趣。自那時以來,我就開始斷斷續續地思考感知與物理學之間的關係。我在哲學觀念上的最後一次重大變化正和這一問題有關。我原本以為感知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兩項關係,因為這比較容易解釋為何感知會帶來主體以外的知識。然而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響下,我認識到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或者至少是過於簡單化了。在我看來,至少感覺,即使是視覺和聽覺,在本質上也不是關係性的事件。當然我不是說,當我看到某個東西時,我和我看到東西沒有關係,我的意思是,這種關係比我原以為的更加間接得多;而且,我在看到東西時發生的內在反應,僅僅就其邏輯結構而言,就算我沒有看到任何外界東西,也是有可能發生的。我的看法轉變了,這讓體驗與外部世界的連結問題的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大約在同一時間,即大約1917年期間,我還對語言和事實之間的關係問題產生了興趣。這個問題分兩個部分:一個和詞彙有關,第二個則涉及句法。在我開始感興趣之前,已經有無數人士探討了這個問題。韋爾比夫人(Lady Welby)關於這個主題寫了一本書,席勒(F. C. S. Schiller)也一直強調其重要性。但是我之前一直認為語言是透明的,也就是說,人們並不需要耗用注意力就可以使用語言這種媒介物。在句法上,數理邏輯中產生的矛盾讓我不得不接受這個看法的不足。至於詞彙,當我研究在哪種程度上可以用行為主義來解釋時,才遇到了語言問題。基於這兩個原因,我比以往更加重視認識論的語言方面。但我從未贊同過把語言當做自主範圍的看法。語言的本質是它的意義,意義令它與本身之外的東西相連,而這種東西一般而言是非語言的。
我最近的工作涉及非證明推理的問題,經驗主義者曾認為是歸納法讓這種推理成立。不幸的是,事實證明,如果不顧及常識地通過簡單枚舉進行歸納,其結果往往是謬誤而非真理。而如果一個原理需要在常識的説明下才能可靠地使用,它是不會令邏輯學家感到滿意的。因此,如果我們想從大體上接受科學以及那些不可駁斥的常識,我們就必須在歸納之外另尋原則。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而我獲得的成果僅僅是指出了一些道路,人們也許可以沿著這些道路找到解決辦法。
自從我放棄了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之後,我一直試圖通過分析來尋找哲學問題的解決辦法;儘管現代的一些趨勢與此相反,而我仍然堅定地相信,只有通過分析,才有可能取得進步。舉一個重要的例子來說,我發現,通過分析物理學和感知,完全可以解決心智與物質的關係問題。的確,我所認同的解決方案現在還沒有被大家接受,但是我相信並希望,這只是因為大家還沒有理解我的想法而已。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英.伯特蘭.羅素的圖書 |
![我的哲學的發展[1版/2021年6月/1W0N]](https://www.wunanbooks.com.tw/NewPhoto/978/986/522/264/2/S_9789865222642.jpg) |
$ 285 ~ 361 | 我的哲學的發展[1版/2021年6月/1W0N]
作者:英.伯特蘭.羅素 出版社:五南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的哲學的發展
《我的哲學的發展》(MyPhilosophicalDevelopment)是羅素(1872~1970)寫於1959年的一部著作,是羅素自己哲學思想發展的一個回顧及對自己哲學思想的總結。他很重視自己在1914年和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三卷本)一書的成就。他在本書建立了邏輯主義數學體系,旨在把整個數學歸結為邏輯學,重點敘述《數學原理》的基本思想,也作為研究羅素哲學思想的第一手材料,有其特殊的價值。
二十世紀當代的許多哲學家和哲學流派受羅素影響最深的要算維根斯坦哲學以及整個邏輯實證主義學派。
作者簡介: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無神論或者不可知論者。羅素被認為是與弗雷格、維根斯坦和懷特海一同創建了分析哲學。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對邏輯學、數學、集合論、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有著巨大影響。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學史》、《數學原理》、《物的分析》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概要
根據我所關注的問題,以及對我產生了影響的人物,「我的哲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唯一貫穿始終的,就是我急於發現我們到底知道多少東西,我們對它們的了解又有幾成把握。在我的哲學歷程中,存在一個主要的分界嶺,在1899到1990年間,我採納了邏輯原子主義哲學(logical atomism)以及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中的皮亞諾技術。這次天翻地覆的改變,令我之後的研究,除了像純數學這樣的方面之外,幾乎與之前毫無關聯。這兩年之間的變化是革命性的,之後的變化則是改良性的。
我對哲學的最初興趣來源於兩...
根據我所關注的問題,以及對我產生了影響的人物,「我的哲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唯一貫穿始終的,就是我急於發現我們到底知道多少東西,我們對它們的了解又有幾成把握。在我的哲學歷程中,存在一個主要的分界嶺,在1899到1990年間,我採納了邏輯原子主義哲學(logical atomism)以及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中的皮亞諾技術。這次天翻地覆的改變,令我之後的研究,除了像純數學這樣的方面之外,幾乎與之前毫無關聯。這兩年之間的變化是革命性的,之後的變化則是改良性的。
我對哲學的最初興趣來源於兩...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概要
第二章 我現在的世界觀
第三章 最初的嘗試
第四章 唯心主義之旅
第五章 叛入多元論
第六章 數學中的邏輯技術
第七章 數學原理:哲學方面
第八章 數學原理:數學方面
第九章 外在世界
第十章 維根斯坦的影響
第十一章 認識論
第十二章 意識和體驗
第十三章 語言
第十四章 共相、殊相和名稱
第十五章 “真理”的定義
第十六章 非論證性的推理
第十七章 放棄畢達哥拉斯
第十八章 對一些批評的回應
羅素哲學發展之研究
第一章 概要
第二章 我現在的世界觀
第三章 最初的嘗試
第四章 唯心主義之旅
第五章 叛入多元論
第六章 數學中的邏輯技術
第七章 數學原理:哲學方面
第八章 數學原理:數學方面
第九章 外在世界
第十章 維根斯坦的影響
第十一章 認識論
第十二章 意識和體驗
第十三章 語言
第十四章 共相、殊相和名稱
第十五章 “真理”的定義
第十六章 非論證性的推理
第十七章 放棄畢達哥拉斯
第十八章 對一些批評的回應
羅素哲學發展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