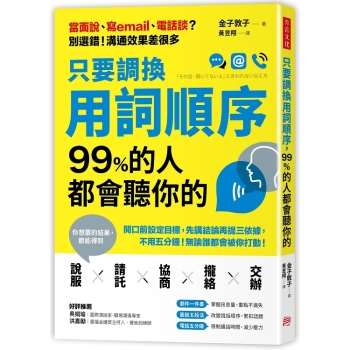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 六度赴白宮受獎 美國優良教師獎得主最新力作
■ 中國時報「開卷」、國語日報「星期天書坊」 介紹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丁亞雯 等各界人士 感動推薦
■《深夜小狗神祕習題》怪才少女 +《潛水鐘與蝴蝶》真摯動人
■ 河濱街教育學院「最佳童書獎」、兒童文學大會「最受矚目好書獎」
每個人都不完美。
我很慶幸我不完美的地方是肢體,而不是心靈。
11歲女孩玫樂娣天資聰穎,文字和音樂對她而言有無法抗拒的魔力。她比同齡的孩子懂得更多、更優秀。可惜的是,她的聰明才智都被卡在腦袋裡,沒有人能與她分享。因為她罹患了腦性麻痺──她無法走路,也無法說話。
旁人看到的,只是一個坐在輪椅上手腳亂踢、口水滴溼前襟、不停發出刺耳尖叫的小女孩,極少人能看透外表,注意到她豐富的內在。有時她覺得自己就像一隻生活在魚缸裡的金魚,終日困在牢不可破的玻璃牢籠裡。她多想掙脫無法行動、無法言語的身軀,讓心的翅膀自由翱翔!
媽媽堅持讓玫樂娣上一般小學,玫樂娣在特殊教育班裡認識了唐氏症的眉俐雅、自閉症的葛洛禮亞、過動兒威利……她真心喜歡這群同學,外界對待他們的態度卻總是恐懼和誤解。尤其在「融合課程」(特教班學生和普通學生一起上課)開始後,玫樂娣更加體會到老師及普通班孩子對他們的害怕和排斥。
一天,學校宣布即將進行全校「小天才競賽」的校內甄選。獲勝的隊伍不但能代表學校參加全州的比賽,晉級後更能坐飛機去華盛頓參加Live實況轉播的全國性決賽!所有同學都躍躍欲試,參加初選,包括玫樂娣在內。但多數人對她的參賽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沒想到,玫樂娣竟得到全校最高分!懷抱著希望的玫樂娣覺得自己終於被認同了,但現實的發展卻不是她所預期的那樣……。
玫樂娣的異想語錄
■ 「我不能說話,不能走路;我不能自己吃飯或上廁所。有夠遜。」
■ 「我猜我是一次一點點地發現,自己與一般人不一樣。因為我從來沒有思考或記憶方面的困難,所以當我發現自己做不來很多事時,真是嚇壞了,而且,氣得很。」
■ 「我彷彿住在一個沒有門、沒有鑰匙的洞穴裡,我無法教人家怎麼救我出去。」
■ 「除了我自己,沒有人知道這些知識全在我腦袋裡。連媽媽也不曉得,即使她擁有『媽媽的直覺』,知道我了解很多東西。但她仍然所知有限。沒人知曉,沒人。這讓我快抓狂了。」
■ 「我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你怎麼了?』人們通常想知道我是不是生病、會不會痛,以及這情況有沒有藥醫。我準備了兩套答案――一套冗長但保持禮貌,另一套則是反唇相譏。對那些真誠關心我的人,我讓語言機替我說出:『我的症狀叫做痙攣性雙側四肢麻痹症,一般簡稱腦性麻痹。這種病限制了我的肢體,但並沒影響我的心智。』我覺得最後一句很酷。
至於對付那些不友善的人,我會說:『你看得到我的不完美,看得到自己的嗎?』」
本書特色
■ 本書不同於坊間同類型書籍,並沒有濃厚的「悲情」/「勵志」色彩或說教意味,仍保有「小說」的故事性和閱讀樂趣。
■ 本書讓青少年讀者體認到,擁有健全的身心是何其幸運,而身心障礙孩童最需要的並不是「憐憫」,而是「保持平常心的對待」。
■ 「每個人都有不完美之處」/「接納自己和旁人的不完美」,更是青少年需要學習的課題。
作者簡介:
莎倫.德蕾珀 (Sharon M. Draper)
創作豐富,曾獲約翰史戴普創作新秀獎 (John Steptoe New Talent Award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青少年圖書獎、名列《紐約時報》暢銷作家,並五度榮獲史考特金獎 (Coretta Scott King Award),六度赴白宮受獎。得獎著作包括《老虎的眼淚》、《傑利科的奮戰》、《古銅烈日》、《十一月的憂鬱》等青少年小說。
其中,《古銅烈日》被美國政府選為「以閱讀跨越文化」計畫的指定書籍。
德蕾珀曾任教中學二十五年,獲選「全國優良教師」(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她熱衷於推廣教育和閱讀寫作,參與多個相關團體與活動,常應邀到美國各地和其他國家發表演講。德蕾珀目前與丈夫及黃金獵犬「哈妮」定居美國俄亥俄州。
譯者簡介:
趙映雪
主修兒童文學的作家及譯者。曾結合她所熱愛的網球與對肢障者的關懷,寫出得獎小說《Love:人生球場,愛與掛零》;而書寫聽障者的《奔向閃亮的日子》獲選《中國時報》年度十大童書。結合自身生活經驗的《美國老爸台灣媽》,是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次數最多的小說之一;描寫中學歲月的《漫舞在風中》,深受青少年喜愛。
目前的她住在藍天大海間,沈迷於網球、閱讀與寫作裡。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譯序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不一樣
我從小長大的家,和大多數人的家不一樣,因為我們家有兩名所謂的「殘障者」:一個是我爸爸,「行動不便」;另一個是我二哥,「聽覺障礙」。可是,在那個家生長了二十幾年,我沒有一天覺得自己的家和別人家有何兩樣。
當然,同學第一次來我們家會問我:「你爸爸的腳怎麼了?」我會毫無芥蒂地告訴他們:「我爸爸四十歲那年有一天,和每天一樣十點鐘上床睡覺。沒想到,隔天早上六點鐘醒來,他的兩隻腳已經癱瘓。」我一點都沒誇張,事情真的是這樣。那年,我爸爸要養一家十口,他拒絕讓自己倒下去。所以他努力復健,讓自己可以像個兩歲小孩那樣站起來、一步一步地走路。可是,他的腳卻再也無法牢牢抓地,更不用說跑、跳或爬坡了,而且只要輕輕推他一下就倒了。他就用這樣的一雙腳,繼續到工地監工;養家的責任完成後,他就用這樣一雙腳,走遍全世界。陌生人自然常用異樣的眼光盯著他看,但他毫不在乎,還笑著說:「我的人生目標已經達成,我很滿意。」
同學再多來幾次便會發現,我們家那非常帥氣的二哥,也和別人不一樣。「我哥哥天生重聽,聽力只有一般人的一半。你跟他講話,要放慢速度、提高音量,讓他看到你的表情,他就會明白你的意思。」後來,二哥有了助聽器,我卻常常挨罵,因為他習慣了靜悄悄的周遭,一旦所有雜音都被放大,他反而無法適應,整天對我嘮叨:「女孩子家,怎麼那麼粗手粗腳啊?」
收銀機還未普及以前,二哥出門買東西時,只要多問兩次價錢,店員就不耐煩。他到銀行或公家機關辦事,要留意何時輪到自己,因為他聽不見廣播。可是二哥從沒把這當作不出門的藉口,他的方法是到哪裡都真心待人,久而久之,行員會用揮手的方式向他示意。讀二專要離家住校,二哥也沒猶豫,第一個寒假就帶了一大群朋友回家。也許他曾想過,如果不要重聽該有多好。但他無法改變事實,便微笑面對。
即使爸爸和二哥這兩個領有「殘障手冊」的家人心態都很健康,我還是為他們各寫了一本小說,目的是為了讓大眾了解,對他們而言,外界的障礙在哪裡,提醒大家對這群特殊的朋友多付出一些時間和耐性。我一直以為,自己會比一般人更能對身心障礙人士感同身受,沒想到翻譯《聽見顏色的女孩》後,還是使我頗為自責。
女兒上幼稚園時,班上有一名罹患腦性麻痹的同學凱希,她和書中的玫樂娣一樣,不能說、不能走,甚至臉部毫無表情,但她比玫樂娣幸運的地方,是還有幾根指頭可聽使喚,可以用手語做簡單溝通。那年,女兒全班都學了手語,好能和凱希「說話」。
導師常提醒孩子,凱希很聰明,要多和她「說話」。我在女兒班上當了一年志工媽媽,可能是受到「腦性麻痹」這個醫學名詞的誤導,我就像書中的可蕾兒,從來沒想過「凱希很聰明」這五個字的意義。我不會手語,無法跟凱希交談,每週待在那教室兩個鐘頭,我居然無視她的存在,沒跟她說聲「嗨」,也沒問過她需不需要任何幫忙。
直到讀了《聽見顏色的女孩》,我才發現自己大錯特錯。我和書中那幾個不夠體貼的老師和同學一樣,也許曾經深深傷害了凱希的心。可蕾兒攻擊玫樂娣的武器是語言;而大部分的人是不是和我一樣,對身心障礙人士攻擊的武器是「視而不見」呢?
這本書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道出埋藏在玫樂娣心中十一年的話語,真摯感人。相信所有人讀了這本書,都會對腦性麻痹患者有深刻、真切的認識,從而修正自己看待他們的眼光。其實,身心障礙人士不管是哪一方面不方便,和一般人並沒有那麼不一樣。他們的心願很簡單:尊重他們的不一樣,多點耐心等待他們,也就夠了。我想,這也就是作者透過這本書,最想要達成的目的了。
丁亞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聽見顏色的女孩》一書,描寫特殊需求孩童的成長和心路歷程,不僅鼓舞了這些孩童和家長,也讓特教人員深省與反思。
所有「正常」的孩童,也能在這本書中學習到「接納自己和旁人的不完美」。我願意推薦這本書給所有青少年。
吳怡慧,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助理教授
本書帶領讀者乘著玫樂娣心靈的翅膀,飛進她充滿色彩、香氣和文字的內心世界;她的樂觀開朗令人動容。
我們身邊也有許多像玫樂娣這樣的「愛奇兒」(特殊需求兒童),這些特別的孩子讓我們更加認識生命的奧妙,並且學習「珍惜擁有」。
看完這本書,我們應該鼓勵孩子學習玫樂娣的同學玫瑰,用坦誠與愛心和這群看似無聲的朋友來往。我相信,這是最好的「寬容」與「接納」的功課。
卓碧金,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理事長
玫樂娣以輕快的筆觸道盡自己成長中面對的考驗;讀完她的故事,彷彿穿著她的鞋走過一遭,感同身受。她對生命的熱愛令人感動,值得學習。
許多腦麻患者都和玫樂娣一樣,在不靈活的軀體之下,擁有無限的潛能;只要給他機會,他一定會讓你驚嘆。
胡昭安,腦麻兒家長、《渝緹的奇幻旅程》作者
我家也有一個極重度的腦性麻痺兒童,就是我的寶貝女兒――渝緹。
看了書中主角玫樂娣的故事,我好像該慶幸女兒沒那麼聰明,所以不用受那麼多苦。
上天安排什麼樣的孩子到你家,我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只能用我們所知道的方法去愛她,也甘願受照顧她的苦。
我的孩子能表達對父母的愛,但是十二歲的她無法告訴我們她為什麼生氣,或是她想要的是什麼。
如果我的孩子肢體更靈活,如果我的孩子也有一台溝通用的機器可以和世界對話,結果會如何?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期待大家看了這本書,能夠多一點體貼給這些特別的孩子,包容他們的不同與緩慢,降到他們的高度,讓他們告訴你這世界有多美好!
黃美廉,腦性麻痺畫家、藝術博士
閱讀這本書,對來我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本書主角和我一樣罹患腦性麻痺,我不得不回想小時候所遭遇過的「霸凌」和不平等的對待,這些都是令人傷感的記憶。
但一字一字讀下去,就知道人的尊嚴和人性善惡所給予身障孩子的影響。現今教育體系或許能使一般孩子不排斥身障孩子,但能夠做到「平等對待」嗎?我想,真正的平等是,社會上大部分的人都認知到身障者也有他們的尊嚴、責任,和一般人並沒有不同。
我要強調一點:腦麻患者並非都是天才,也並非都是白癡。一個人的豐富,取決於內在而不是外表,但是身障者往往因為外表不完美,而失去展現內在的機會。
希望《聽見顏色的女孩》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和接納每一個孩子(不只是身障孩子),啟發孩子們的創意和愛。
賴欣巧,腦性麻痺患者、臺大歷史系學生
從小因為腦性麻痺造成的肢體障礙,我和玫樂娣一樣飽受歧視。事實上,玫樂娣可以洞悉外界,旁人卻看不到她美麗的內心世界。
智力未受損的腦性麻痺患者,潛力超乎你的想像;《聽見顏色的女孩》會讓你用新的眼光看待他們。
媒體推薦:
《學校圖書館期刊》
充滿勇氣、真誠坦率、引人入勝。這是一本意義深遠的好書。
《科克斯書評》
堅毅不屈、真實感人。
《書目雜誌》
這本振奮人心的小說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
名人推薦:譯序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不一樣
我從小長大的家,和大多數人的家不一樣,因為我們家有兩名所謂的「殘障者」:一個是我爸爸,「行動不便」;另一個是我二哥,「聽覺障礙」。可是,在那個家生長了二十幾年,我沒有一天覺得自己的家和別人家有何兩樣。
當然,同學第一次來我們家會問我:「你爸爸的腳怎麼了?」我會毫無芥蒂地告訴他們:「我爸爸四十歲那年有一天,和每天一樣十點鐘上床睡覺。沒想到,隔天早上六點鐘醒來,他的兩隻腳已經癱瘓。」我一點都沒誇張,事情真的是這樣。那年,我爸爸要養一家十口,他拒絕讓自己倒下去...
章節試閱
1
文字。
我被好幾千個文字包圍。也許是好幾百萬個。
大教堂。美乃滋。紅石榴。
密西西比州。那不勒斯人。河馬。
像絲綢一樣柔軟。駭人的。如彩虹般燦爛。
搔癢。打噴嚏。盼望。擔憂。
一直以來,文字如同片片雪花繞著我打轉——每個字都優美精緻、與眾不同;每個字都完整地在我手中融化。
在我的內心深處,文字大片大片地漂流進來,不斷堆積。一層又一層的片語、句子、連貫的構想。機智慧黠的說法、玩笑、情歌。
從我還很小很小開始──說不定才幾個月大──文字就如同甜蜜的糖漿那樣送上來,我彷彿喝檸檬汁般地盡情暢飲,幾乎可以舔出那味道。文字讓我混雜的思惟和感受變得具體。爸媽一直用交談和話語將我緊緊裹住,他們在我身旁聊天、嘮叨,什麼都說出來,甚至唱出來。爸爸總是對著我唱歌,媽媽輕聲傾吐她對我的支持。
爸媽對我說的每一個字,以及關於我的每一句話,我都一一吸收、儲存,而且記了下來。所有的字。
我不明白我是如何解開那些謎一般的文字和思想,這些東西就是迅速、自然地在我心裡自動化開。差不多才兩歲大,我所有的記憶都有了文字,我所有的文字都富有意義。
然而,這些文字和意義只能堆積在我的腦海。
我不曾開口說出一個字。而現在,我差不多十一歲了。
2
我不能說話,不能走路;我不能自己吃飯或上廁所。有夠遜。
我的手臂和手掌十分僵硬,但我能夠用力按壓電視遙控器上的按鈕,也能靠著輪椅上的旋鈕,控制輪椅移動。我抓不住一支湯匙或鉛筆,一拿就掉。我的平衡能力更是零——連蛋頭先生都比我厲害。
人們看我時,我猜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矮小、黝黑、一頭鬈髮、被五花大綁在粉紅色輪椅上的小女孩。我得說明,粉紅色輪椅一點都不可愛。粉紅色沒能改變任何一項事實。
他們看到女孩有雙深棕色、充滿好奇的眼睛,但其中一隻有點鬥雞眼。
她的頭沒能鎖緊。
有時還流口水。
她看起來實在很小,對一個十歲又九個月大的女孩而言。
她的雙腿纖細,也許是因為未曾使用過的緣故。
她的身子會不自主地抽動,兩隻腳有時突如其來地就踢了出去,雙臂不時胡亂揮舞,身邊有什麼就碰倒什麼──不管那是一疊CD、一碗湯,或是插了玫瑰的花瓶。
她對自己的身體沒多少控制力。
在人們一一列出我的毛病後,也許有人會忽然發現,我的笑容其實滿好看的,而且還有深深的酒渦──我覺得我的酒渦相當迷人。
我還戴著小小的金色耳環。
有時,人們甚至沒過來問我叫什麼名字,彷彿這一點也不重要還是怎樣。當然重要嘍,我的名字是玫樂娣。
我能夠記得很小很小時候的事情。當然了,要將真實記憶和爸爸為我拍攝的錄影帶畫面分開是很難的。那些錄影帶,我看了有一百萬次吧。
媽媽將我從醫院帶回家──她的臉上泛著笑意,可是眼光閃著憂慮。
玫樂娣被放進一個小小的嬰兒浴缸,四肢看起來好瘦弱,沒拍水也沒踢水。
玫樂娣墊著毯子,躺在客廳沙發上──臉上帶著滿足的神情。從還是小娃娃起,我就很少哭;媽媽發誓,真的是這樣。
洗過澡後,媽媽用乳液為我按摩全身——此刻我還能聞到薰衣草的香味——然後用一條附帶小帽子的毛茸茸浴巾將我裹住。
爸爸拍的錄影帶裡,有我被餵飯、換尿片,甚至睡覺的鏡頭。我漸漸長大,我想他一定在等著我翻身、坐起來、走路。我卻沒能做到。
但其實我吸收了一切。我開始能辨別聲音、氣味以及口感。每天早上暖氣爐跳動起來的一聲轟,和燃燒時的嘶嘶聲;屋子燒暖時,灰塵被加熱的刺鼻氣味;還有卡在喉頭想打噴嚏的感覺。
包括音樂。旋律流過我身上,然後就停留了下來。催眠曲糅雜在柔軟的「睡覺時間」的氣味之中,伴我一起入眠。音樂讓我微笑。我的生命一直播放著上了色彩的背景音樂。在音樂中,我幾乎能聽見顏色、嗅出畫面。
媽媽喜愛古典音樂。一整天,她的音響流出的都是貝多芬激昂、慷慨的交響曲。當我聆聽時,這些樂曲似乎都是蔚藍色的,聞起來像剛漆上的油彩。
爸爸偏愛爵士樂,一有機會,他便朝我眨眨眼,取下媽媽的莫札特,放進邁爾士.戴維斯或是伍迪.賀曼的CD。對我而言,爵士樂聽起來是棕色或金黃色的,聞起來如同潮溼的塵埃。爵士樂會讓媽媽抓狂,這或許也是爸爸喜歡播放爵士樂的原因。
「爵士樂讓我全身發癢。」爸爸的音樂忽然在廚房響起時,媽媽會皺著眉頭這麼說。
爸爸走向她,溫柔地抓抓她的手臂和背後,然後擁抱她,她就不再皺眉了。但爸爸一離開房間,她便迅速換回古典樂。
不知為何,我向來喜歡鄉村樂曲──那種喧鬧響亮、撥動著吉他、令人心碎的音樂。鄉村樂曲就像檸檬──不酸,而且如同蜜糖一樣甜美而濃烈。檸檬蛋糕上的糖霜,沁涼、新鮮的檸檬汁!檸檬,檸檬,檸檬!我愛檸檬。
記得還很小的時候,有一次坐在廚房裡,媽媽餵我吃早餐,收音機忽然播出一首歌,一首讓我歡悅得叫出來的歌。
於是我唱著
艾爾薇拉,艾爾薇拉
我的心在燃燒,艾爾薇拉
馬兒快跑,呣啵啪呣啵啪,哞哞
馬兒快跑,呣啵啪呣啵啪,哞哞
嗨吼,銀色馬兒,快跑
我為何早已熟知這首歌的歌詞和節奏?不知道。之前這首歌一定早已透過某種方式滲進我的記憶──也許是收音機,或電視節目。反正,我差點沒掉出椅子。我的臉扭成一團,開始抽搐、痙攣,拚命朝著收音機比畫,還要再聽一次。但媽媽只是盯著我,好像我在發什麼神經。
她怎麼能了解,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我為何會愛上橡樹嶺小子唱的〈艾爾薇拉〉?我無從解釋,樂聲響起後,我是怎樣從旋律中聞到新鮮檸檬切片的味道,還看到帶著果粒的音符在飛揚。
要是我有畫筆──哇!那會是怎樣的一幅畫啊!
但媽媽只是搖搖頭,繼續往我嘴裡送進一瓢一瓢的蘋果泥。媽媽不明白的事情可真多。
我想,無法忘記任何一件事應該是好的──我能夠將生命中每個片刻塞進腦裡。但同時也很令人沮喪,因為我無法與人分享其中任何一件,而且沒有一件願意離開。
我記得某些蠢事,感覺像喉頭卡了團燕麥,或是舔到牙齒上殘留的牙膏。
清晨的咖啡更是深深烙印的記憶,混雜著煎培根的香味,和晨間新聞主播在電視上滔滔不絕的背景噪音。
然而,我記得的大部分是文字。我很早就明白,世界上一定有好幾百萬個文字。在我身邊的每個人,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地說出文字來。
電視購物台的主持人:買一送二!限時搶購!
來到門外的郵差:早安,布魯克司太太,孩子怎麼樣啦?
教會唱詩班: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門。
超市店員:感謝您的光臨。
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能用文字來表達自己。我敢說,大部分人沒能了解文字的真正力量。但我了解。
思想需要文字,文字需要聲音。
媽媽剛洗完頭,我好愛聞她髮上的味道。
爸爸刮鬍子前,我好愛他那刺刺的鬍碴。
但我從來沒能告訴他們這些話。
3
我猜我是一次一點點地發現,自己與一般人不一樣。因為我從來沒有思考或記憶方面的困難,所以當我發現自己做不來很多事時,真是嚇壞了,而且,氣得很。
在很小的時候,爸爸給我帶回一隻布偶小貓咪──那時我還不到一歲,我很確定。那是隻潔白、柔軟的小貓咪,剛好是我胖胖的娃娃指頭可以抓起的大小。我坐在地板上的嬰兒提籃裡──綁得牢牢的,好讓我可以安全地張望身邊的粗毛綠色地毯,和顏色相配的沙發。媽媽將布偶貓放進我手裡,我露出微笑。
「看,玫樂娣,爹地給你帶了隻漂漂咪咪。」媽媽用那種大人跟小孩講話時故意裝出的娃娃音對我說話。
好啦,什麼是「漂漂咪咪」?好像平常要應付那麼多真實的事物還不夠困難,現在我還得想辦法去了解這些捏造出來的字!
不過我喜歡這隻小貓咪舒舒柔柔的毛。沒想到貓咪一下子就掉到地上,爸爸將貓咪放回我手上。我真的想抓住貓咪,抱緊貓咪。但是,再一次,它又掉了下去。我記得自己非常生氣,大哭了起來。
「小乖,再試一次。」爸爸說著,可是他的語氣之中帶著憂慮。「你做得到
的。」爸媽一次又一次將貓咪放回我手中,可是我小小的指頭始終抓不住它,貓咪總是跌回地毯上。
接下來,我自己也跟著摔到地毯上,我猜這也是整件事我能記得如此清楚的原因。挨得夠近去看時,這種綠地毯真的很醜。在我出生前,就已經不流行粗毛地毯了。我常常掉在那裡、等著有人將我抱起來,所以我有非常多的機會去研究這種地毯的織法。我沒法翻身,所以被救起來以前,那景象就是——氣呼呼的我、粗毛地毯,加上被打翻在我臉上發酸的豆奶味。
不坐娃娃椅時,爸媽會在我的身體兩邊塞緊枕頭撐著。我看見從窗戶射進來的光束,轉著頭追隨那些飄浮在光束裡的小塵埃,然後,砰,我整個人臉朝下地摔趴下去。我尖聲大叫,爸爸或媽媽其中一人會過來抱起我、安撫我,試著更牢靠地把我平衡在那一堆枕頭之間。可是沒幾分鐘,我再次趴倒。
這時,爸爸會做出一些很好笑的動作,像是學《芝麻街》裡的青蛙那樣跳,我笑了出來,結果再次摔倒。我不要跌倒,更不想跌倒,但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真的毫無平衡力,零。
那時我自己還不明白,但爸爸早已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嘆了口氣,把我抱到他腿上,緊緊摟住我,再把小貓咪,或任何我當時感興趣的玩具拿過來,讓我可以摸到。
雖然爸爸也會編造新字,但他從沒像媽媽那樣用童音童語講話。他總是用和大人對談的語調跟我說話,用真正的文字,認定我會聽得懂。他是對的。
「你的日子不會好過的,小玫樂娣,」他輕聲說道:「要是可以的話,我想都不想就跟你交換了。你明白這點吧?」
我只能眨眨眼,但我懂他的話。有時候,他的臉上爬滿淚水,他會在晚上抱著我走到屋外,朝著我耳朵輕聲細語地說著星星、月亮,和晚風。
「孩子啊,天上的星星為你而演出,」他說:「看那令人驚豔的星光秀!感受到風了嗎?它在搔你的腳趾頭呢。」
而到了白天,有時候爸爸會解開媽媽堅持一定要捆在我身上的小毯子,讓我去感覺晒在臉上、腿上的陽光溫度。
他在陽台掛上餵鳥器,我們一起坐在那裡,看著鳥兒翩翩來訪,一次啄一粒種籽。
「紅色的是紅雀,」爸爸告訴我,「那邊那隻是藍鵲。牠們相看兩討厭。」說完就笑了出來。
爸爸最常做的,就是為我唱歌。他的嗓音清亮,似乎是特別為披頭四的〈昨日〉、〈我想牽你的手〉這樣的歌打造的。爸爸最愛披頭四。不,沒有人能理解父母,還有他們為什麼喜歡那些東西。
我的聽力向來靈敏。我記得聽著爸爸的引擎聲轉進我們這條街、駛入車道,然後撈著口袋找鑰匙。進門後,他將鑰匙丟在底層台階,接下來就是冰箱門被打開的聲音——兩次。第一次是找飲料,第二次是找一大片慕恩斯特乾酪。爸爸最愛吃乳酪了,不過乳酪常常害他消化不良。爸爸能製造出最大聲、最臭的屁來。我不知道他上班時如何克制,或者有沒有嘗試要克制,可是他一回到家,馬上就毫不節制了。邊踩樓梯一定邊放屁。
踩,屁。
踩,屁。
踩,屁。
等他終於走進房間時,我已經快要笑死了。他靠到床邊來親我,用一嘴的薄荷味。
只要有時間,爸爸就會為我朗讀。我知道他一定已經累了,但他還是會微笑著,挑出一、兩本書,我就能隨著他進入野獸國,或跟著戴帽子的貓,看牠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說不定我比爸爸更早就背下了書中的每一個字。《月亮,晚安》、《讓路給
小鴨子》,還有很多的書。爸爸為我念過的每一本書的每一個字,都永遠刻在我的心上。
事情是這樣的:我實在是聰明得過頭,很確定我擁有照相般無比清晰、過目不忘的記憶力。這就像我腦袋裡有個照相機,每當我看到或聽到什麼資訊,一按下快門,便永久留存。
我在公共電視看過一個報導天才兒童的節目。這些孩子能夠記住很複雜的長串數字,或是打散的文字和圖畫的排列順序,還能一字不差地背誦長篇詩詞。我也可以。
我記得每個電視購物台的免付費電話、地址,以及網站。倘若將來我需要一組新的刀子或最完美的健身器材,資訊已經都存在我的腦海。
每一齣電視劇的所有男女演員的名字,我全都知道;節目幾點上演、哪個頻道,還有哪些是重播的,通通難不倒我。甚至連劇中的所有對話、穿插的廣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有時,我真希望腦袋裡有個刪除鍵。
我的輪椅安裝了一個電視遙控器,就在我的右手邊。左手邊的遙控器,則是用來控制收音機。我的拳頭和大拇指有足夠的控制力來按按鈕,所以有辦法任意轉台,我真的很高興這點!連續二十四小時看名人摔角或電視購物,真的會讓人瘋掉!我可以調整音量,倘若有人事先幫我把DVD片子放好,我還能夠自己放片子。很多時候,我都是在看爸爸為我拍的舊錄影帶。
我還喜歡看有線頻道介紹古早的國王以及他們征服的王國,或是醫師治癒了某種怪病。我看了火山、鯊魚、雙頭狗,以及埃及木乃伊等專輯,全都記得,一字不漏。
只是,這有什麼用呢?除了我自己,沒有人知道這些知識全在我腦袋裡。連媽媽也不曉得,即使她擁有「媽媽的直覺」,知道我了解很多東西,但她仍然所知有限。
沒人知曉,沒人。這讓我快抓狂了。
於是,每隔一陣子,我就要瘋狂地失控一次。徹底失控。我的手腳僵直,像暴風雨中的樹枝那樣猛烈揮舞,甚至連我的臉也糾結成一團。我無法順暢呼吸,但為了大吼大叫和扭動,我又必須呼吸。這不是癲癇,癲癇是醫學上的問題,而且會讓你昏睡過去。
這些症狀──我稱它為「龍捲風爆發」──是我的一部分。所有我控制不了的東西,一古腦不安地迸發出來。我無法停止,就算我竭盡全力也沒辦法。即使我知道這樣會嚇壞許多人,但我就是失控了。這畫面是很難看的。
有一回,差不多四歲吧,媽媽帶我上大賣場,就是那種從牛奶到沙發都賣的地方。那時我還小,可以坐進推車前的兒童座。媽媽總是有備而來,她會在我四周塞上很多枕頭,讓我不至於歪倒。那時推車裡已經丟進了衛生紙、漱口水和清潔劑,我東張西望,很享受這段旅程。
接著,在玩具部,我看到了整組色彩鮮豔的塑膠積木。就在那天早上,電視新聞才對這種玩具發出警告──廠商宣布回收這種積木,因為積木表面的漆含鉛。好幾個孩子已經因為鉛中毒住進醫院。可是危險玩具就在這兒——仍然擺在貨架上。
我指著玩具。
媽媽說:「不行,小乖,你不需要這種玩具,家裡已經夠多了。」
我再次指著玩具,開始尖叫,還踢著腳。
「不行!」媽媽語氣強硬地回答:「別給我在這裡發飆!」
我不要積木,我只是想告訴她,這種玩具很危險。我要她跟店裡的人說,在下一個小孩中毒以前,趕緊把積木下架。可是我能做的只有尖叫,手指著玩具,雙腳亂踢。我繼續這樣做,而且愈來愈大聲。
媽媽快速將推車推出玩具部。「停下來!」她對我大吼。
我沒辦法停下來。沒辦法讓媽媽明白我的意思,令我十分懊惱。龍捲風發作了,我的手臂成了作戰工具,兩隻腳化為武器。我用腳踢她、不斷尖叫,一直指著積木的方向。
許多人打量著我們,有人指指點點,有人撇過頭去。
媽媽走到了店門口,把我從兒童座用力扯出來,她挑的東西全留在推車上。走到汽車那裡,她眼眶含著淚水,幫我扣上安全帶時,她幾乎對著我咆哮:「你發什麼癲啊?」
其實,她曉得這個問題的答案,也知道這不是我平常的舉止。我抽抽噎噎,用力吸著鼻子,逐漸平靜下來。只能期盼店裡的人看到那則新聞。
回到家,媽媽撥了電話給醫師,告訴他我脫序的行為。醫師開了鎮定劑給我,但媽媽沒讓我吃。危險期早已過去。
我不覺得後來媽媽有弄明白我那天想說的話。
1
文字。
我被好幾千個文字包圍。也許是好幾百萬個。
大教堂。美乃滋。紅石榴。
密西西比州。那不勒斯人。河馬。
像絲綢一樣柔軟。駭人的。如彩虹般燦爛。
搔癢。打噴嚏。盼望。擔憂。
一直以來,文字如同片片雪花繞著我打轉——每個字都優美精緻、與眾不同;每個字都完整地在我手中融化。
在我的內心深處,文字大片大片地漂流進來,不斷堆積。一層又一層的片語、句子、連貫的構想。機智慧黠的說法、玩笑、情歌。
從我還很小很小開始──說不定才幾個月大──文字就如同甜蜜的糖漿那樣送上來,我彷彿喝檸檬汁般地盡情暢飲,幾乎可...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