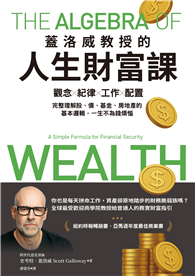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菲利浦.泰爾的圖書 |
 |
$ 314 ~ 558 | 歐洲1989:現代歐洲的關鍵時刻,從冷戰衝突到政治轉型,解讀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舊大陸與新秩序
作者:菲利浦.泰爾 / 譯者:王榮輝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9-10-31 語言:繁體/中文  共 1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作家蔡慶樺專文導讀
楊照(作家、Courant書系選書人)
伍碧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顯峰(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副教授)
洪德欽(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聯名推薦
想了解歐洲近代衝突的讀者,都應該看這本書。──萊比錫書展大獎評語
在他的這本「令人驚嘆的書」裡,作者以全歐洲的視角破天荒地對舊大陸上的新秩序,提出了一套全面性的歷史分析。他揭開了許多關於「一九八九」的神話,為新自由主義秩序做了第一次的總結。──《南德意志報》彥斯・比斯基(Jens Bisky)
一九八九年,是踏入近代歐洲新方向的轉捩點
▍兩德統一扭轉柏林,轉型成就德國新的政治生態。
▍蘇聯改革失利與嚴重的通貨膨脹,開始對下層人民實行更進一步的緊縮政策。
▍波蘭國會大選,終結歐洲共產主義,是東歐民主化的起點。
▍捷克發生反共產黨統治天鵝絨革命,朝向民主化國家發展。
▍烏克蘭人民運動成立,爭取改革運動。
本書作者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中歐歷史學院教授菲力普.特爾,根據親身經歷為讀者詳細地描述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歐洲歷史。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下時,一場遍及整個歐洲大陸的大規模實驗也跟著展開。在短短幾年中,前「東方集團」國家走向新自由主義的體制,政權也服膺於私有化與自由化。轉型造就了贏家與輸家。俄國落入一場經濟混亂,總統普丁趁勢建立了他的威權政權。諸如波蘭、捷克與烏克蘭等國則勵精圖治,如今更成為歐盟的成員國。有別於華沙與其他的首都發展成為新興都市,鄉村地區卻是日益貧困。
在本書中,他以敘事的方式,為讀者講述了這些轉變的細節和其中難忘的故事。他表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到來為東歐國家帶來了深遠影響,此外,經濟「休克療法」並非歐洲經濟增長的基礎,人力資本和基礎性的轉型才是經濟成功與失敗的決定性因素。與此同時,特爾還就西方的資本主義如何對東歐進行「重塑」、西歐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步伐和範圍,以及二○○八年後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東歐、西歐產生的不同影響等問題進行了闡述。
作者簡介
菲利浦・泰爾Philipp Ther
生於一九六七年,維也納大學東歐史研究所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約翰・甘迺迪紀念研究員、於佛羅倫斯的歐洲大學學院教授。其著作《現代歐洲的民族清洗》(Ethnische Säuberungen im modernen Europa)一書,曾在二〇一二年榮獲德國書業協會表揚,更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歐洲1989》(Die neue Ordnung auf dem alten Kontinent)則在二〇一五年獲頒萊比錫書展獎非小說類大獎、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年度政治類選書。
譯者簡介
王榮輝
曾就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大學歷史系與法律系;其後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Gottingen)攻讀碩士,主修哲學、西洋中古史與西洋近現代史。通曉英、德、法、日與拉丁文等外文。2009年起,擔任台北歌德學院特約翻譯。譯有:《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7-「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謊媒體──我們如何避免被操弄?」:有自覺使用媒體的第一步》、《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6-「宗教怎麼來的?為什麼人會相信看不見的神?」:寫給所有人的宗教入門書》、《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生活的藝術:52個打造美好人生的思考工具》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