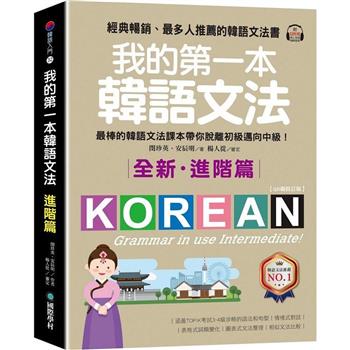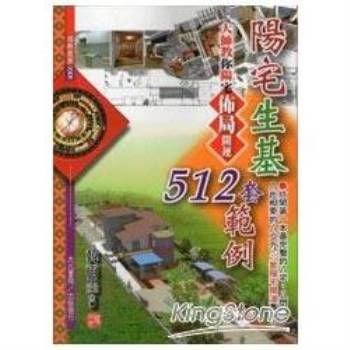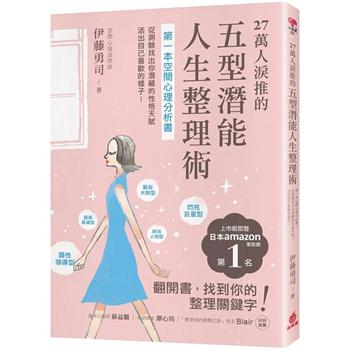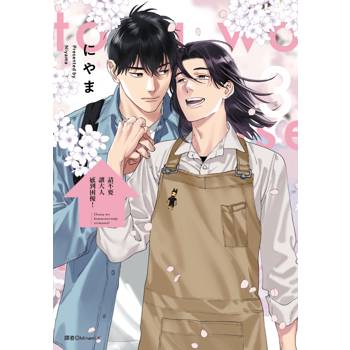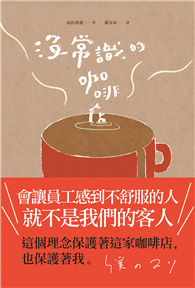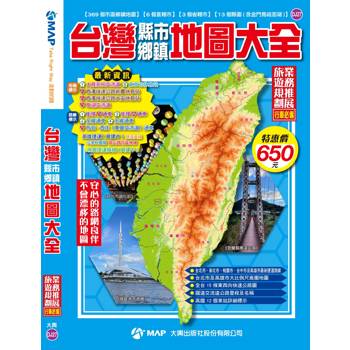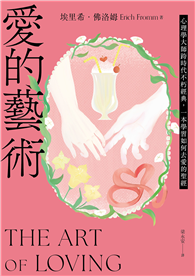菲力浦•拉金是蜚聲國際的英國詩人,其作品影響大、流傳廣,為一眾知名作家如德里克•沃爾科特、謝默思•希尼、克萊夫•詹姆斯等所稱道,許多詩人更是將其作品視為寫作靈感的來源。
《應邀之作:拉金隨筆》收錄拉金1955年至1982年間應報刊、雜誌等媒體約稿發表的五十餘篇隨筆、雜文、書評和樂評等,在其創作生涯中佔有重要地位,可以說濃縮了拉金一生的主要審美理想和藝術觀點。拉金文筆凝練,亦莊亦諧,許多文章雖篇幅不長,卻字字珠璣,向為歐美讀書界所推重。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菲力浦·拉金的圖書 |
 |
$ 512 | 應邀之作:拉金隨筆
作者:(英)菲力浦·拉金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12-01 語言:簡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20頁 / 32k/ 13 x 19 x 2.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拉金
拉金是烏克蘭的村落,位於該國西部沃倫州,由留波姆區負責管轄,面積0.98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90米,2001年人口21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22.45人。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應邀之作:拉金隨筆
內容簡介
目錄
前言
致謝
回 憶
《吉爾》序言•003
《向北之船》序•021
單槍匹馬,未經訓練•028
萊斯特的早年時光•036
弗農•沃特金斯:初次相逢與再次相逢•042
採訪錄
《觀察家報》採訪•053
《巴黎評論》訪談•070
002
尋常文字
聲明•109
愉悅原則•111
寫詩•116
書籍•119
補貼詩歌•123
1977年布克獎頒獎辭•133
被忽視的責任:當代文學作品手稿•141
特定之作
野蠻的七分之一•161
威尼斯狂歡節•172
獵逐•177
威斯坦怎麼了?•181
貝傑曼的融合•193
缺失的椅子•202
大師們的聲音•206
哈代夫人的回憶•217
威廉•巴恩斯的詩•228
膚淺與脆弱•235
戰爭詩人•246
新刮皮的土豆•254
懸賞:優秀的哈代評論者•261
哈代的詩歌•272
阿波羅的一份特質•275
維多利亞時代最典型的桂冠詩人•283
寒士村•293
受害尤深:艾米莉•狄金森與沃爾特•德拉•梅爾•297
帕爾格雷夫的終版文選:A.E.豪斯曼藏本•308
這種事只會發生在英國:為美國讀者分析約翰•貝傑曼的詩歌•319
鮑威爾先生的壁畫•346
極度精緻主義者•356
真正的威爾弗雷德•362
芭芭拉•皮姆的世界•381
安德魯•馬韋爾的變幻面容•389
難以言表的乏味感:弗洛倫絲與哈代•405
姑娘們•416
認識他感覺可真好•421
蝙蝠俠與飛鏢•425
非凡的格萊迪絲•435
遠處的車流•440
恐懼詩人•448
爵事鉤沉
《爵事鉤沉》序•459
稍等片刻•483
新聞報導•487
布魯斯盛典•489
規律法則•492
貝西•493
真相時刻•495
威爾斯還是吉本?•498
小眾趣味•502
人聲演唱•504
阿姆斯壯的成就•505
致謝
回 憶
《吉爾》序言•003
《向北之船》序•021
單槍匹馬,未經訓練•028
萊斯特的早年時光•036
弗農•沃特金斯:初次相逢與再次相逢•042
採訪錄
《觀察家報》採訪•053
《巴黎評論》訪談•070
002
尋常文字
聲明•109
愉悅原則•111
寫詩•116
書籍•119
補貼詩歌•123
1977年布克獎頒獎辭•133
被忽視的責任:當代文學作品手稿•141
特定之作
野蠻的七分之一•161
威尼斯狂歡節•172
獵逐•177
威斯坦怎麼了?•181
貝傑曼的融合•193
缺失的椅子•202
大師們的聲音•206
哈代夫人的回憶•217
威廉•巴恩斯的詩•228
膚淺與脆弱•235
戰爭詩人•246
新刮皮的土豆•254
懸賞:優秀的哈代評論者•261
哈代的詩歌•272
阿波羅的一份特質•275
維多利亞時代最典型的桂冠詩人•283
寒士村•293
受害尤深:艾米莉•狄金森與沃爾特•德拉•梅爾•297
帕爾格雷夫的終版文選:A.E.豪斯曼藏本•308
這種事只會發生在英國:為美國讀者分析約翰•貝傑曼的詩歌•319
鮑威爾先生的壁畫•346
極度精緻主義者•356
真正的威爾弗雷德•362
芭芭拉•皮姆的世界•381
安德魯•馬韋爾的變幻面容•389
難以言表的乏味感:弗洛倫絲與哈代•405
姑娘們•416
認識他感覺可真好•421
蝙蝠俠與飛鏢•425
非凡的格萊迪絲•435
遠處的車流•440
恐懼詩人•448
爵事鉤沉
《爵事鉤沉》序•459
稍等片刻•483
新聞報導•487
布魯斯盛典•489
規律法則•492
貝西•493
真相時刻•495
威爾斯還是吉本?•498
小眾趣味•502
人聲演唱•504
阿姆斯壯的成就•505
序
這本書裡收集的文章,除去一篇以外,其餘都是應邀而作的文字。當然,大多數都是些評論文章。因為一旦你成為知名作家,就會出現一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人們以為你從此就有能力評判其他的作家。不過,在我受邀完成的每篇稿件背後,往往還有其他幾份被拒絕的篇目。這樣做或是出於時間考慮,或是因為不感興趣,或是水準不足。當然,有人來約稿還是很榮幸的事,但終究要有個限度:報紙和雜誌欄目的空缺必須得填滿。如果你不想做還會有其他人。只有相當多產或境遇極其窘迫的人,才能夠包攬全部約稿,有求必應。
因此,這些再版的文章,幾乎沒有多少連貫性。我從不向任何編輯提議說,我應該寫這篇文章,或是要評價那本書。這樣一來,我的勞動成果其實是別人的想法所致,而不是源於我自己。這並不是說,我在完成這些任務時漫不經心。一個優秀的書評家會把學者的知識、批評家的判斷力和說服力,以及記者文章的可讀性結合到一起。當我感到自己跟這個理想標準的差距還有多遠時,只能更迫切地想要拼盡全力寫好。我聽人說,一個人如果在三年時間裡堅持給自己的導師撰寫每週讀書報告,就會發現文學新聞評論的工作比較容易:我並不這樣看。我發現這些書讀起來很費勁,想圍繞它們說點什麼也很費勁,最費勁的是想好以後再說出來。我最後能堅持下來,是因為幾位友善的文學編輯始終鼓勵有加,尤其是《衛報》的比爾·韋伯;先後任職於《旁觀者》雜誌、《新政治家》與《聆聽者》(當然,現在已經叫《倫敦書評》了)的卡爾·米勒;還有分別任職於《聆聽者》《新政治家》與《文匯》的安東尼·斯韋特。我很想記錄一下我對他們的感激,儘管當初我對他們表現出勉為其難的樣子。
我自己主動寫的那篇文章,是《爵事鉤沉》(All What Jazz, 1970)的序言。這部爵士唱片評論集是我在1960年至1968年間給《每日電訊報》寫的。我原本打算私人出版這本書。這也是當初我為什麼要找到現已倒閉的赫爾·普林特斯公司付印的原因。我的出版商一直等到我寫信詢問他們是否準備發行這本書的時候,才把它接手過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要在書裡使用那種輕快而挑釁的語氣以及我在寫作時的愉悅。其實我後來還在繼續寫唱片評論,直到1971年底。我在最近三年裡寫的幾篇也和這篇序言放到了一起。
儘管我在接到文學約稿時,難免總是心頭一沉,在完工時也難免產生一種非比尋常的釋懷感,但接受類似委託,無疑讓我心智的某個部分得到了鍛煉,否則它可能繼續處於休眠狀態。從這個方面看,它們對我很可能沒什麼壞處。重印這些文章,是因為其中有些內容已經開始被人斷章取義地引用,而我想要重申它們的表述語境,尤其是文字形成的日期。我希望,它們還會再傳遞一些其他內容。否則的話,我也沒理由非要像現在這樣翻屍盜骨。
除了一些零碎的文字修整,這些再版文章基本上是它們首次問世時的面貌。文章排列是按照出版日期的先後順序。“回憶”這一部分則是例外,它以主題思想出現的年代順序作為排列依據。
P. L.
1982年2月
因此,這些再版的文章,幾乎沒有多少連貫性。我從不向任何編輯提議說,我應該寫這篇文章,或是要評價那本書。這樣一來,我的勞動成果其實是別人的想法所致,而不是源於我自己。這並不是說,我在完成這些任務時漫不經心。一個優秀的書評家會把學者的知識、批評家的判斷力和說服力,以及記者文章的可讀性結合到一起。當我感到自己跟這個理想標準的差距還有多遠時,只能更迫切地想要拼盡全力寫好。我聽人說,一個人如果在三年時間裡堅持給自己的導師撰寫每週讀書報告,就會發現文學新聞評論的工作比較容易:我並不這樣看。我發現這些書讀起來很費勁,想圍繞它們說點什麼也很費勁,最費勁的是想好以後再說出來。我最後能堅持下來,是因為幾位友善的文學編輯始終鼓勵有加,尤其是《衛報》的比爾·韋伯;先後任職於《旁觀者》雜誌、《新政治家》與《聆聽者》(當然,現在已經叫《倫敦書評》了)的卡爾·米勒;還有分別任職於《聆聽者》《新政治家》與《文匯》的安東尼·斯韋特。我很想記錄一下我對他們的感激,儘管當初我對他們表現出勉為其難的樣子。
我自己主動寫的那篇文章,是《爵事鉤沉》(All What Jazz, 1970)的序言。這部爵士唱片評論集是我在1960年至1968年間給《每日電訊報》寫的。我原本打算私人出版這本書。這也是當初我為什麼要找到現已倒閉的赫爾·普林特斯公司付印的原因。我的出版商一直等到我寫信詢問他們是否準備發行這本書的時候,才把它接手過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要在書裡使用那種輕快而挑釁的語氣以及我在寫作時的愉悅。其實我後來還在繼續寫唱片評論,直到1971年底。我在最近三年裡寫的幾篇也和這篇序言放到了一起。
儘管我在接到文學約稿時,難免總是心頭一沉,在完工時也難免產生一種非比尋常的釋懷感,但接受類似委託,無疑讓我心智的某個部分得到了鍛煉,否則它可能繼續處於休眠狀態。從這個方面看,它們對我很可能沒什麼壞處。重印這些文章,是因為其中有些內容已經開始被人斷章取義地引用,而我想要重申它們的表述語境,尤其是文字形成的日期。我希望,它們還會再傳遞一些其他內容。否則的話,我也沒理由非要像現在這樣翻屍盜骨。
除了一些零碎的文字修整,這些再版文章基本上是它們首次問世時的面貌。文章排列是按照出版日期的先後順序。“回憶”這一部分則是例外,它以主題思想出現的年代順序作為排列依據。
P. L.
198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