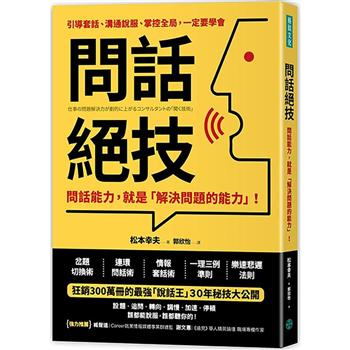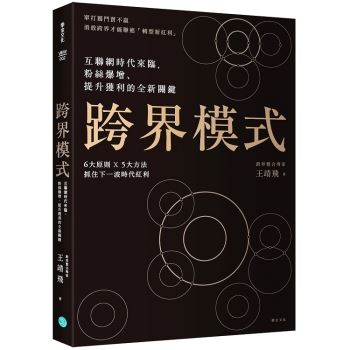被查禁長達六十年之久的科幻小說
開創反烏托邦文學,影響《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
完成後即被當局查禁……走私文稿到西方,旋即成為不可動搖的文學珍品……
【沒有了「我」,只有「我們」,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如果擺在人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沒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沒有幸福的自由,人們該怎麼辦?
●未來世界,每個人都只是號碼,沒有名字,綠牆裡面的編號們,住在透明的玻璃屋裡;任何東西都是分配的,甚至性生活也是用登記的,不允許愛情與自由生育。
【我們就像齒輪,同時起床、吃飯、散步、睡覺】
●「每天早晨,百萬個我們像齒輪機器一樣精準地在同一時刻醒來,又在同一時刻一致展開工作──並在同一時刻集體結束工作。」
●「在同一秒鐘,同時將湯匙舉到嘴邊;又在同一秒鐘,集體出門散步、走入禮堂、進入泰勒運動廳,又在同一時刻,一齊上床睡覺。」
【在我們看來,古代的社會多麼荒謬】
●「當時的國家(他們竟敢自詡為國家!)對人民的性生活毫不管束,這難道不是件荒謬的事嗎?只要人們想,隨時都能性交,想做幾次就做幾次……簡直跟動物一樣,完全不科學!」
●「最難以置信的是,當時的政府──他們不須按規定散步、沒有用餐時間的精準規定、可以隨意決定什麼時候起床、睡覺。」
●「或許古人那奇形怪狀又不透明的住所正是造成他們狹隘、可悲的心理成因。」
【我們將愛情數學化、組織化,嫉妒已不復存在】
●在這個未來世界裡,無須為了食物、生活、工作、愛情、子女煩惱,一切按照數字化的流程行動。
●且為了防止歷史上常帶來紛爭的愛情問題,誕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性法》:「任何編號皆享有將其他編號作為性產品使用的權利。」
●「愛情這項釀成古人無數愚蠢悲劇的根源,到了我們的時代,已經轉化為和諧、愉悅且有益的生物功能」
【靈魂是種病,這是個永遠完美的世界】
●人們就活在這個流水線般的社會裡。從出生到死,一舉一動都照著安排好的計畫行動。
●每個編號赤裸裸地活在這個數字化的世界裡,沒有靈魂。有了靈魂之後,反而被認為是生了病,得用手術去除。
●社會按照定好的流程走,永遠沒有一絲變化,這個僵化平穩、一切按照數字前進的人類社會,是我們所追求的完美世界嗎?
作者簡介:
葉夫根尼.薩米爾欽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884-1937)
俄國小說家、劇作家和諷刺作家,他的巨作《我們》(1924)是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奧威爾的《1984》並稱反烏托邦的文學三部曲。
1920年完成了《我們》的創作,內容被認為是針對蘇聯極權國家的政治諷刺,因而被當局查禁無法出版。1923年,薩米爾欽安排《我們》的手稿走私到紐約市。
1924年英譯本《我們》在國外出版,薩米爾欽與西方出版商的交易引起蘇聯政府大規模撻伐他。薩米爾欽在俄國被列入黑名單,因在俄國作家生命無望,1931年離開俄國移居巴黎,1937年因心臟病過世。
譯者簡介:
何瑄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喜愛文字與旅行,現為兼職譯者,著有童書《成語怪探:沒道理的A、B計畫》上下冊、譯有《外套與彼得堡故事:果戈里經典小說新譯》、《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選集II》等,另有散文專欄發表於天下雜誌換日線。
章節試閱
筆記三
摘要:
西裝.牆.時間表
我瀏覽一遍昨日的筆記──發現我寫得不夠清楚。
當然,對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來說,這一切都記錄得十分清楚明瞭。不過,誰知道「積分號」將來會把我的筆記運送到何人手上呢?或許,你們就如同我們的祖先一樣,偉大的文明之書僅讀到九百年前那一頁便戛然而止;或許就連這些基本常識,例如時間表、個人時間、母性標準、綠牆、至恩主等,你們都不知道。要解釋這所有的一切,我感到既可笑又無比困難,就好比一位二十世紀的作家,必須在自己的小說中逐一解釋何謂「西裝」、「公寓」、「妻子」這些詞語一樣。但如果他的小說要翻譯給原始人閱讀,怎麼能夠缺少關於「西裝」的詳細解釋呢?
我相信,目睹西裝的原始人內心會想:「嗯,這有什麼意義?只是累贅而已。」我認為,假如我告訴你們,自從兩百年戰爭結束以後,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跨出過綠牆,你們也會有如同原始人看到西裝時的相同感受。
然而,親愛的讀者,請多少發揮一點想像力,這對你們大有裨益。據我們所知,人類的歷史顯然是從游牧型態朝向定居社會發展。由此可見,現在(我們)的極致固定生活形式,不正是最完美的生活形態嗎?過往,人們輾轉從世界的一端遷移到另一端,這種情況只發生在國家、戰爭、貿易仍舊存在與發現新大陸的史前時代。如今,誰還需要這麼做?
我認為,人類這種定居習慣並非一蹴而成。兩百年戰爭期間,道路盡毀,荒草叢生──起初,人們居住在不同城市,相互為綠色荒野隔絕,生活想必十分不便。可是,那又如何?人類剛失去尾巴的時候,想必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學會如何不用尾巴驅趕蒼蠅。我敢說,早期的人類必然也困擾於沒有尾巴的生活。然而到了今天──你們能想像自己長了一條尾巴嗎?抑或是,你們能想像自己一絲不掛、赤身裸體地在街上行走嗎?(或許,你們仍舊穿著「西裝」出門也不一定)我們的情況亦然:我無法想像一座沒有綠牆遮蔽的城市,亦無法想像沒有時間表與精確數字的生活。
時間表……由金色底色與紫色數字組成,此刻正掛在我房間牆上,嚴肅又溫情脈脈地凝視著我。我不禁想起祖先們稱之為「聖像」的東西,內心浮現創作詩歌或祈禱文的念頭(兩者其實是同一件事)。啊,為何我不是詩人呢?如此便能恰如其分地歌頌時間表、歌頌聯眾國的心臟與脈搏。
我們所有人(你們可能也是如此),孩提時候都在學校讀過古代文學遺留下來的最偉大、動人的巨作──《鐵路時刻表》。不過,將它與時間表相比──你們會見識到石墨與鑽石的差別:儘管兩者皆由碳元素構成,但鑽石的光芒是何等永恆、澄澈與璀璨!有誰在匆匆翻閱《鐵路時刻表》時能不興奮得屏住呼吸?可時間表不同──它切切實實地將我們每一個人轉化為史詩巨作中的鋼鐵英雄。每天早晨,百萬個我們像齒輪機器一樣精準地在同一時刻醒來,又在同一時刻一致展開工作──並在同一時刻集體結束工作。我們如同百萬隻手被安裝在同一軀體,按時間表的指示,在同一秒鐘,同時將湯匙舉到嘴邊;又在同一秒鐘,集體出門散步、走入禮堂、進入泰勒運動廳,又在同一時刻,一齊上床睡覺。
我得坦言:即便是我們,也並未獲得關於幸福命題的絕對精準解答。一天兩次──從下午十六點到十七點,以及晚上二十一點到二十二點,我們強大的聯合機體會分解為無數個獨立細胞:這是時間表規定的個人時間。在這段時間,你們會看見一些人悄悄地放下房間窗簾;另一些人邁著整齊步伐,在大街上列隊漫步;或者像我一樣,端坐在書桌前。然而,我堅信:我們遲早會在大一統公式當中找到地方放入這些時段,總有一天,這八萬六千四百秒鐘皆會納入時間表中。
我曾聽過、讀過不少人類生活在自由狀態的年代(即無秩序的野蠻狀態)所發生的奇異故事。對我來說,最難以置信的是,當時的政府──哪怕是最原始的國家機關,竟能允許人們在缺少近似於我們的時間表的規範狀態下生活──他們不須按規定散步、沒有用餐時間的精準規定、可以隨意決定什麼時候起床、睡覺。一些歷史學家甚至指出,當時的街道徹夜敞亮,整晚都有行人車馬來來去去。
對此我實在無法理解。要知道,即便那個年代的人們智慧有限,可也應該意識到,儘管緩慢,這種生活實際上是日復一日的集體謀殺。國家(出於人道主義)禁止對個人處以死刑,卻對半數國民進行慢性謀殺。殺死一個人,意即將個體生命減少五十年,被視為一種罪行;可將人類的壽命集體縮減五千萬年,卻不構成犯罪。這不是很荒謬嗎?這種數學道德問題,我們隨便一個十歲的編號都能在半分鐘內解答。可那些人卻做不到這一點──他們所有的康德加在一起都辦不到。(因為他們的康德無一能夠領悟與建立科學倫理體系──一種以加減乘除為基礎的科學倫理體系)
此外,當時的國家(他們竟敢自詡為國家!)對人民的性生活毫不管束,這難道不是件荒謬的事嗎?只要人們想,隨時都能性交,想做幾次就做幾次……簡直跟動物一樣,完全不科學!他們甚至如動物般盲目地生育下一代。這不是很可笑嗎?他們通曉園藝、畜牧、漁業等知識(我們有明確的數據資料,證明他們完全掌握這些知識),卻未能踏上這道邏輯階梯的最後一級──生育學。(他們竟然沒能發現我們熟知的母性與父性標準)
這真是太可笑、太難以置信了,導致我在寫這段話時,暗自擔憂未來的不知名讀者會以為我是個愛說笑的惡劣傢伙,以為我故作正經地說些無稽之談,只為了嘲弄各位。
可是,首先,我並不擅長說笑──每個笑話當中都隱藏著謊言;其次,聯眾國的科學研究證實,古人的生活正如我先前所述,而聯眾國的科學絕不可能有誤。當古人如同一群猿猴、野獸般生活在自由狀態之下,又怎能發展出國家邏輯?甚至到了今天,我們當中還有些人不時聽見內心深處的遠古角落傳來猿猴時期的野性回音,我們又能要求古人做得多好呢?
所幸這種案例僅是偶爾發生,如同微小破損的零件,可以輕易修復,不會阻礙整部機器偉大、永恆的行進步伐。我們有至恩主熟練、強大的鐵腕以及保衛者明察秋毫的雙眼,清除這些變形的小螺絲釘……
對了,順帶一提,我想起昨天見到的那個身形如字母S上下佝僂的編號是誰了──我似乎曾在保衛部見過他出入。我現在理解,為何當時下意識地對他懷抱敬意,以及看到站在他身邊,脾氣古怪的I,我會感到困窘……我必須承認,對於I……
鐘響了,現在是睡覺時間:晚上二十二點三十分。明日繼續。
筆記三
摘要:
西裝.牆.時間表
我瀏覽一遍昨日的筆記──發現我寫得不夠清楚。
當然,對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來說,這一切都記錄得十分清楚明瞭。不過,誰知道「積分號」將來會把我的筆記運送到何人手上呢?或許,你們就如同我們的祖先一樣,偉大的文明之書僅讀到九百年前那一頁便戛然而止;或許就連這些基本常識,例如時間表、個人時間、母性標準、綠牆、至恩主等,你們都不知道。要解釋這所有的一切,我感到既可笑又無比困難,就好比一位二十世紀的作家,必須在自己的小說中逐一解釋何謂「西裝」、「公寓」、「妻子」這些詞語一...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薩米爾欽是一位俄羅斯小說家,代表作為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我們》。
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薩米爾欽是一位俄羅斯小說家,代表作為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