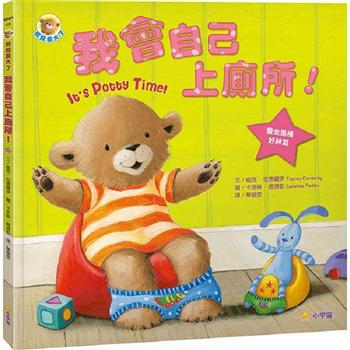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蓓特.安.莫斯可維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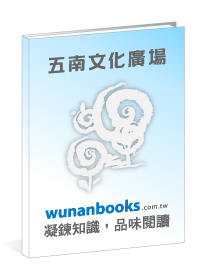 |
$ 190 ~ 211 | 我認識你嗎?一個生命老去的美麗故事-臉譜叢書FF1080
作者:蓓特.安.莫斯可維(Bette Ann Moskowitz) / 譯者:蘇瑩文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06-09-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0頁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認識妳嗎?:一個生命老去的美麗故事
◆榮獲紐約州基金獎(New York State Foundation Award)非小說類文學獎!
《我認識妳嗎》是個既美麗又痛楚的故事,說到了老去和存活,清晰的描述一個女人的精神如何滑落到老邁狀況。作者莫斯可維茲意圖去了解她母親衰老的過程──包括了孤獨、衰退、失去記憶和尊重,以及尿失禁,並檢視人到了老年期的這種極端境況下,生命到底是什麼。她想探索,在療養院這樣的地方中 “生命”的各種可能性,以及越來越長壽的社會應該要如何來對待這些增多的年歲。
莫斯可維茲道出了人們有朝一日終將提出的問題──你什麼時候會成為雙親的父母?一方面希望老人家能夠安全,一方面有希望能保有她的尊嚴和獨立,你要如何來取決?你希望自己如何老去?
作者簡介:
蓓特?安?莫斯可維茲BetteAnnMoskowitz蓓特?安?莫斯可維茲一生從未停筆。她事業起步於創作歌詞,並曾撰寫和出版過醫學資料、樂評及書評、詩作、個人隨筆,以及長短篇的小說。她的小說:LeavingBarney在一九八九年出版。《我認識妳嗎》是她第一本非小說創作。她的兩名子女已經成人,目前與丈夫同住在紐約北郊。
商品資料
- 作者: 蓓特.安.莫斯可維茲
- 出版社: 臉譜 出版日期:2006-09-07 ISBN/ISSN:9867058437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教育> 家庭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