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英譯者導言】
此處所翻譯的論釋,不尋常又稀有。即使在寧瑪派內,除了這部論釋的作者米龐仁波切的直接教法傳承外,鮮少為外人知。我們在祖古貝瑪望賈仁波切(Tulku Pema Wangyal Rinpoche)傳法期間,領受到這部論釋的口傳與闡釋。祖古貝瑪望賈仁波切從他的父親甘珠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領受到這個教法,而甘珠仁波切則從米龐仁波切最親近的弟子之一噶陀錫度卻吉嘉措(Kathok Situ Chkyi Gyatso)那裡領受這個教法。儘管這部論釋稀有罕見,但是其主題──蓮師七句祈請文,卻是藏傳佛教世界最廣為人知的祈願文。凡是蓮師受到崇敬之處,七句祈請文就會受到人們的珍愛和念誦,在佛教於西藏萌芽階段即興起的寧瑪派中尤其受到重視。這是針對蓮師所做的首要祈請文。蓮師被視為一切皈依的體現,所有證悟者的化身,以及藏傳佛教傳統所有後繼之大師和上師的典範。在寧瑪派中,沒有一座修法、沒有一種禪修、沒有一個儀軌,不是以念誦三次七句祈請文做為起始。而且如我們可以從這本論著的後記了解到,修行者投入數個月、甚至數年的時間來持誦七句祈請文,累積大量的持誦次數並不是一件非比尋常的事情。
對許多西方人士而言,即使對那些受到藏傳佛教吸引的人來說,蓮師似乎是一個不可思議、如謎一般難解的人物。根據紀錄,來自烏迪亞納(或許是位於現今巴基斯坦境內的一個地區)、身為密續佛教大師的蓮師,在西元第八世紀造訪西藏,因此幾乎沒有什麼重大的理由可以懷疑蓮師的史實性。然而關於蓮師的傳統文獻,其中包括數本未經刪節的傳記,充滿了我們平常會聯想成為傳說和神話的那種奇蹟。讓我們簡短地回顧蓮師重要的生平事蹟,以及他和西藏及西藏人民的關係。
蓮師
根據西藏編年史的記載,當西藏國王赤松德贊希望在他的國家奠定佛教教法的時候,他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是邀請偉大的比丘兼學者寂護大師入藏。寂護大師是規模宏大的那瀾陀佛學院的知名住持,在當時,那瀾陀佛學院是佛教國印度的榮耀。寂護大師抵達西藏後,努力教導國王及子民。他開始在桑耶興建寺廟,授戒第一批比丘,並且展開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然而,他的努力未達成功。他遭遇來自西藏貴族和皇室大臣的強大反對力量,這些人的心和興趣在於他們本土宗教的信仰和修行法門,而這個宗教即是西藏信仰鬼神的異教。儘管這些人具有強烈的敵意,然而寂護大師覺得,最大的反對力量完全不是來自人類,而是來自神本身。寂護大師這個外來阿闍黎的出現,打擾妨礙了西藏本地的神祇,他的教法將會廢除供養他們的血祭,破壞他們與西藏這片土地和人們的連結。這些神祇發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天災來展現他們的暴怒。寂護大師推斷,直接處理這些神祇,用魔法對抗魔法乃是唯一的解決之道。他坦承這種英勇之舉超過了他的能力範圍,於是建議國王尋求佛教密續大師、具有無礙力量的瑜伽士蓮花生大士的保護。
偉大的蓮師按時抵達西藏,並且應西藏國王之請,把西藏轉化成為一片佛土。如寂護大師所預測的,蓮師的首要任務是調伏眾神,以及頑強傲慢、統領天下的鬼靈。根據傳統的說法,當蓮師在西藏境內不同地方的許多場合對抗和擊敗這些鬼神時,並不是用摧毀或驅除的方法,而是用他的威嚴來壓倒他們,使其順從他的話語。據說,許多鬼神因而皈依蓮師。他們進入佛法之門,成為佛教徒。其他比較不肯順從的鬼神則受到蓮師瑜伽力量的制伏,誓言護持佛法。因此,在平息鬼靈世界之後,蓮師自由而無礙地傳播佛教教法,尤其是金剛乘的教法。據說,為了達到傳播教法的目的,蓮師徹徹底底地加持西藏整片國土,其徹底的程度沒有一個地方不曾被他的聖足碰觸過,沒有一塊土壤不充滿蓮師的加持。
這不是人們第一次試圖透過超自然的手段來改變西藏的宗教信仰。根據西藏文獻的記載,在蓮師應邀入藏的數個世紀前,西藏國王松贊干布曾經建造一整個寺院網絡,這些寺院都座落於風水要地之上,目的在於約束難以駕馭的國家;他把西藏想像成一個伸展手腳躺在地面上的巨大女體─仰躺的食人女妖。典籍告訴我們,這個方法發揮了一時之效,佛教教法開始傳佈生根。然而,這些散佈在西藏各地、用來「鎮伏國界」的寺院難以維繫。在松贊干布過世後,這些寺院荒廢失修,佛教修行也開始消失式微,並被舊日的陰影入侵取代。據說,蓮師為了防止他離開西藏、王朝瓦解之後可能發生的類似衰微,於是封藏伏藏教法,提供西藏未來的世代使用,而這些教法將由蓮師親近弟子的轉世取出。這些伏藏教法曾經是、也仍然是寧瑪派教法和修行的重要特徵,也是蓮師造訪西藏所留下最不可思議的遺產之一。伏藏教法也扮演保護密續修行法門所仰賴的口傳傳承的角色,並且一直是使教法一再重振復興的手段。
藉由蓮師改變西藏人與非人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藉由蓮師加持的力量,他把西藏和整個喜馬拉雅山區創造成為一片受保護的土地,使得經與續的研究與修行,能夠不間斷地興盛一千年。在佛陀的教法在其發源地消失之後,這些教法仍然在西藏和整個喜馬拉雅山區活躍達數世紀之久。在西藏歷史的不同階段,創建新學派和傳承的其他偉大上師,擴展並豐富了這個雖然經歷迫害和時間的流逝、卻仍然保持完整的傳統。這些大師即是在此既有傳統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學派和傳承。這些大師及其教法之所以能夠繁榮興盛,也要歸功於由咕嚕仁波切的加持所創造維護的環境。咕嚕仁波切和西藏命運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密切,因此當咕嚕仁波切為了保護西藏所設計的特殊儀軌受到忽視時(這是由於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過世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繼任之前的過渡期,派系不容的情況大為惡化之故),許多西藏人視其為大難臨頭的前兆。
當我們進一步閱讀咕嚕仁波切傳統的生平記述時,我們發現,儘管咕嚕仁波切在西藏和鄰近地區所展現的事蹟有多麼偉大勝妙,都難以道盡他的事業。根據傳統的記述和密續中的授記,咕嚕仁波切第一次在這個世界上顯現,是在釋迦牟尼佛滅入大般涅槃後不久,他以一個美麗孩童的身相顯現,坐在達那科夏湖內一朵莊嚴的蓮花上。他被當地國王因札菩提收養,在王宮中長大。成年時,他從阿難尊者那裡領受比丘戒。在後來的階段,他修持金剛乘的法門,尤其是大圓滿教法,並且達到「大遷虹身」的成就,他的人身轉化為光,永遠不死。等到他在西藏遇見赤松德贊和寂護大師時,按照人間的計算方式,他已經超過一千歲了。
他的事業也不侷限在這個世界。據說,他曾經造訪許多不同的世界體系,教導當地的眾生。在他長遠的生涯中,他根據眾生的需求,以許多不同的形相顯現,其中包括八大神變和無數小神變。最後,他在西藏完成任務後,前往羅剎居住的妙拂洲。根據古代印度的宇宙觀,妙拂洲是位於南瞻部洲西南方的一個附洲。南瞻部洲即是我們身處的世界,座落於宇宙中軸須彌山的南方。即使故事說到這裡,仍難以道盡蓮師的事蹟。蓮師永遠記得西藏這片土地,以及散佈世界各地、充滿信心的弟子。蓮師定期造訪他們,尤其是在陰曆初十和二十五日,乘著日出和日落的光芒從妙拂洲前來。
這個對咕嚕仁波切生平事蹟所做的簡短記述,原本應該是要詳加說明,而不該因為當代人對這個議題的敏感程度而有所讓步。在藏傳佛教的傳統中,一般人都相信關於咕嚕仁波切的生平。此外,對咕嚕仁波切的虔誠追隨者而言,不論是寧瑪巴或其他學派,他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一個來自過去、受人懷念的英雄。他是當下的真實,時時刻刻受到人們的喚請。人們毫不猶豫、自然而然地預期他會直接介入日常生活事務。當喇嘛傳授教法時,甚至於尋常人的對話中,都會提及咕嚕仁波切的生平事蹟。而他所展現的奇蹟,以及他顯現在聖哲和瑜伽士面前的種種,都彷彿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事實上,其中一些確實是最近才發生的。
對西方人士而言,面對這種活生生的傳統,可能會令人感到困惑費解。對我們而言,這些事件似乎是虛構的神話,因此,當我們和那些相信這些事件是真實的歷史描述的人互動時,我們會感到不安。藏傳佛教徒對咕嚕仁波切毫不保留的信心,對我們的思考方式是一種挑戰,因此,我們可能會採取各種不同的策略來適應這種可能會令人感到不自在的情況。舉例來說,我們也許會告訴自己,他的生平細節─他從蓮花中出生、他的不死和超凡的力量,並不是宗教教義。它們不是需要盲目地、毫不質疑地贊同的宗教信仰。當我們專注於更重要的佛法面向時,這些肯定可以被放在一旁。我們可以把咕嚕仁波切的生平記述視為一種象徵,他從蓮花中出生,只是一種以充滿詩意的方式來表達化身的教義;而他騎乘在光線之上,事實上是指妥噶修行法門的淨相等等。我們用這種簡化的論點來解釋被人們視為荒誕古怪、不可能是真實的事件和行為,然後將其重新公式化,使它們在智識上比較容易被人們接受。
到某個程度,這個程序是可理解的。然而,當我們把宗教的概念簡化到一個層次,只用我們目前對世界的了解來加以詮釋時,就會有風險。對那些把佛法當做心靈改革手段的人而言,用這種方式來稀釋、刪節教法,並非明智之舉。這樣的結果是,我們發現自己無動於衷,沒有改變,並且堅信唯物主義的想法,而佛法所扮演的角色正是要轉化這種唯物主義的想法。這種對咕嚕仁波切的描述,明顯地影響那些用開放的態度和信心接受它們的人,而我們卻讓自己對這種力量免疫。我們無法否認,所有過去偉大的瑜伽士和所有當今的偉大上師,都透過在一種世界觀內修行而獲致了證。在這種世界觀內,他們從不覺得有必要去質疑我們之前所描述的咕嚕仁波切的生平事蹟。這個事實應該讓我們停下來,或許讓我們不急著把咕嚕仁波切的生平事蹟視為民間傳說。這種簡化的問題在於,人們試圖對傳統的記述有更精密複雜的詮釋,但所得到的結果不是對佛法的意義有更深刻的內觀,反而是產生唯物主義的修行態度。
然而,這不是我們面對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和態度。我們或許需要行走在一條介於天真輕信和自以為是的懷疑論之間的窄索上;天真輕信和自以為是的懷疑論,都關閉了我們更深入了解佛法的大門。舉例來說,我們或許難以相信咕嚕仁波切抵達西藏時已經一千歲,或他仍然活在須彌山西南方的一個小島上。但是有一件事情似乎是肯定的:如果我們打從一開始就決定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就永遠無法了解任何事情。當我們面對神祕而不可思議的事物時,保持一種開放探索的態度,而非以所謂現代看待事物方式的名義加以排斥,會是比較有益的(肯定比較有趣)。
想克服我們因狹窄機械的宇宙觀,而不願意贊同難以理解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西藏傳統的直接覺受無疑是有幫助的。在藏傳佛教的世界中,凡俗存在的藩籬被衝破,奇蹟湧現的時刻確實會發生。即使現在,仍有文獻詳細記錄喇嘛們從岩石或湖中取出伏藏教法,或曾經造訪「隱密的土地」。即使在最近幾年,也有許多人親眼目睹一些瑜伽士在他們死亡的時刻展現虹身,他們的肉身融攝入光中,只留下毛髮和指甲。許多西方人士即使沒有親身體驗這樣的奇蹟,但是他們已經感受到一個偉大的上師對他們的覺知所帶來的影響。舉例來說,花時間親近甘珠仁波切,等於是進入任何奇蹟都可能發生的領域。
上師相應法和七句祈請文
在提到上師相應法(或上師瑜伽)或「與上師之本質雙運」的修行法門時,人們或許最能夠領會七句祈請文的重要性。雖然在佛教教法的所有層次都提及上師的重要性,尤其金剛乘更強調尋找和服事具格的上師,乃是成功實修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上師相應法的目的是在清淨和加深弟子和上師之間的關係,屬於前行法之一。當修行者進入密續修道更進階的層次時,上師相應法仍然保持其重要性;事實上,其重要性增加了。根據頂果欽哲仁波切所說的話,對上師生起虔敬心,把自己的心和上師的證悟心融合在一起,「對所有修行法門來說是最重要且最必要的,而它本身也是達致證悟最可靠、最迅速的方式。」但是,上師究竟是什麼?我們或許最容易從佛性的背景脈絡來了解上師這個重要人物的本質和重要性。
我們常常就積聚功德與智慧二資糧來說明心朝向證悟的進展。功德與智慧二資糧相對應於世俗和勝義兩種菩提心,這兩種菩提心則分別是慈悲與空性智慧的修行。據說,此二資糧會帶來成佛的「果」。然而如教法所強調的,我們應該了解,修道的究竟目標並不是合成的或最近製造出來的,也不是某件取得或養成的事物。或許我們說證悟是實現或發現某件已經存在於心中的事物,是比較正確的說法。
此某件事物,這個「元素」,即是所謂的「佛性」,是最祕密的心性,一直沒有受到迷妄、染污和輪迴痛苦的垢染。《寶性論》中舉出許多例子,說明佛性為什麼一直是隱藏的,長久被埋沒遺忘,甚至深藏在最迷妄、最惡毒的眾生心中。心朝向證悟的長久而漸進的過程,即是在去除障蔽。這些由業和煩惱所製造的障蔽,隱藏這內在的寶藏,如同一塊被埋藏在地底的精煉黃金一般,這個寶藏已經是圓滿無瑕,具足所有證悟的功德。佛性即心性,不會因為輪迴狀態而有所損壞,也不會因為證得涅槃而有所增益。
當我們思量發掘佛性的長久過程時,記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根據佛教的教法,外在世界和觀察這個外在世界的心,並非兩個完全獨立的領域,而是緊密相連的。簡言之,眾生所覺知的那種現象,極為仰賴眾生之心的內在條件。就某種程度而言,世界是「心造的」這句話是真實不虛的。隨著心的進化,隱藏佛性的染污障蔽透過生起正面的念頭和行為而減少,我們就會從外在世界覺察出改變,佛法的徵相因而開始顯現。
在早期階段,這或許只不過是短暫地注意到佛教教法的象徵物品,舉例來說,風馬旗、一張舍利佛塔的照片、一張引人注目的佛陀圖像、一篇耐人尋味、關於達賴喇嘛的新聞文章。漸漸地,我們對佛法的興趣變得更清晰,最後,我們將有機會遇見教法。我們將會和佛教的修行者及上師相遇,而且因為他們的緣故,我們將有可能進入修道,從事修行。所有這一切並不僅僅是機緣巧合。佛法在我們的外在世界出現,以及佛性從內在增長,或更確切地說,從內在開展,這兩者相互對應,如同回音一般。最後,在經過一段漫長的準備期之後(這個準備期可能會延伸數個生世),一位真正具格、具有圓滿了證和證悟善巧的上師,將會在弟子所處的環境中出現。弟子因為具有大量累積的正面心靈能量或功德而產生的靈修習性,而能夠覺知這樣一位上師的真正品質。之後,隨著障蔽被進一步地移除,上師的慈悲和加持,弟子清淨、真誠無偽的虔敬心將會相遇,並且這樣的時刻將會到來:上師能夠直接指出心的真實本質,弟子也能夠首次認識心的真實本質,也就是佛性。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中,佛性通常被稱為內在的上師或究竟的上師。如頂果欽哲仁波切所說的:
在究竟的(勝義的)層次上,上師即是我們自己的心性,其本身即是佛性,如來藏藉由外在或相對的(世俗的)上師和他的口訣教導,我們能夠為自己帶來內在的或究竟的上師的了證,而其本身即是明覺。
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弟子的覺知中,這樣一位真正上師的顯現,乃是弟子最終、最圓滿的佛性投射成為外在的覺受。這是一個漫長的、趨於會合過程的頂點,在這個過程最後,外在和內在的上師終於會合在一起。在這個時刻,弟子從內在認識心的本質,外在則體驗到一種任運的、非造作的信念,相信他或她的上師確實是佛。內在上師的面容被揭露,上師和弟子的心無別地融合在一起。在過去偉大修行者的生平事蹟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關於這種非凡事件的記述。
對寧瑪傳承而言,咕嚕仁波切是這樣一位上師的典型,一位能夠直接把弟子放在證悟狀態中的「完美上師」。事實上,他是我們自己的佛性。伊喜措嘉曾經說:「把上師觀修為你明覺的光芒。」毫無疑問的,這是咕嚕仁波切在這個世界顯現為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原因,完全超越凡人的限制。他內含所有自生智慧的證悟功德,即我們一直存在、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佛性。正如在伊喜措嘉的傳記中,咕嚕仁波切對西藏國王赤松德贊所宣布的:
從勝妙吉祥的蓮花田,
沒有處所或方向,無處可尋,
一個光球,
阿彌陀佛離於生死之金剛身、語、意,
降至一朵蓮花之上,
獨立自存,未經雕琢,
漂浮在廣大無際的汪洋,
從此有了我。
我無父、無母、無傳承,
我乃勝妙自生。
我從未出生,也將不會死亡。
我是證悟者,
我是蓮花生。
有一些人受到佛教教法的吸引,但是尚未遇見一位完全合格的上師。另外一些已經遇見具格上師的人,或許仍然需要昇華他們看待上師的方式,直到上師和弟子之間的關係變得如我們之前所描述的那般充滿意義。直到那個時刻降臨時,上師才會鼓勵弟子把咕嚕仁波切當做觀修之所依來修持上師相應法。這個技巧包含觀想咕嚕仁波切,迎請他前來,念誦祈願文和咒語,觀想自己領受他的加持,觀想自己的心和咕嚕仁波切的心融合在明晰、了無概念的明覺狀態中。
如果修行者在今生已經對自己的上師具有足夠的信心,那麼他們以自己的上師為修持上師相應法的對象,觀想上師平常的樣子,當然是可能的,而且非常有效。但是這種信心─完全沒有受到一絲一毫猶豫所染污的信心,是極為罕見的。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修行者被鼓勵去觀想自己的上師為咕嚕仁波切的身相,並且視上師和咕嚕仁波切是無別的。據說,藉由如此觀想,可以移除阻礙修行者把自己的上師真正覺知為佛(不同於僅僅相信上師為佛)的障蔽和疑慮。最後但絕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們要記住:上師相應法常常要求禪修者也要把自己觀想為一個尊貴的身相,舉例來說,觀想為伊喜措嘉,以金剛瑜伽女的身相顯現。這麼做的理由在於,上師相應法是一種圓滿的上師和圓滿的弟子相遇的禪修「預演」。如我們之前所描述的,在這個究竟的相遇中,修行者揭露和認識了佛性,也就是內在或究竟的上師。
當咕嚕仁波切在上師相應法中扮演核心角色時,我們就能夠輕易地領會七句祈請文的重要性;這是勝妙且充滿力量的迎請,總是能夠萬無一失的迎請咕嚕仁波切前來。七句祈請文不是一般的祈請文,而是如同咕嚕仁波切本身一般,從另一個領域顯現。正如同咕嚕仁波切不需要雙親的神奇自生,據說,七句祈請文也是在沒有作者的情況下任運顯現,是「不壞之究竟實相的本然共鳴」。空行母首先聽聞七句祈請文,並且加以善用。當需求生起之際,空行母們便把七句祈請文傳授給人類世界。
上師相應法(當此法以咕嚕仁波切為基礎時)和七句祈請文緊密相連。正如同上師相應法在金剛乘修道的每一個次第都保持其重要性,七句祈請文在上師相應法的所有層次都顯得意義重大。就外在層次而言,七句祈請文記錄了咕嚕仁波切的出生和起源地,慶祝了咕嚕仁波切的成就,並且懇請他賜予加持。就內在層次而言,七句祈請文的每一個文字都富含意義,提煉出整個金剛乘的精華。七句祈請文如同一顆美麗動人的多面寶石,吸收並集中了整個修道的光芒,然後反射出燦爛的光輝。
至於這本論著的起源,蔣貢米龐仁波切在後記中指出,有一個事件突然觸發七句祈請文的隱藏意義在他心中顯現。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是什麼事件引起它的突然顯現,但有趣的是,米龐仁波切所使用的語言暗示著這本論著本身不是尋常的撰述,而是一部伏藏教法,尤其是一部「心意伏藏」或「貢特」(gongter)。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本論著本身即是咕嚕仁波切所傳授的教法,很久以前被封藏在他的弟子的心意中,當適當的因緣具足時,這個教法注定重新顯現,不需要傳統的黃色紙卷或其他物質的支持。
我們無法否認這本精彩著作的優美與深奧。不論其起源的本質為何,它是以優雅和明晰的文字撰寫而成,而優雅與明晰是米龐仁波切所有著作的特徵。即便如此,對譯者而言,這是一本困難的書籍,主要是因為它包含了許多源自密續的引言,這些密續引言以精微難解的風格聞名。我們已經竭盡所能地保全這些引言的意義,並且盡可能地向博學多聞的專家請益。然而,儘管我們已經全力以赴,我們令人感到難為情的學識仍然無法捕捉一些法本的涵義;當然,我們也可能誤解了一些涵義而不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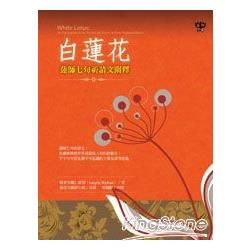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