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光水色映雲霞 閱讀《金秋進行曲》
方明
歷代歸隱鄉間曠野、隔絕紅塵世事,在林木蘢蔥、溪水涓涓的莽莽重山之間靜渡餘生而行雲吟哦的詩人,我們將之歸類為《山水詩人》或《田園詩人》,其實兩者之間亦有主題表達的差别,但文體上的分類似乎沒有如斯嚴謹。相信讀者對中國著名的田園山水詩人,諸如王維、陶淵明、謝靈運、孟浩然等留下之山川靈水,優逸如渾樸自然之潑墨詩篇十分熟稔,但有關田園山水之散文或雜記,則鮮有成書成冊,或偶爾詩人們在行吟之餘,提補一、二篇章,翻閱明裕先生的散文集《金秋進行曲》,竟被數拾篇一折青山一灣碧翠的田園山水的報導秉文所驚艷,台灣綠野澗壑似夢還真的自然扇屏,而作者將自已親人被鎖住在千嶂雲霞的谷地裡,在此汗珠涔涔躬耕之入世隨和的苦樂態度,描述得淋漓盡致。
此本散文內容有不少講述作者長輩如何在貧困忒惡的環境中,為五斗米而朝夕躬稼,而周遭卻有< 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 >之爽悅農景,故賞閱《金秋進行曲》時,在敬佩上一代長輩披荊斬棘吃苦耐勞之精神,又可沉浸於作者妙筆細膩道出<山花高下色>、<春鳥短長聲>、<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之詩境,鄉間百姓在物質窮匱之下,仍可樂天知命、隨遇而安之簡樸、爽直、開朗之美德,令生活在都市叢林裡滿身交織著爭鬥貪鄙幽明以及糾葛著各種名利腐惡城市人反省思考。
閱讀到能以鄉村為題材而寫下數拾篇田園生活即景的秉文,明裕先生應是先例,《金秋進行曲》散文集幾乎是述台灣鄉野習俗、村民作息起居集大成的冊子,將<鄉下人>生活在物質窮匱的環境下,仍然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充分表現簡樸、爽直、開朗之美德,此書亦是探究台灣百姓克勤克儉、互助互愛的紙上活電影之溫馨投影。
全書插入<李商隱與朱淑真>的愛戀詞作為潤滑劑,真是人間花草皆有情,< 一樹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屬何人>相互映照。 2024 年 7月 完稿
自序 蔡明裕
幾十年前我開始寫作時,那時我已離開,以農業為主的故鄉幾年,而大多寫故鄉,純撲的景象與故事,我和那時文壇盛行的鄉土文學,稍微有一點關聯。
我也喜愛讀一些作家寫的鄉土文學作品,讓我能深入的了解,鄉土文學的涵意和流行背景,也增加了我寫作的動機。
後來遇到金門來的楊樹清、顏國民等幾位作家,他們都比我早寫作幾年,而且有人已準備出書的打算,他們邀我參加寫作小組,總共大約有五、六位,就這樣每周聚會一次,也提出這一周各人寫的作品,互相討論優缺點,以增進大家的寫作能力。
大家討論過比較好的作品,就投稿出去,那時報章雜誌很多都有投稿的園地,大部分都有刊登出來,也鼓舞了大家寫作的信心。
那時的寫作小組成員,後來大多有出書,甚至有的人,到現在已出書幾十本,而目前的我,在名作家方明兄的鼓勵下,才要出第一本書,我想在現代網路發達時代的電子書,除非名作家,紙本書市場已經沒落,出書我認為只是一種結集的意義而已。
跋 楊樹清(報導文學家,燕南書院院長)
點唱蔡明裕的《金秋進行曲》
一年前,原本要為蔡明裕的《金秋進行曲》作序;一年後,寫序人變作題跋者。
時空會場叫醒王樂仔仙
「大俠:蔡明裕的『提拔』完成了沒,可以在這個禮拜交嗎?」老友出版人顏公~顏國民加入催稿行列。我的思緒,迅即飛回十七年前,再遇蔡明裕的一場新書發表會。
「叫醒榮格/叫醒梁啟超/叫醒胡適/叫醒傅柯/叫醒坎伯/叫醒張愛玲/叫醒弘一法師/叫醒雷震/叫醒賴和/叫醒莫札特/叫醒羅門/叫醒管管/叫醒李炷烽」……,一個周末的午後,許水富在台北時空藝術會場的《多邊形體溫》個展暨新書發表會,詩人管管、顏艾琳朗誦那首〈叫醒靈魂〉的詩,從照本宣科到隨興點唱在場的人,連渡海而來的金門縣長李炷烽也在被「叫醒」之列,逗得眾人哈哈大笑,原來詩也可以用「叫」的!「叫醒王樂仔仙!」場邊,看到一道消逝多年又現身的熟悉身影,我跟著加入「叫醒」的隊伍。
這是一場號稱「詩.書.畫裝置展」、一本「視覺構成混合多媒體的感覺作品」或者「詩,散文與手抄字的眾生」,許水富以「所有破壞和改變都是為了建一座紀念碑」自況,詩人白靈形喻許水富的創作表現接近「詩癲」:「『燦爛濾過孤獨症候群』成了許水富無可救藥的病症,和勳章」。是啊,「病」!隨後,老詩人菩提以丹田之力唸起了那首〈病〉:「一口口吞噬/身體一個洞一個洞的痛/小小細菌侵略臉龐/長不出翠綠的笑容/荒蕪胸丘沈默預告/死亡昨天剛過去」…。
擔綱主持這麼一場集合著同鄉、同學、詩人、作家、畫家,甚至連中國一級音樂家章紹同都到場的「複合式」作品、「複合式」觀眾的發表會,我的心情一點也不輕鬆。我還得擔心許水富的身體狀況,怕他在擠滿人潮的密閉空間又暈眩症發作,有兩次與他在羅門、蓉子的「燈屋」,看到他「缺氧」般地衝出幽暗往屋外透氣,一次他在地下道天旋地轉地連忙到台大急診處吊點滴;我也得目光鎖住在座的兩位大詩人L和G,上回兩人一言不合,G拿著酒瓶正要砸向L,幸好許水富起身及時制止了「災難」的發生;還有,寫《殺夫》的李昂也來了,許水富搞笑發出「今天是『殺夫』的好天氣,李昂在百忙中還能趕來」,凝結「多邊形體溫」的《多邊形體溫》,笑聲與黑色幽默沖淡了所有的病容與焦慮狀態,換來一席「醇酒五甕/詩句一鍋/燭火六盞/散文半碗/茶點四盤/書畫三卷」,既熱鬧又溫馨的文學饗宴。
我們離不開台北的理由
離不開台北的理由──就在於處處有著文化刺激,要怎麼「發癲」、如何「搞怪」,隨你;這座城市也隱藏著「遇見」的驚喜,你不知何時會遇到一位詩人、撞見一位畫家,或者碰到一位同鄉、一位老友……,譬如,這次許水富《多邊形體溫》展場,有人驚呼長年一襲長袍一頂呢帽的周夢蝶,有人擁抱「讓我把春水叫寒」寫《秋蟬》的李子恆,牧羊女遇到了青春年華時的文友陳亞馨,金門縣長李炷烽也「遇見」他童年時在湖下村駐紮的詩人菩提,還提示在《金門日報.浯江夜話》讀到楊清國寫當年菩提在湖下種種。
建築在台北大城的時空藝術會場,時間與空間,藝術與文學交會,「時空」的命名,我喜歡。我靜靜地欣賞著許水富的作品,也觀看著眾人在此交遇、交集時所發出的氣味、聲響。忽然,有人拍打著我的肩膀,「王樂仔仙!」我幾乎是驚愕地回神。
不高的個兒、稚氣未脫的娃娃臉、蓬鬆的頭髮、簡單的衣著,我見到的這個人,畫面是與二十多年前立即聯結的。他怎麼會出現在此時此地此一場合?我不是說他不該出現──而是,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們應該在許多文藝場子相見的,即便走在台北的大街小巷,也都該有遭遇的時刻。我與他相識在一九八○的耕莘寫作會,一九八四年間我與顏國民(顏凡)、黃曉茵在唐山樂集組織了個「唐山勤寫小組」,讀書會形式,每周一晚間筆會一次,讀書、交換寫作心得,風雨無阻持續兩年餘,他幾乎是每會必到,有回提交一篇小小說〈王樂仔仙〉,寫活了一位江湖賣藝的人物,從此,我們幾忘了他的姓名,直呼「王樂仔仙」。
冒冒失失闖入迷宮城市
蔡明裕來自雲林鄉下,那個叫「土庫」的地方。少年北上討活,在三重一家車床工廠當「黑手」,後來又轉到一所學校當職員。
這個人與他身處的環境、時空,總會讓我想起小說家黃凡〈賴索〉裡的一段形容「賴索就這樣冒冒失失的闖入這棟迷宮似的建築。這是個現代科技融合了夢幻、現實、藝術、美、虛偽、誇大的綜合體。他從一個攝影棚到另一個攝影棚,從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時代。」
原本要留在鄉下種田的,卻來到了五光十色的夢幻之都,蔡明裕是不是誤入都會叢林?「阿草、阿草」鄉土味十足的外表、臉上永遠掛著一抹憨笑,木訥、拙於言辭的他,是讓人看一眼就看出不具攻擊性、不會防衛性的莊稼人;沈沈緩緩的步履,行走在快節奏的都會,他就像一面選錯顏色、貼錯瓷磚的壁牆。
以冷眼熱筆觀看眾生相
說蔡明裕不屬於這座城市、不協調於這群人,他卻有一隻「奇異筆」,這隻筆的世界始終停格在他鄉土活動時期的人與人性,淡淡的筆觸但有冷冷的、細緻的人性解剖,我在剪貼簿裡找到他一篇發表於一九八四年的〈耗子〉:「鄰居的阿比伯經營碾米廠,每當在穀倉捉到老鼠的時候,都會生氣的想盡辦法折磨牠到慘死為止,有一次我看到阿比伯拿著一瓶汽油淋著鐵絲籠裡一隻肥大的老鼠,就好奇的站在那裡觀賞。一直到那隻老鼠一身抖索的蹲在角落時,阿比伯才劃了一根火柴往鼠身上丟去,『嘩』一聲,滿身著火的老鼠一霎那在鐵絲籠裡來回狂命奔跳,阿比伯高興的把汽油繼續淋了下去,那隻老鼠才不停的發出『吱吱』的慘叫聲,阿比伯興奮的叫著:該死的鼠輩!」
文字與畫面同時呼出、怵目驚心的人鼠大戰,蔡明裕那枝筆確有個令人驚奇的人性角落;《金秋進行曲》中,我又撞見一隻老鼠,寄身在〈土角厝〉中,但這一回不再是主角,而是當配角,不那麼濃重地哀嚎了,而是多了淡淡的喜感,「住了幾十年的土角厝,也逐漸老舊了,晚上會聽到土角壁的大竹管裡傳出蛀蟲的陣陣鳴叫聲,父親怕土角壁的大竹管會很快從裡面腐蝕到外面,嚴重的話土角壁的大竹管會斷裂,土角壁就會崩塌,土角厝就危險了,父親不得已就在土角壁的大竹管鑽一個小孔,把買來的殺蟲劑倒進去滅蛀蟲,第二晚就沒蛀蟲鳴叫聲了。老鼠也出現了!母親只好去鄰居要一隻貓回家養,貓抓老鼠是天性,一物尅一物,貓也使家人帶來一些歡樂,能陪小孩子玩球、或互相抱著玩、牠軟綿綿的身體抱著睡覺也很溫暖;土角厝也會漏雨了,雨下久一點,母親就要忙著用臉盆、碗公、水桶等接那些滴入厝內的雨水,最後父親決定爬到厝頂察看幾片屋瓦損壞,再去郊外的磚窯廠買一些新屋瓦回來更換。」
蔡明裕從以前到現在,從爬格子到敲鍵盤,從散文到作詞,一直都是勤奮的筆耕者。我也看好他應能在文壇獨樹一幟。他卻一度莫名地消失在文字、文人世界,我有整整20年不曾遇見他、失落他的音訊,逛書店時也不曾發現過他的著作。偶爾想起,這人不會是從人間蒸發了吧?
「我是從《幼獅文藝》的一則花邊看到你會來主持這場新書發表會,我是來看你的,我退休也結了──四十六歲才結婚,還在努力『做人』,我也到過你們金門了,SARS期間才花了三千多塊廉價走了一趟,還買了一條根。哈!」重逢的時刻,蔡明裕就說了這些,然後,掏了四百塊買了本許水富的《多邊形體溫》,跟我們一道到「稻香村」喝幾杯高粱;然後,這人又一次消失在我的視界……。
用筆刻畫鄉土是他強項
台北時空再遇見那個人那枝筆後,又隔了一個十五載。蔡明裕寄來一本書稿,《金秋進行曲》,終於要出書成類了。他在自序中述及「幾十年前我開始寫作時,那時我已離開,以農業為主的故鄉幾年,而大多寫故鄉,純撲的景象與故事,我和那時文壇盛行的鄉土文學,稍微有一點關聯」。
一九八七,龔鵬程序楊樹清的散文集《渡》,論及「鄉土文學興起後的散文,常是對都市生活後的逃避和悔懺,描述原本歆羨都市,北上求發展的嘉南高屏地區的青年,追戀故鄉之純樸與貧困,又不能且不願真正歸去。這些散文裡,往往會交揉著一些社會寫實的精神和浪漫的農村緬懷,人物與語彙亦大體自成一類型。相較之下,台東花蓮的青年作家、金馬澎湖的作者們,便還没有發展出一個類。在這幾十年的大變動中,在這與台灣本島,特別是西部北區都會生活的接觸中,我們感覺金馬澎湖的音太微弱了。雖然它們在歴史和現實上都那麼重要。」
依此觀看蔡明裕,刻畫寫鄉土是他的強項,描繪童年、親情亦獨特,雖離文字的精練,文學的純粹,還有一段距離,但至少達致「真摯動人」丶「寧拙無巧」丶「自然流暢」的基調。文章要在純樸拉出情感的深度丶文字的溫度,真是不容易 。明裕努力作到了。
散文作者如今也化身作詞人。某日在KTV,友人點唱台語歌手高向鵬的《我的心真痛︾,字幕秀出「作詞/蔡明裕」,我眼睛一亮,跟著哼唱,「愛情的劇本是你甲治寫/角色安排隨時替換/這齣戲結果嘛知影/緣份變卦我輸你佔贏/我的心真痛痛痛痛/對日出到深夜/我的心真痛等等等/等你來靠岸/也是對你依依難捨/望你回頭叫阮的名/啊嘸是世間痴情的人註定受拖磨/是我愛你勝過我生命」。
「我的心真痛。歌詞寫得極好,有痛的感覺」。來賓掌聲鼓勵!終曲之後,我忍不住傳了通信息給蔡明裕。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古人以五行之一的金與秋季相配,故稱「金秋時節」。蔡明裕筆耕田畝半世紀,終於有了《金秋進行曲》散文初集,以文字奏出一個滿目金黃的豐收季節。《我的心真痛》之後,讓我們再點唱一首《金秋進行曲》。
序不成,是為題跋的人。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蔡明裕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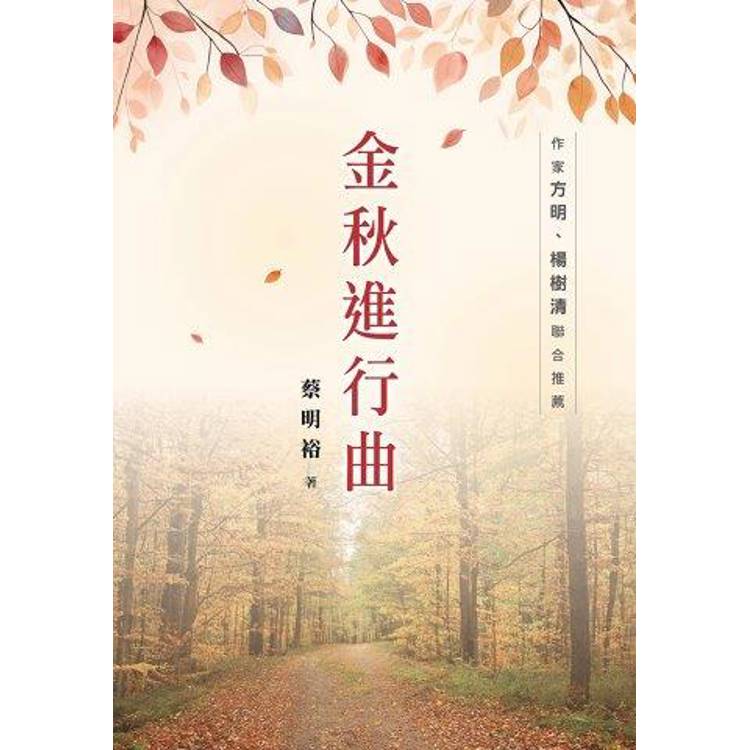 |
$ 264 ~ 270 | 金秋進行曲【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蔡明裕 出版社:大元書局 出版日期:2024-12-04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蔡明
蔡明,女,北京人,回族。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中國著名演員。小學時扮演電影《海霞》中的小海霞而成名,之後蔡明多次在春節聯歡晚會等節目中亮相,成為了中國大陸家喻戶曉的影視、小品演員。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金秋進行曲
翻閱明裕先生的散文集《金秋進行曲》,竟被數拾篇一折青山一灣碧翠的田園山水的報導秉文所驚艷,台灣綠野澗壑似夢還真的自然扇屏,而作者將自已親人被鎖住在千嶂雲霞的谷地裡,在此汗珠涔涔躬耕之入世隨和的苦樂態度,描述得淋漓盡致。
此本散文內容有不少講述作者長輩如何在貧困忒惡的環境中,為五斗米而朝夕躬稼,而周遭卻有< 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 >之爽悅農景,故賞閱《金秋進行曲》時,在敬佩上一代長輩披荊斬棘吃苦耐勞之精神,又可沉浸於作者妙筆細膩道出<山花高下色>、<春鳥短長聲>、<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之詩境,鄉間百姓在物質窮匱之下,仍可樂天知命、隨遇而安之簡樸、爽直、開朗之美德,令生活在都市叢林裡滿身交織著爭鬥貪鄙幽明以及糾葛著各種名利腐惡城市人反省思考。
作家方明推薦:閱讀到能以鄉村為題材而寫下數拾篇田園生活即景的秉文,明裕先生應是先例,《金秋進行曲》散文集幾乎是述台灣鄉野習俗、村民作息起居集大成的冊子,將<鄉下人>生活在物質窮匱的環境下,仍然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充分表現簡樸、爽直、開朗之美德,此書亦是探究台灣百姓克勤克儉、互助互愛的紙上活電影之溫馨投影。 方明推薦
作家楊樹清推薦:蔡明裕有一隻「奇異筆」,這隻筆的世界始終停格在他鄉土活動時期的人與人性,淡淡的筆觸但有冷冷的、細緻的人性解剖。
作者簡介:
蔡明裕,一九五五年生,雲林人,大學畢,喜愛山與海、鄉野,得過鹽分地帶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三三集刊曾刊出小說與散文,大華晚報新作家介紹。
章節試閱
山光水色映雲霞 閱讀《金秋進行曲》
方明
歷代歸隱鄉間曠野、隔絕紅塵世事,在林木蘢蔥、溪水涓涓的莽莽重山之間靜渡餘生而行雲吟哦的詩人,我們將之歸類為《山水詩人》或《田園詩人》,其實兩者之間亦有主題表達的差别,但文體上的分類似乎沒有如斯嚴謹。相信讀者對中國著名的田園山水詩人,諸如王維、陶淵明、謝靈運、孟浩然等留下之山川靈水,優逸如渾樸自然之潑墨詩篇十分熟稔,但有關田園山水之散文或雜記,則鮮有成書成冊,或偶爾詩人們在行吟之餘,提補一、二篇章,翻閱明裕先生的散文集《金秋進行曲》,竟被數拾篇一折青山一灣...
方明
歷代歸隱鄉間曠野、隔絕紅塵世事,在林木蘢蔥、溪水涓涓的莽莽重山之間靜渡餘生而行雲吟哦的詩人,我們將之歸類為《山水詩人》或《田園詩人》,其實兩者之間亦有主題表達的差别,但文體上的分類似乎沒有如斯嚴謹。相信讀者對中國著名的田園山水詩人,諸如王維、陶淵明、謝靈運、孟浩然等留下之山川靈水,優逸如渾樸自然之潑墨詩篇十分熟稔,但有關田園山水之散文或雜記,則鮮有成書成冊,或偶爾詩人們在行吟之餘,提補一、二篇章,翻閱明裕先生的散文集《金秋進行曲》,竟被數拾篇一折青山一灣...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方明 ) 1
自序 (蔡明裕) 3
土角厝/ 百千層樹花 白水木/ 用心/ 燈仔花伴童年/ 手搖發電機/ 火柴盒/ 稻子收成時/ 藝術家的精神/ 忍冬/ 種田的辛勞 /木棉花 /東澳冷泉 /三合院的感想/ 筒仔米糕的感想/ 大圳 /杏仁茶和油條/ 五分車的回憶/ 揹巾/ 蘿蔔糕/ 牛墟/ 出海口的感想 /牽牛花的季節 /南山/在故鄉的五分車/海邊的流戀/耕作/堅強 /強壯 /異地見聞錄/ 粽葉飄香時/ 愉悅的休閒 /上山 /蘭陽溪/ 山坡上的芒草 /收舊貨的人 /冬天的林景 /太武山美景 /貢糖與落花生 /金門的勝景 /斗 笠 /在台北博...
自序 (蔡明裕) 3
土角厝/ 百千層樹花 白水木/ 用心/ 燈仔花伴童年/ 手搖發電機/ 火柴盒/ 稻子收成時/ 藝術家的精神/ 忍冬/ 種田的辛勞 /木棉花 /東澳冷泉 /三合院的感想/ 筒仔米糕的感想/ 大圳 /杏仁茶和油條/ 五分車的回憶/ 揹巾/ 蘿蔔糕/ 牛墟/ 出海口的感想 /牽牛花的季節 /南山/在故鄉的五分車/海邊的流戀/耕作/堅強 /強壯 /異地見聞錄/ 粽葉飄香時/ 愉悅的休閒 /上山 /蘭陽溪/ 山坡上的芒草 /收舊貨的人 /冬天的林景 /太武山美景 /貢糖與落花生 /金門的勝景 /斗 笠 /在台北博...
顯示全部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