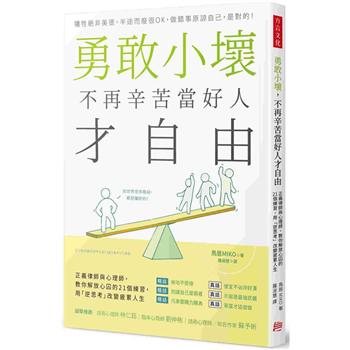蕭煌奇,台灣新北市板橋區人,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畢業,是一名視障人士,同時是一位傑出的華語流行音樂創作歌手和柔道運動員。1995年起擔任全視障樂團全方位樂團團長、主唱、薩克斯風手,亦會演奏吉他和爵士鼓,經常受邀至世界各地演出。1999年,蕭煌奇獲得了台灣十大傑出青年獎。2016年,蕭煌奇在台北小巨蛋舉辦了神秘世界演唱會,成為史上首位攻蛋的盲人歌手。2018年拿下第4座金曲最佳台語男歌手獎。
在2002年12月推出第一張創作專輯《你是我的眼》與2004年12月推出第二張創作專輯《黑色吉他》,蕭煌奇包辦了大部分的詞曲創作,也是台灣少數主打國台語雙聲帶市場成功的創作型男歌手,其國語歌曲《你是我的眼》在2007年5月被林宥嘉在第一屆《超級星光大道》翻唱,奪下25分滿分,更讓原唱蕭煌奇爆紅。蕭煌奇至今仍非常感謝林宥嘉:「真的很誇張,自從宥嘉唱了這首歌,而且拿下高分後,不斷有活動邀約找上門,希望能請到原唱表演。每周都無法休息地跑活動,有時一天還連跑二、三場」,這個翻唱讓他的音樂創作被更多人看見和傳唱,也讓他有更充裕的資源擴充團隊。而台語歌曲《阿嬤的話》在2007年8月被賴銘偉在第二屆《超級星光大道》翻唱,引起廣泛討論,之後歌曲更是風靡全台。因為小時候學聲樂時候有學義大利語,所以可以傳唱三大男高音名曲。曾在台灣寶特公司工作。
由於罹患先天性白內障讓蕭煌奇一出生就失明,直到4歲那年動手術而變成弱視,雖然看不遠,但是還有些許視力。到了他15歲那年,跟朋友打電動造成後天青光眼視神經萎縮,再度失明。他形容:「別人睜開眼看到的是全世界;我只看得到整片的白,就算睡著了,眼前還是一片白」。2015年,蕭煌奇參加《我是歌手》,成為最後一位補位歌手。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名稱:我看見音符的顏色-盲眼歌手蕭煌奇的故事
第一位獲選『十大傑出青年』的盲人歌手,
勇敢唱出最動人的生命樂章!
丘秀芷.陳昇.廖正豪◎誠摯推薦
繼《乞丐囝仔》後,最感人的生命故事!
『對大部分的朋友來說,煌奇當然不只是一個朋友,他更像是一種啟示,一種……跌倒了要自己爬起來的啟示。一種生命是曼妙芬芳沒有權利抱怨的啟示。如果你覺得他只是一個唱歌的人,那就太浪費了!』~~陳 昇
『看不見』,一定是盲人生命中的缺憾?
對蕭煌奇而言,卻是人生轉變的契機!
他出生時全盲,四歲時動手術成為弱視後才見到光亮。雖然無法看得太遠,天生樂觀的他卻又學柔道、又玩音樂,眼中的世界無比遼闊!
十五歲那年,上天卻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因用眼過度而永遠失去了視力。在重見光明多年之後再度失去光明,是多麼殘酷的折磨!他覺得自己被世界所拋棄,悔恨、痛苦、恐懼……種種情緒交織成一張大網,而他,則深陷其中。
就在這個時候,最愛的『音樂』成了他最大的支柱,幫助他走出黑暗的角落。他決心不要向命運低頭,因為盲人除了看不見之外,一樣有權利、也有能力實現夢想──他要讓更多的人聽到自己創作的音樂!
於是,音樂開啟了一扇窗,讓他重新找到失去的光明!歌聲詮釋了心情,讓世人聽見他無懼黑暗的勇氣!當指尖在琴弦上輕輕撥動,他比常人更看清了自己的道路,而生命的樂章也已燦然溢出繽紛的顏色!
作者簡介:
蕭煌奇
E世代的盲眼歌手,1976年生。他除了詞曲創作、演唱外,也是一位柔道高手,曾多次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柔道比賽。
他出生時因先天性白內障而全盲;四歲動了眼部手術後成為弱視;高一時因用眼過度而終於永遠失去了視力。但是這位熱愛生命的大男孩並不因此而自暴自棄,高中畢業前,他組成了台灣第一個視障音樂團體──『全方位樂團』,並且擔任團長、主唱及薩克斯風手,以豐富的詞曲創作歌頌人生!
他最大的願望是參與唱片製作及進入流行樂團,出版個人專輯,並與好友一同在音樂的領域中有所發揮,做自己的音樂。
『為夢前行,你我並無不同!』就是這樣的一個信念,使他在追夢的道路上勇敢邁進!
◎阿奇的主要得獎紀錄:
1994年:代表國家赴北京參加『殘障亞運』,榮獲柔道銅牌。
1998年:榮獲行政院文建會主辦之第一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競賽詞曲創作冠軍。
1999年:榮獲第二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競賽詞曲創作亞軍。譜曲、演唱的作品<給我一槍>,榮獲中華音樂交流協會選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
獲選第三十七屆『十大傑出青年』,為該年度最年輕的得獎者,同年得獎者包括『乞丐囝仔』賴東進等人。
商品資料
-
作者: 蕭煌奇
-
出版社: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06-26
ISBN/ISSN:957803381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4 則評論
4 則評論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