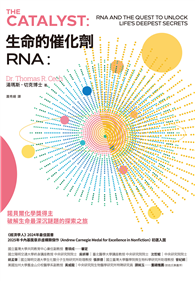在某個地方,有人死了卻成為鬼繼續活下去,有人像鬼一樣活著卻像個男人一樣死去,還有人本來應該像個男人一樣死去,卻為了像鬼一樣活下去而逃走。那是什麼地方?
過去從未過去,而是在背叛與欺騙、秘密與失語間,化為陰魂不散
小男孩在黑暗中爬梳家族、民族與國家的哀傷與憂愁
透過童稚之眼,閱讀愛爾蘭在壓迫與殖民下糾纏不去的幢幢鬼影
《在黑暗中閱讀》是愛爾蘭詩人與學者薛穆斯・丁恩目前唯一出版的一本小說。故事的背景設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德里市,由無名敍事者以日記體例,敍述自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一年,從童年至成人,從無心至有意,從單純好奇親人間諱莫如深的過去,至最終拼湊出糾纏雙親家族三個世代的秘密真相,一路在黑暗中閱讀家族史與國族史的經歷。是理解同樣與大國為鄰,有著同樣複雜難解歷史糾葛的島國愛爾蘭,其百年來矛盾與憂鬱的經典之作。
本書特色
榮獲
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
英國衛報年度小說大獎
布克獎入圍
「小說檢視在北愛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小男孩的個人成長、家族秘密和愛爾蘭歷史三者如何互相糾纏交織成一則深沉的故事……藉由小男孩探索家族禁忌的故事,『把事實寫出來』,開啟了閱讀與書寫北愛經驗的新方向。」──莊坤良(逢甲大學外文系教授丶台師大英語系兼任教授)
「在北愛,個人的悲劇及創傷與政治事件息息相關,政治抗爭所帶來的衝突與災難,立即衝擊著家庭倫理與人際關係。丁恩的小說也直指從十九世紀以來愛爾蘭抗暴、反英國殖民歷史裡層出不窮、也最令人不安的『背叛』主題。」──曾麗玲(台大外文系教授)
作者簡介:
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
丁恩於一九四零年出生於北愛爾蘭德里市,是愛爾蘭知名的詩人、文評家、學者。他是《田野日愛爾蘭文選集》的創辦人之一兼總編輯。除了學術著作,丁恩還出版了四本詩集。《在黑暗中閱讀》是丁恩唯一的小說作品。丁恩曾於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擔任講師,現今則在聖母大學授課。
譯者簡介:
謝志賢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愛爾蘭文學碩士,喬伊斯研究博士。現為自由譯者與文藻外語大學英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其他出版文學譯作還有《新都柏林人》、《入海騎士》、《深谷幽影》。
章節試閱
第一部
第一章
樓梯
一九四五年二月
樓梯那兒,有股清楚且簡單的沉默。
那樓梯間短短的,總共才十四階,全鋪著油氈,上頭原有的花紋其磨損程度讓它看起來就好像模糊的記憶一般。走上第十一階來到樓梯轉角,從那兒的窗戶總能看見外頭的大教堂與天空。再爬三階便到了大概有六呎長的樓梯平台。
「別動,」我媽站在平台那兒說,「不要經過那扇窗。」
我站在第十階,她在平台。我能碰到她。
「有個東西在我們之間。一個影子。別動。」
我沒想動。我著迷了。但是我沒看見什麼影子。
「有人在那兒。一個不高興的人。下樓去,兒子。」
我退了一步。「那妳怎麼下來?」
「我在這兒待一會兒它就會走開了。」
「妳怎麼知道?」
「我會感覺到它走了。」
「那如果它不走呢?」
「它一定會的。我不會待很久的。」
我就站在那兒,抬頭看她。那時我還愛她。她個頭小而且總是很焦慮,但她並不真的害怕什麼。
「我確定我可以走到妳那兒啊,跳個兩次就好了。」
「不行,不行。天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感覺到它就夠糟了;我不想你也感覺到。」
「我不在意感覺到它啊。它就有點像是溼衣服的味道,對不對?」
她笑了。「不是,一點都不像。別說服自己相信這些東西。就下樓去吧。」
我下樓了,興奮地坐在有著紅色火焰與黑色鉛灰的火爐旁。我們家鬧鬼了!我們家有鬼,就在大白天。我聽見她在樓上走動。整棟房子都微微顫抖。不管我走到哪兒,它就在我面前屈服,然後在我後頭安頓下來。過了一會兒她下來了,一臉蒼白。
「妳看到什麼了嗎?」
「沒有,沒什麼,什麼都沒有。只不過是你老媽神經過敏了。全都是幻覺。那兒什麼都沒有。」
她還來不及多說什麼,我便衝到窗戶那兒,但什麼都沒有。我凝視著那迷茫的黑暗。我聽見臥房時鐘的咔嗒聲以及風吹穿過煙囪的聲音,然後看著當我手指滑下,扶手上的灰色微光突然在我手上消失的樣子。就在廚房門四步前,我感覺到有人在我背後,然後轉頭看見一道暗影從窗戶那離開。
我媽在爐邊無聲哭泣。我走過去坐在她旁邊的地板上,然後凝視鎖在火爐欄杆後頭的一抺紅。
消失
一九四五年九月
有人告訴我們說,綠色眼珠的人跟小妖精很親近;它們只是暫時待在這裡,尋找它們可以帶走的人類小孩。如果我們遇見有一隻綠色眼珠和一隻棕色眼珠的人,我們就要在胸前劃十字,因為那個人就是之前被小妖精帶走的人類小孩。那隻棕色眼珠表示它曾經是人類。當它死後,它就會回到藏在唐尼哥山脈後頭的那些妖精土丘,不像我們其他人是去天堂、煉獄、靈薄獄,或是地獄。這些奇怪的目的地讓我興奮,特別是當神父來到瀕死之人家裡進行臨終聖禮或臨終抺油禮的時候。這是為了不讓那個人下地獄。地獄是個很深的地方。如果你掉進地獄,就會在半空不斷翻轉,直到黑暗把你吸進去一個很大的火焰漩渦,然後你就會永遠消失。
我姐姐艾莉許是家中年紀最大的小孩。她比李恩大兩歲;李恩是老二,比我大兩歲。而其他人就隔一年或兩年出生──吉拉、埃門、烏娜,還有笛兒卓。艾莉許與李恩帶我跟他們一起去達菲的馬戲團看有名的班布茲倫,他是表演消失術的魔術師。那座帳篷高到就好像那些支柱是集合在吊架燈照不到的黑暗中。就在那些長凳的陰影中,我站在那些綁滿繩子的其中一根支柱底座旁邊,看他穿著高筒靴、高禮帽,褲腰高過他那顆像氣球般肚子的彩色條紋長褲,還有那件當觀眾鼓掌時他就會翻蓋上來的紅色燕尾服,他這樣看起來就像突然著火的樣子。接著,那頂黑色高禮帽又再出現,彷彿火突然熄滅了。他從空中、他的嘴巴、口袋,還有耳朵裡掏出珠寶還有撲克牌還有戒指還有兔子。當東西都不再消失了,他就從那撮巨大的鬍子後頭對我們微笑,漲起他那顆彩色條紋的肚子,舉起高禮帽致意,輕輕拂了拂那件火焰外套,碰的一聲消失在煙霧之中,聲響嚇得我們跳到半空。但是他的鬍子還在,就在他剛才的位置,在半空中用錯誤的方式微笑。
大家都笑了而且拍手。然後那撮鬍子也消失了。大家笑得更大聲。我偷偷側瞄了艾莉許與李恩。他們也在笑。但是他們真的都知道發生什麼事嗎?班布茲倫先生真的沒事嗎?我抬頭看往黑暗,有點害怕我會看見他的靴子和彩色條紋肚子航向那個吊架燈照不到的黑暗而去。李恩笑了說我是個蠢蛋。「他是從機關門下去的,」他說。「他就在那裡面,」他說,邊指著那個正被兩個人推出去的平台,他們後頭還跟著個孤獨恍神的遊蕩小丑,一手拿著班布茲倫先生的帽子,邊擦去眼中的淚水。大家都在笑而且拍手,但是我覺得很不自在。他們怎麼能這麼確定?
艾迪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那一年是個嚴冬。大雪覆蓋著那些防空洞。晚上,從樓梯窗戶看出去,原野成了孤寂的白色樂園,被星光照亮的風讓玻璃震動得像片不受拘束的黑水,還讓窗檯上的冰打著呼,而我們都入睡後,有道陰影在一旁看著。
那年冬天,鍋爐炸開了,流出來的水從後刺穿爐火,隨著一陣羽狀煙霧和憤怒嘶聲熄滅。那真的很淒涼。沒水,沒暖氣,沒半毛錢,而且聖誕節要到了。我爸找了我舅舅,也就是我媽的兄弟,來幫他修理。來了三個──丹、湯姆,還有約翰。湯姆是有錢人;他是建築承包商,雇別人來工作。他有顆金牙還有一頭捲髮還穿西裝。丹是個皮包骨而且沒有牙齒,他的臉就在嘴巴周圍皺成一團。約翰有煙槍的嘶吼聲,還有能治癒人的笑聲。他們會邊工作邊聊天,說了一個接著一個的故事,而我就跪在桌子旁的椅子上,一邊搖前搖後,一邊聽。他們的故事包括了賭鬼、酒鬼、硬漢、騙子、第一流的泥水匠、拳擊賽、足球員、警察、神職人員、鬧鬼的、驅魔的,還有政治謀殺。有幾個他們不斷說到的重大事件,像是IRA和警察在製酒廠發生大槍戰的那天晚上,艾迪伯伯就是在那時候失蹤的。那是一九二二年四月。艾迪是我爸的哥哥。
幾年後有人在芝加哥看見他,其中一個人說。
是在墨爾本,另一個說。
不對,丹說,他在槍戰那時候死的,屋頂塌下來時,他摔進了正好爆炸的威士忌大酒缸。確定的是他再也沒回來,不過我爸完全不談論這件事。舅舅們總會多花點時間談這件事,就好像在等他回應或是插嘴說出什麼決定性的東西。但他從來沒有。他要嘛起身到外面拿煤炭,要嘛就是儘快轉移話題。那總讓我覺得很掃興。我想要他把那個故事變成他自己的,然後插進他們的談話。但他老是不太參與對話,特別是關於那個主題。
還有一個故事是那個讓布朗神父一個晚上就黑髮變白髮的大驅魔。他們說,那個幽靈生前是一個水手,他老婆趁他不在時勾搭上了另一個男人。他回來後,他老婆就再也不願意和他住一起。所以他就在對面的房子弄了個房間,然後就每天盯著對面他的舊家,幾乎足不出戶。然後他死了。一星期後,那個情夫在樓梯間跌一跤死了。還不滿一年,那個老婆被人發現死在臥房裡,臉上滿是驚恐的表情。那棟房子的窗戶全都打不開,而且樓梯間有股又濃又重會讓你反胃的味道。布朗神父是教區的驅魔師。他被找來後,他們說,他試了四次,邊握著他的十字架邊用拉丁文大喊,才好不容易進到大廳門。一進去,大戰就開始了。整棟房子發出了嗡嗡聲,就好像是用錫做的一樣。神父勇敢擊退了樓梯上的幽靈,他像是驅散將熄之火一樣驅趕它,然後把它囚禁在樓梯平台窗戶的玻璃裡。接著他把受祝過的蠟燭之蠟滴在窗銷上。他說,絕不可以讓人去解開封印,而且封印每個月都要更新。還有,他說,如果將死之人或是犯了不赦之罪的人在晚上接近那扇窗,他們就會在裡頭看到一個受苦的小孩拉長一張著火的臉。它會嗚咽懇求把它從囚禁它的惡魔手中釋放出來。但是如果窗銷被打開了,惡魔就會像一道光一樣進入那個人的身體,然後那個人就會被附身而且永陷絕境。
你永遠也比不過惡魔。
鍋爐修好了,然後他們走了──巨大的白色冬天又在紅色火焰周圍堆積起來。
意外
一九四八年六月
隔年夏天的某日我看到一個家住在布魯契街的男生被輛正在倒車的卡車輾死了。他本來是站在後輪邊,準備等卡車開動時跳上它後頭。但是司機突然倒車,然後那個男孩被捲到輪子底下,接著在街角的人們都轉身開始大叫跑過去。太遲了。他就躺在卡車底下的黑暗中,攤出一隻手,而血緩緩往四面流出來。卡車司機崩潰了,接著那個男生的媽媽出現,看啊又看啊,然後就突然坐了下來,人群圍了過來站在她面前擋住了這個可怕的景象。
我就站在米南公園的矮牆上,大概二十碼遠,接著我看到警車從路盡頭那邊的軍營開過來。兩個警察下車,其中一個警察彎腰查看卡車底下。他站起來把頭上的帽子推到後面,然後雙手在大腿上磨蹭。我想他覺得噁心想吐。他的苦惱就像股味道一樣,透過空氣傳到我這邊;我覺得有點暈眩便坐在牆上。那輛卡車好像又搖晃了一下。第二個警察手上拿著筆記本向每一個事情發生時就站在街角的人問話。他們全都不理他。接著救護車來了。
接下來幾個月,我一直看見卡車倒車,還有羅瑞.漢納威被捲到底下,手攤出來的樣子。有人跟我說其中一個警察在卡車的另一邊吐了。我一聽到這件事,便又感到那時的暈眩,並同情起那警察。但這好像是不對的;每個人都討厭警察,要我們離他們遠一點,他們是壞人。所以我什麼都沒說,特別是因為我一點也不同情羅瑞的媽媽或那個卡車司機,他們兩個人我都認識。那之後還不滿一年,有天警察打斷了我們為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一年一度的篝火而砍樹的工作。我們躲進玉米田後,丹尼.格林詳細告訴我小漢納威是怎麼被警車壓死的,那輛車甚至沒有停下來。「那些雜種,」他說,邊用潮溼的草擦亮他斧頭的斧刃。我綁緊了繞在我腰上的曳引繩而且不發一語;不知怎麼的,這減輕了我一開始感覺到的那種微妙的背叛想法。結果我真的開始為羅瑞的媽媽與那個之後便再也沒工作的司機感到悲痛。警車從下方的路開過時,黃綠色的玉米發出了呼呼聲。我們把樹帶回去時天已經黑了,剛硬的樹枝把黑暗的巷弄掃得一乾二淨。
第一部
第一章
樓梯
一九四五年二月
樓梯那兒,有股清楚且簡單的沉默。
那樓梯間短短的,總共才十四階,全鋪著油氈,上頭原有的花紋其磨損程度讓它看起來就好像模糊的記憶一般。走上第十一階來到樓梯轉角,從那兒的窗戶總能看見外頭的大教堂與天空。再爬三階便到了大概有六呎長的樓梯平台。
「別動,」我媽站在平台那兒說,「不要經過那扇窗。」
我站在第十階,她在平台。我能碰到她。
「有個東西在我們之間。一個影子。別動。」
我沒想動。我著迷了。但是我沒看見什麼影子。
「有人在那兒。一個不高興的人。下樓去,兒子。」
...
推薦序
小說簡易導讀
《在黑暗中閱讀》是愛爾蘭詩人與學者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目前唯一出版的一本小說,丁恩在數次訪談中都曾提及小說中部分內容或橋段皆取材自他自己的成長經驗。故事的背景是設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德里市,由一名無名敍事者敍述自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一年,從童年至成人,從無心至有意,從單純好奇艾迪大伯的下場,至最終拼湊出糾纏家族三個世代的秘密真相,在黑暗中閱讀家族史與國族史的經歷。
故事開始前,丁恩便引了愛爾蘭民謠〈她從市集走過〉中兩句歌詞「常言道,每對結縭的愛侶/總有一人懷著未曾訴說的哀淒」點題,暗示「說不出口的秘密」是引領故事發展的重要主題之一,而這秘密便是艾迪之死的緣由。在小說中,這個秘密也因應不同角色轉化為不同的形態:對敍事者的父親,艾迪之死是讓他在外人面前抬不起頭的羞愧,也是導致家族宿仇加劇的主因;對敘事者的母親,艾迪之死在小說前半段是蟄伏在暗處,卻又不時縈繞心頭的鬼魂,到了後半段更成了讓她進入沉默的枷鎖;對旁人,這個秘密或者是閒睱時的八卦,又或是成了口耳相傳的鬼怪奇談;對敍事者,這秘密是他身分認同的關鍵,去拼湊出隱藏在後的真相成了從少年變成大人的成長課題。然而,去探究艾迪的下場,對敍事者不單只是追溯自己家族的過去,也顯示了瞭解國家因信仰與政治因素而分裂,是如何影響到家人之間的關係與個人的成長。
個人、家庭,與國家三者最明顯的連結便是在與小說同名的〈在黑暗中閱讀〉這一章。在這一章,敘事者找到了母親年輕時看的小說《珊番渥》(Shan Van Vocht)。「珊番渥」是愛爾蘭文,意思是窮老太婆,但它也是愛爾蘭的別名。愛爾蘭作家經常用貧苦老嫗的形象來具現愛爾蘭在英國統治下的困苦生活。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格雷葛利夫人(Lady Gregory)與葉慈(W. B. Yeats)合著的《胡立漢之女凱撒琳》(Kathleen Ni Houlihan)一劇,劇中是以一七九八年起義為背景,愛爾蘭化身為窮老太婆步入民家,鼓吹愛爾蘭青年為她上戰場,犧牲生命,抵禦外侮。丁恩所虛構的這本《珊番渥》與《胡立漢之女凱撒琳》相同,亦是以一七九八年起義為背景,因此當敘事者在閱讀這本小說時,他不只是在閱讀虛構的故事,也同時在閱讀愛爾蘭這個「窮老太婆」的歷史。而敍事者母親在扉頁上的簽名更複雜了被閱讀的對象:「我媽在扉頁寫了她娘家的姓。我盯著它看。即使墨水已經褪色了,但那些字母還是很清楚。它們對我來說很陌生,就好像它們代表的是她成為我認識的媽媽之前的某個人。」對敍事者,母親娘家的姓代表的是另一個身分,一個成為他母親之前的陌生人,也是一段他所不知道的過去,即使已然褪色淡去,卻仍清晰可見。也因此閱讀《珊番渥》對敍事者而言,也是在閱讀自己母親的過去。透過這個簽名,丁恩巧妙地將愛爾蘭的歷史與敍事者母親的過去連結,也將敍事者的個人身分、家庭、與國家三者串連在一起。
另一個將《珊番渥》與敍事者母親連結在一起的便是情節安排。《珊番渥》雖是以一七九八年起義為背景,但主要是羅伯與安的愛情故事。與《胡立漢之女凱撒琳》相似,羅伯為了國家大義,決心離開凱撒琳,放棄愛情。敍事者雖未明說故事的細節,但在他自己與女主角安的纏綿幻想中,卻暗示了故事是以悲戀結尾:「所以我就只跟她說話然後跟她說她有多漂亮還有我怎樣都不會去參加叛亂而只坐在那兒在她耳旁低語然後讓她知道現在就是永遠而不是在未來當槍戰與砍殺結束的時候,當人生剩下的就只是在晚上聽著風在墓地與空曠的山坡嚎哭的時候。」這個因為國家大義而導致的悲戀結局,可說是丁恩對極端國族主義的回應;比葉慈在一九三八年對《胡立漢之女凱撒琳》的晚年省思:「是否我那劇作送了/某些人至英軍槍火下(Did that play of mine send out/ Certain men English fire shot)」 來得直接具體,卻又不若喬伊斯在《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借主角斯提芬之口責難:「愛爾蘭是隻吞食己出豬崽的老母豬(Ireland is the old sow that eats her own farrow)」來得苛刻。丁恩的反思呈現了在國家大義所帶來的激情退去後,逝者已矣,但留給生還者的不見得是光明的未來,反而是淒涼的懊悔。但那份懊悔並非來自於葉慈與喬伊斯文中為愛爾蘭獨立而亡的青年人,而是在家中苦等守候丈夫、兒子、兄弟,或情人歸來的女性;對丁恩來說,「珊番渥」並非是「有著女王般步伐的年輕女性」 所化身的老嫗,亦不是食子的惡虎,而是心懷哀淒的老太婆。丁恩更以敍事者母親的遭遇體現那份哀淒:在結婚前,敍事者母親曾有段悲戀,愛人麥伊亨尼抛棄她,娶了她妹妹凱蒂,卻在凱蒂懷了米芙之後又棄她而去。敍事者的母親便是麥伊亨尼失蹤的關鍵。而在這一章,當敍事者在黑暗中探究「窮老太婆」的過去,想像他與安的浪漫情節,也暗示了他將在現實生活探索母親在「她成為我認識的媽媽的之前的某個人」的過去,並拼湊出她這段悲戀背後的真相。
但真相究竟是什麼,就連敍事者自己也不確定,僅能從「在實際的經過與我所想像的之間,我之前聽過的,我一直聽到的」之間去判斷,而始料未及的是,他越是去探索真相,越是瞭解這段過去,便越讓他與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疏離。從破碎的真相中,敍事者或許解出了瘋子喬的謎語:「在某個地方,有個人死了卻成了鬼繼續活下去,還有另一個人像鬼一樣活著卻像個男人一樣死去,另外還有另一個人本來應該像個男人一樣死去的卻為了像鬼一樣活下去而逃走了。那是什麼地方?」但解開後,他卻成了糾纏母親內心,提醒她深深罪惡感的活鬼魂,母子關係也因此不復過往。
《在黑暗中閱讀》裡的鬼怪奇談通常都不是單純的靈異體驗,而是用來包裝某些不堪提起的回憶的偽裝,這也讓鬧鬼(Haunting)一詞變得複雜。在英語,haunt一字本就有兩個意思:一是遇見鬼魂的體驗,二是因為回憶或情緒所產生的內心糾結。在小說裡,丁恩便利用了這兩層意思將鬼魂與過去連結,並將回憶鬼魅化──鬧鬼(haunting)不是單純「見鬼了」,亦是不斷回想起不堪過去的精神折磨。更特別的是,「鬧鬼」不只會發生在個人身上,更會成為「病灶」在家族裡蔓延,並成了「有害的血緣」世代相傳。凱蒂故事裡的麥拉夫林家族、布朗神父大驅魔的葛雷納漢家族,甚至是敍事者自己家族裡的宿仇,都是將不可明說的過去轉化成了鬼怪奇談,藉此掩飾家醜與內心的罪惡感。然而這個轉化過程也讓敍事者的雙親、外公,以及遇見狐狸精的賴瑞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沉默。敍事者的母親更因為承受不住罪惡感,情緒崩潰,並封鎖自己的內心與過去的鬼魂為伍。
敍事者對過去種種的好奇心,最後演變成為執著,就如他的母親所說:「我覺得你有時候著魔了。你就不能讓過去的事過去嗎?」這份執著也深深影響了敍事者的成長。就敍事角度、風格、與結構來看,《在黑暗中閱讀》乍看是本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通常成長小說的主角在成長過程中都會經歷身分認同的疑難,但最後他/她克服困難,尋得了人生方向,順利在心理層面脫離青少年的迷惘,成為成熟的大人。《在黑暗中閱讀》的敍事者在故事裡確實遭遇了身分認同的困難──被誣陷為告密者、與雙親及手足的疏離感等──為了順利渡過這個危機,他必須解開艾迪之死與家族宿仇的秘密,好讓自己釋懷,並找到屬於自己的未來。可是在解謎的過程,他越陷越深;生理上他是長大了,但心理上他卻越走越回頭,最後就是停留在過去。如果鬼魂在某種程度是過去罪惡感與悔恨的投射,母親是因為看得見鬼魂而封鎖自己,那敍事者成了糾纏她的鬼魂之一也表示他一直活在過去,甚至成了過去本身。當敍事者針對母親說他對過去著魔似的執著,他在內心反駁:「但那不是過去啊而且她也知道。」這句話似非而是地暗示了敍事者與其母兩人的處境──過去不是過去,而是他們的現在與未來,但他們都無法從過去走出來。如果敍事者的現在與未來就是過去,那他在心理上的成長自然便受限,甚至是停滯不前。這或許也解釋了小說最後兩章竟相隔十年的時間。十年來,敍事者就像個局外人,默默看著事態與家人的變化,但也因為選擇沉默,他與雙親的關係仍未見好轉。在最後一章,敍事者簡述了十年後雙親的生活、凱蒂與家族的相處,還有他的兄弟們如何遭受英軍的暴行,卻對他自己這段時間的生活隻字未提,因為他就是活在過去,沒有成長,也因此沒有值得交待的情節。即使他最後終於補完了艾迪之死的關鍵,但自始至終,他都未能建立自己人生的論述。
丁恩於小說中,藉由敍事者未能成長的人生,暗示了在英國殖民下且分裂的愛爾蘭長久以來也未能成長,總是一犯再犯過去的錯誤。個人、家族、與國家三者在《在黑暗中閱讀》裡從未是獨立的個體,而是三位一體的存在,三者彼此影響,彼此牽連。在愛爾蘭文學,這雖不是新鮮的主題,但丁恩將敍事者母親做為「窮老太婆」的再現,卻讓讀者省思極端國族主義背後鮮被提起的淒涼。在這本小說,丁恩仔細建構了每個事件與每個章節,讓它們緊緊相扣;某個莫名的橋段,可能是解開之前或之後謎題的線索。而讀者,就得和敍事者一樣,在黑暗中摸索與閱讀,尋得方向。
小說簡易導讀
《在黑暗中閱讀》是愛爾蘭詩人與學者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目前唯一出版的一本小說,丁恩在數次訪談中都曾提及小說中部分內容或橋段皆取材自他自己的成長經驗。故事的背景是設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德里市,由一名無名敍事者敍述自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一年,從童年至成人,從無心至有意,從單純好奇艾迪大伯的下場,至最終拼湊出糾纏家族三個世代的秘密真相,在黑暗中閱讀家族史與國族史的經歷。
故事開始前,丁恩便引了愛爾蘭民謠〈她從市集走過〉中兩句歌詞「常言道,每對結縭的愛侶/總有一人懷著未曾訴說的哀淒」點題,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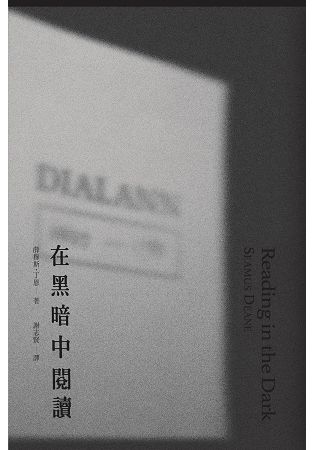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