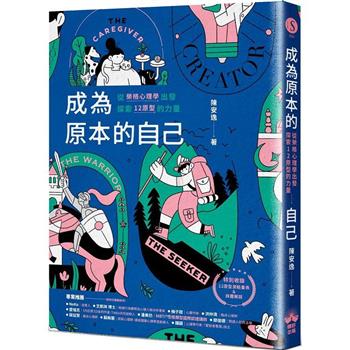☆轟動2013全球書市,歐美文壇最受矚目新銳作家
☆版權受出 英、美、德、法、義大利、荷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瑞典、丹麥、挪威、芬蘭、捷克、斯洛伐克、以色列、巴西、中國
迪麗真妮扣人心弦的小說是對暴政的強烈控訴,對背負歷史傷痕者動人的致敬,也是對人性嚮往自由的頌揚。--《追風箏的孩子》作者卡勒德.胡賽尼 Khaled Hosseini
每場革命都有不為人知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伊朗人將國王驅逐出境,以為換來了自由民主的共和,然而,伊斯蘭神權取而代之,以激烈手段排除異己。一九八八年,一場整肅風暴在德黑蘭監獄染血前行,預估有四千至一萬兩千名政治犯遭到處決……
那段被遺忘的歷史影響這些孩子每一步和每個決定,
閉上眼睛,一切重現眼前
他們深信,活著就足以證明有可能從殘破的瓦礫中重建美好的事物
總有一天,他們要攜手回到故鄉藍花楹樹下,敘說回憶裡的故事
奧米德的爸媽被帶走時,他正在吃飯。媽媽匆匆撫摸他的臉,她的手指冷得像冰。爸爸親吻他的額頭,叫他不要害怕,他們很快就會回來。但他們從來沒有回來。於是他時時睜大眼睛、豎起耳朵,彷彿一直在聆聽,想要揪出徘徊在空氣中任何一點一滴父母的消息……
瑪莉安接起電話時,一顆心直往下墜,對方還沒開口,她就知道了。她已經好幾個月沒見到丈夫。誰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每個人都怕遇上最壞的結果。她聽說有家屬去探監時,卻拿到囚犯的私人物品,才知道人已經不在了。他已經不在世上了。家屬就是這樣得到死訊:一張紙和半袋人生的碎片……
本書透過六個交錯的故事,揭露一九八八年發生在德黑蘭艾文監獄的血腥肅清。
臨盆在即忍受殘酷訊問的女子、盼望擁抱女兒卻莫名被處決的父親、手握丈夫死亡宣告和半袋人生碎片的妻子、不能開口問起父母去向的孩子,這些人躲不開歷史染血的雙手,可是他們深信,活著,就足以證明有可能從殘破的瓦礫中重建美好的事物。活著,就能繼續說故事,為死者傳頌驪歌。
作者簡介
薩哈兒.迪麗真妮(Sahar Delijani)
一九八三誕生於德黑蘭,年長後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研讀比較文學,目前旅居義大利杜林(也是書中數名角色流亡成長的地方)。
迪麗真妮發表過許多詩作與短篇小說,作品散見各文學期刊。二○一○年她以〈另一個新生〉(Another Birth)入圍手推車獎(Pushcart Prize,美國小型出版社最佳年度文學作品獎),本書便是以這篇短篇小說為基礎發展而成。
參見迪麗真妮網站:www.sahardelijani.com/en.
譯者簡介
楊惠君
政大英語研究所碩士,從事翻譯工作多年,譯作豐富,包括《辛格家族》、《來自巴拉圭的情人》、《謀殺之心》、《班伯里十字》、《飲食與愛情》、《法律與文學》、《建築的表情》、《完美的房子》、《生命就是堅持信念,走到最終》等。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