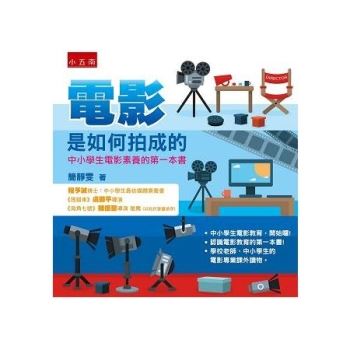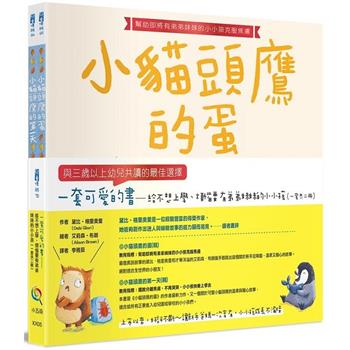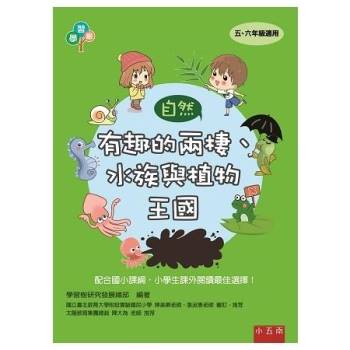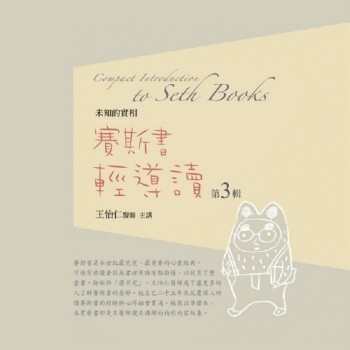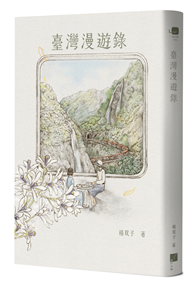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書籍特色】
不僅僅是「勵志書」,本書真的能讓你找到自我與人生的希望!
本書出版後好評不斷,打動並激勵無數青少年讀者的心!
獻給重視自我探索的讀者,一部坦誠、真實的好書。
二十個真實事件:童年歷經性侵、家庭破裂、「出櫃」、家暴、憂鬱症、重傷後復原、面對摯愛的死亡等等,再走過憂鬱重生的激勵故事。
【內容簡介】
人生總會有遇到悲劇、不幸或困難的時候,也因此,其他人克服難關的故事,總是能帶給我們極大的力量。因為這證明了,人的精神力量,是可以克服逆境的。
《藍色憂鬱的反思》集結了二十個故事,希望能給正在艱困的人生中掙扎的人,帶來希望。故事的主人翁主要是二、三十歲的澳洲年輕人,各自有著慘痛複雜的過去:童年受到性侵、家庭破裂、「出櫃」、家暴、憂鬱症、重傷後復原、面對摯愛的死亡等等。
雖然大多數的故事主角,都是一般人,不過參加過〈老大哥〉節目演出的潔絲.哈帝、奧運跨欄選手凱爾.范德庫普以及「生活終結樂團」主唱克里斯.契尼等名人,也在書裡分享了他們遇到的難關。換句話說,人生沒有大小眼,誰都有遇到難關的時候。
然而,就像這些故事證明的,在逆境讓人最痛苦、最脆弱的時刻,也會激發我們的勇氣與決心,谷底反彈,重新出發。
在人生不順遂的時候,這些故事讓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孤單的──其他人也經歷過這些事情,而且熬過去了。希望這些人的故事可以啟發你,找到通過困境的道路,來到憂鬱的另一邊。
作者簡介:
麥可‧柯林(Michael Colling)
住在墨爾本,是青少年工作負責人,以各種方式積極協助年輕人度過難關。他也是「Schools Out! Youth Consultants」的創辦人,為全國的青少年開設增進生存技巧的課程,並致力傳送希望的訊息給年輕人。他在二○○五年為NOVA100 FM電台主持了「Nova’s All Ears」節目,探討青少年自殺與憂鬱症的問題,並因此獲得「澳洲商業廣播節目獎」。
譯者簡介:
鄭淑芬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修畢學分),主修國貿、英文、翻譯。目前專職翻譯,具備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英譯中證書。最新譯作:《領導之道》、《鍛鍊人生反彈力》、《真愛旅程》(時報)。鄭淑芬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修畢學分),主修國貿、英文、翻譯。目前專職翻譯,具備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英譯中證書。最新譯作:《領導之道》、《鍛鍊人生反彈力》、《真愛旅程》(時報)。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好評推薦】
˙我年少時要是能看到這種書,就不會在成年後,還要花那麼多年的時間處理自己的問題。這本書最傑出的是謹慎而清楚地傳達了一個最簡單的訊息,那就是:你不孤單。我很驚訝看到這本書裡,對每一個討論到的主題,展現了豐富的同情和理解。透過「傾聽」這個最簡單的行為,讓年輕人表達自己、訴說自己的故事。《藍色憂鬱的反思》給了許許多多人希望。
──戴倫.海斯(Darren Hayes),歌手,前「野人花園」主唱
˙每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人,不論是已經找到自己,或者是還在尋找,都應該要讀《藍色憂鬱的反思》。這本書坦誠、真實、切題,能引起共鳴。主編麥可‧柯林(Michael Colling)所集結的故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任何人都能找到與自己切身相關的故事。要將生命的拼圖組合完整,絕對少不了這本書。
──布瑞特.莫瑞(Brett Murray),DARE:OPS創辦人,專業講師及青年激勵者
《藍色憂鬱的反思》以鏗鏘有力的聲音,再次證明人類擁有驚人的能力,能化苦難為幸福——這是每一個人都擁有的力量。──傑克.希斯(Jack Heath),啟迪基金會(Inspire Foundation)創辦人暨執行長
名人推薦:【好評推薦】
˙我年少時要是能看到這種書,就不會在成年後,還要花那麼多年的時間處理自己的問題。這本書最傑出的是謹慎而清楚地傳達了一個最簡單的訊息,那就是:你不孤單。我很驚訝看到這本書裡,對每一個討論到的主題,展現了豐富的同情和理解。透過「傾聽」這個最簡單的行為,讓年輕人表達自己、訴說自己的故事。《藍色憂鬱的反思》給了許許多多人希望。
──戴倫.海斯(Darren Hayes),歌手,前「野人花園」主唱
˙每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人,不論是已經找到自己,或者是還在尋找,都應該要讀《藍色憂鬱的反思》。...
章節試閱
人間至慟
強‧史戴賓(Jon Stebbins)與妻子蘇(Sue)敘述他們在獨子自殺後,從極度痛苦到漸漸平復的過程。
最初的衝擊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晨,警察打電話來,跟我們說馬修自殺了,而他自殺的地點,是一個我們全家經常去度假、共度了很多快樂時光的地方。那一刻,我們的生命徹底改變,再也無法逆轉。
從那時起,我們就像兩個不同的人,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我們看世界的眼光變了,看自己的眼光也變了,別人看我們也不一樣了。或許有兩年之久,馬修的死,帶給我們極大的痛苦,有時候那痛苦就好像從四面八方逼近的牆一樣,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日子久了,那巨大的痛苦才慢慢消退,現在只會偶爾出現,也不再像頭幾年那樣強烈得嚇人了。
我們對自殺沒有直接的經驗,沒有「典範」可依循。我們都來自幸福的家庭,知道家人一定會支持我們(也確實如此),但我們也瞭解,其他家人跟我們一樣倉皇失措,我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打造一個新的世界。我們兩個都是專業人士,處理各種與人有關的疑難雜症(蘇是家庭輔導工作者,強是心理諮商師),但這件事讓我們學到,自殺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就像是遇到一個全新的世界,以前的經驗都派不上用場。
失去孩子,絕對是人生最可怕的經驗──我們遇到很多父母都這麼說──所以,當然到目前為止都是我們最慘痛的惡夢。我們能夠有今天這樣的成果,實在是漫長而耗費心力的過程。現在,大多數時候,馬修相對來說已經在我們的記憶裡安息了。
我們各自走過了不同的道路,也有一些共同的感受。在與各位分享我們各自的心路歷程前,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兒子,馬修。
馬修(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八七年十月四日) 馬修是我們的次子,也是唯一的兒子。我們另外還有兩個女兒,在馬修死時,分別是十九歲和十三歲。馬修高大、帥氣、聰明、敏感,很有愛心,是個開朗、友善、溫和的人。他還具有以下特質:
‧很注意各種社會議題和社會缺陷
‧明辨是非
‧厭惡暴力、戰爭、核子問題等等
‧很有創造力──馬修寫了一些很美的詩和散文,我們視為珍寶
‧注重環境以及環保問題
‧喜歡自然和動物
我們會提這些細節,是因為幾乎所有子女自殺的父母,都說自己的孩子有類似的個性與特質。
表面上,馬修的生活很精彩,可是卻因為一年比一年不快樂,最後決定自殺。回想起來,我們瞭解到,馬修的不快樂,是因為他對自己和未來缺乏信心。很多人都問我們,我們也這麼自問:「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考慮要自殺嗎?」回想起來,確實是有一些狀況,譬如他很不快樂,缺乏自信,對未來也不抱希望(他的中學生活並不愉快,雖然他死前的那一年,可以說是最順利的一年)。在他死前三週,他才跟女朋友分手,我們猜那件事應該也有很大的影響。很多父母都說,他們的孩子在自殺前,都剛好結束一段感情。
回想起來,上面說的那些「跡象」,似乎都很明顯,可是我們卻很難分辨馬修的問題,跟一般正常青少年會遇到的問題有什麼不一樣;畢竟,很多年輕人都有同樣的狀況,甚至還更嚴重,但他們並沒有選擇自殺。我們當時有鼓勵馬修去進行諮商,他也照做了。馬修死後,我們兩個都承認,確實有點擔心馬修會自殺,但那只是隱隱約約的感覺而已,我們更擔心的,是他沒有能力為自己找出正面的人生方向。
我們的故事 因為愛馬修,也因為想要瞭解,為什麼馬修以及其他無數的年輕人,會認為生命毫無意義,以至於選擇以最終極的手段結束痛苦,於是,馬修死後,我們的生命就從這個念頭出發。我們的另一個動力,是想要進一己之力,去瞭解並支持其他也面臨喪子之痛的父母。我們認為這就是馬修的死賦予我們的意義。接下來就讓我們訴說各自的心路歷程。
蘇 在馬修的成長過程中,我跟他一直很親。我有很多美好、快樂的回憶,但也分享了他的痛苦和掙扎。馬修是個很能把感覺說出來的孩子,我們也很有話聊。馬修死時,我真的大受打擊,因為那不是我的人生經驗可以理解的事。回想起來,第一年那一整年,我都處在震驚之中。雖然我還是勉強能正常運作,但每次都只能維持一個鐘頭左右。一直到第二年,那種痛苦的真實感才慢慢浮現;我這才真實感覺到,我再也不能與他分享生命中的所有喜怒哀樂了。這個領悟,在身體上、精神上都帶給我極大的痛苦。那是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好像所有發生的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不過,馬修死後沒多久,我就下定決心要好好活著;我要用最大的力氣去奮戰,以最強的意志去求生。這是段很艱辛的旅程,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會成功的。
身為一個母親,要接受馬修痛苦到選擇自殺的事實,到現在仍讓我很難受。我很瞭解他,個性溫和又厭惡暴力的他,竟然採取了這麼激烈的行動,讓我感到非常悲痛。
我發現我必須尋求家人和朋友以外的協助,這份認知是我回復正常生活的重要關鍵。我很幸運找到一位悲傷輔導師,可以陪我走過部分傷痛的旅程,也教了我一些應付悲傷的技巧。在事發初期,強和我都太傷心了,而且我們傷心的方式很不一樣,所以需要外界的支援。雖然我們夫妻感情很好,但在那種時候,我們很難互相支持。有太多事情需要面對,而我們在感情上都彷彿瞬間枯竭,僅剩的一點力氣,也必須留給女兒,為女兒維持一定程度的「正常生活」。
回想起來,馬修死後,我最難面對的幾件事是:
‧覺得自己不是個盡責的母親
‧質疑自己當人的價值
‧失去信心
‧儘管別人給我很多支持,還是覺得很孤單
‧強烈思念馬修
‧擔心另外兩個女兒,又怕過度保護她們
尋找意義,成了我的重心。在傷痛初期,對我來說,瞭解細節成了很重要的事。譬如我會去跟馬修的朋友談,尤其是他生命最後那些日子跟他在一起的朋友。我必須追溯他生命最後的旅程,直到我把所有能找的資訊都找遍了,並且接受,有些問題永遠得不到答案。這是我的悲傷之旅中,一段很重要、也很孤單的旅程。其他我覺得也很重要的行動,包括:
1.我刻意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支援網,成員都是在我心情跌落谷底時可以求助的人。
2.馬修死後兩、三個星期,我開始寫日記。這給了我發洩情緒的管道,也成為觀察我進展的好方法。頭兩年我每天都寫。
3.馬修死後三星期,我回到工作崗位。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我能平復悲傷的關鍵因素。剛開始,工作可以讓我從巨大的痛苦中暫時逃脫數個鐘頭,同時也擴展了我的思考模式,強迫我再度跟人群接觸。如果我每天都待在家裡,肯定永遠起不了床。
4.頭幾個月,我也向同樣有喪親之痛的家庭求助,並加入了自殺倖存者支持團體「同情之友」(TCF,The Compassionate Friends)。起初要踏出這一步,真的讓人很害怕,但是更進一步參與這個團體的活動後,對我的調適過程帶來深遠的影響。感覺自己的想法和情緒都是正常的,會帶給人極大的力量。透過我跟在「同情之友」認識的喪親家庭一起努力的結果,我已經能將馬修死亡的悲劇,轉化成具有正面價值的事了。
這段傷心的旅程,讓我能夠:
‧帶領「同情之友」支持團體,至今已達十七年。
‧取得「失落與悲傷諮商」的碩士文憑。
‧與強一起,在澳洲以及國外以自殺哀傷為主題的座談會及工作坊上演講。
我非常想念馬修;傷痛仍在。但我現在已經學會將他的死融入我的人生中,再度找到了自我的價值。
強 有好幾個星期,除了深切的懼怕以及越來越明顯的痛楚外,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懼怕,是因為我擔心自己熬不過這個經驗,那份痛苦大到我難以承受。兩、三個星期後,我就回到墨爾本大學,繼續講師的工作,也設法應付得很好(我認為如此),可是一直要過了一年半之後,我才能重拾諮商工作,因為我的個人經驗太鮮明了,我沒有自信能保持客觀。
對於事發第一年的記憶,很多細節都模糊了,不過我知道我很容易在最重要的場合突然哭出來。而馬修死後大約兩、三個星期,雖然一切都好像隔了一層,感覺很不真實,但我卻實際上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痛楚,有時候會讓我痛得縮成一團──這在開車時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後來一年一年過去,這份痛楚慢慢淡化,現在只有偶爾看到或發生一些事讓我想到馬修時,我的心才會隱隱抽痛。
除了身體和精神上的深刻痛苦外,我對頭幾年的記憶,就是對這種事的不知所措。因為它超出我的想像範圍,我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依據。那是一種被徹底毀滅、徹底孤單的感覺──儘管周圍全是關心我的親人和朋友。
身為父親,我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既無能又無助,只剩下深深的困惑。我失去信心與自信,也對於自己未能幫助馬修而感到內疚,不過幸好我很快就接受了,我已經在自己的知識和理解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只是很難過這樣做還不夠。我也對人生的不公平感到憤怒,不過這種感覺通常也很快褪去,只能對無法挽回的失落,感到挫折萬分。
在行動上,頭兩、三年我還理不出方向,會週期性地失去活力、無法專心,沒有信心做出各種決定。現在這種情況也消失了,長久維持積極、自信的態度,也變得容易多了。但是我相信,馬修的死,在我內心深處留下一處脆弱的傷口,那是一種永遠無法再度完全信任這個世界的感覺(這或許也是一種寶貴而真實的遺贈吧!)。
雖然蘇和我感情很好,但因為我們面對悲傷的方式不一樣,我們都感覺到彼此的關係越來越緊繃。幸好很早就有人提醒我們,可能會有這種差異,因此一般來說,我們都能設法支持彼此的差異。我傾向在短暫的瞬間,「用大腦」積極處理我的悲傷,專注在各種問題上,大量閱讀,也提出各種疑問,然後就徹底抽離一段時間。而蘇的方式是會堅持處理同一個問題,直到她徹底搞清楚為止。她習慣「用心」來處理感覺、找別人談話。從這種角度看來,我們的應對方式,其實就是典型的男女差異。
老實說,回首過去,我真的很佩服自己在馬修死後達成的成就。除了頭兩年──那兩年基本上只能說是「勉強撐著」,我把諮商工作完全停掉,將精力都集中在教書上——我做了很多事(有些令人興奮,有些令人沮喪,但全都不簡單),都源於馬修的死。這些事包括協助帶領「同情之友」自殺支持團體,跟其他喪親家庭一起合作,為「同情之友」在維多利亞州各地規劃並主持訓練課程,協助訓練志工、諮商師以及支持團體的主持人。我還先後拿到了悲傷與失落這個領域的碩士及博士學位,專攻支持喪親家庭,主持一系列的工作坊及研討會,目前則跟幾個喪親家庭一起進行一個大規模的研究計畫。出於本能,基本上我做的這些事,都是我最熟悉與擅長的事,那就是發揮我的教學技巧,並且與人合作。
在從悲痛復原的道路上,我學到很多關於自己的事,很多都讓我很意外,這包括發現自己在本質上是個對生命很樂觀的人,還有,我面對馬修死亡的方式,是讓自己投入那些有可能讓我們理解、或者更加理解此種悲痛經驗的活動裡。
現在的我們 馬修結束自己的生命已經二十年了,對我們來說,這段路就像二十光年一樣漫長。要是馬修沒有死,我們不知道我們會是什麼樣子,但我們能訴說的故事,一定跟現在很不一樣,因為他為我們設定了過去這二十年的方向。我們還是很想念他。我們家,以及我們的記憶裡,永遠會存在一個裂縫,一個永遠無法收攏的裂縫。我們失去了一個善良、充滿愛心的年輕人,一個兒子、朋友,或許也失去了原本可能有的新家庭與孫子孫女。在這段艱辛的歲月裡,幸好我們能擁有彼此,還能有兩個寶貝女兒的支持,並且分享她們錯綜複雜的情緒──既有快樂,也有挑戰——因為她們也必須以自己的方式,釋懷失去兄弟的痛苦,並且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愛與家人確實幫助我們熬了過來,走出馬修的死帶給我們的傷痛,但是那道傷口,終究永遠無法完全癒合。
人間至慟
強‧史戴賓(Jon Stebbins)與妻子蘇(Sue)敘述他們在獨子自殺後,從極度痛苦到漸漸平復的過程。
最初的衝擊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晨,警察打電話來,跟我們說馬修自殺了,而他自殺的地點,是一個我們全家經常去度假、共度了很多快樂時光的地方。那一刻,我們的生命徹底改變,再也無法逆轉。
從那時起,我們就像兩個不同的人,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我們看世界的眼光變了,看自己的眼光也變了,別人看我們也不一樣了。或許有兩年之久,馬修的死,帶給我們極大的痛苦,有時候那痛苦就好像從四面八方逼近的牆一樣,幾乎讓人...
目錄
序
前言
一 與媽媽同行的日子
二 努力解開心結的人生
三 半夜的信號
四 歡笑、眼淚與記憶
五 我的文化衝擊
六 因禍得福
七 膚色有別,血都是紅的
八 失落與尋得
九 痛苦的就學經驗
十 以愛之名?
十一 撞擊、燃燒、重新出發
十二 學會接受
十三 各人的十字架
十四 置之死地而後生
十五 「很快就見面了,孩子」
十六 這樣的家
十七 人生最大的難關
十八 異性戀世界裡的同志
十九 只要一句話
二十 人間至慟
編輯後記
來自「Reach Out!」的訊息
序
前言
一 與媽媽同行的日子
二 努力解開心結的人生
三 半夜的信號
四 歡笑、眼淚與記憶
五 我的文化衝擊
六 因禍得福
七 膚色有別,血都是紅的
八 失落與尋得
九 痛苦的就學經驗
十 以愛之名?
十一 撞擊、燃燒、重新出發
十二 學會接受
十三 各人的十字架
十四 置之死地而後生
十五 「很快就見面了,孩子」
十六 這樣的家
十七 人生最大的難關
十八 異性戀世界裡的同志
十九 只要一句話
二十 人間至慟
編輯後記
來自「Reach Out!」的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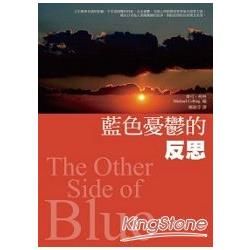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