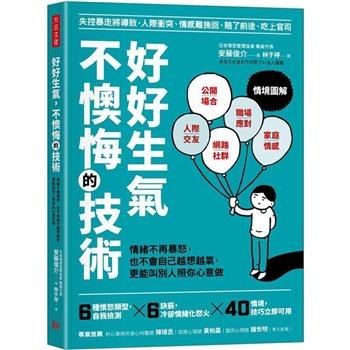闖關
霧鎖機場。
李映元搭乘的世界航空AX111客機,已經在台灣上空盤旋將近半個鐘頭,根據管制塔台傳來的消息,今天早上忽然升起一大片濃霧,籠罩桃園機場附近的區域,地面的能見度不到三百公尺,那是台灣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大霧。因為這個原因,除了AX111客機之外,還有十幾架飛機也在空中滯留,等待降落。
飛機平穩地翱翔著。閉上眼睛,李映元靠在座位的椅背上,想像著飛機破雲而出,就會有一座美麗島映入眼簾,如同一顆翠綠的寶石,閃耀在湛藍的太平洋西岸,多少年來,這種景象早已在他的腦海裡一再浮現。而由於他並不是那種故意不回家,而是根本回不了家的人,在過去的歲月裡,鄉愁從未枯萎,只是不斷被惡意摧折而化為絕望。所以,像個曾經多次被判死刑的囚犯,他也已經學會如何安靜地等待星光褪逝,畢竟在黎明行刑之前,長夜也將到達盡頭。
「再長再苦的思念我都忍受過了,但這一次,就請讓夢裡的故鄉,真實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吧!」李映元在心裡暗自祈禱,一萬五千公尺底下就是他的島國,可是,他仍然不曉得能在那裡著陸。
霧終於散了,機長高興地廣播,準備改飛高雄小港機場的飛機,在最後一刻,得到降落桃園的許可。李映元稍微鬆了一口氣,因為,如果臨時改變降落地點,他原來的入境計畫就會全部落空,而他的返鄉之旅,真的就只能完全依靠命運的安排了。
機艙門已經被打開,李映元緩緩起身,背起墨綠色的背包,禮貌地對鄰座一位年輕媽媽說再會,看到她輕輕搖動懷中嬰兒的小手臂,幸福地向他回禮時,他感到一絲溫暖的感動,臉上不禁出現登機以來難得的微笑。
跟著同機的旅客穿過空橋,李映元抵達機場航廈,低頭看看手錶,再核對時間。首先,他走到化粧室稍作梳洗,再一次從鏡子裡,仔細端詳自己體重增加十公斤後的模樣,「真的還是不夠胖。」他的心裡開始感到有點擔憂,然後,他轉身不經意地和同機抵達的一位紅衣夾克男子打過照面,接著,他們分別走進入境大廳。
桃園國際機場和三十五年前李映元出國時改變許多,擴建之後的建築透露出濃厚的中國風格。早上的陽光透過精心設計的採光屋頂,正好照在大廳正中央一座九公尺高的鋼雕,兩道簡潔的弧形在此矗立,伸展到空中相互纏繞,線條龍飛鳳舞,非常優美。李映元知道它被稱作「國境之門」,是慶祝台灣終於回歸中國的象徵,在統一大業完成之後,中國政府特地指示北京一位非常著名的雕塑家,由他主持鑄造,再慎重其事以專機空運過來,當作祖國贈送給台灣的賀禮。
由於誤點和正常的班機幾乎同時抵達,加上被耽擱起飛時間的飛機,機場起降的調度,包括停機坪、滑行道和跑道都十分忙碌,出入境的旅客也一下子增加了許多,每個人都抱怨連連,讓整個機場的服務與工作人員焦頭爛額,窮於應付。
儘管有二十道入境的櫃台,通關的隊伍卻越排越長,現場開始出現不耐煩的氣氛和混亂的場面,這種情況比李映元預期的更加理想。儘管這樣,擁擠在嘈雜的旅客當中,他拿著假護照的手心還是禁不住冒汗,心跳開始加速,但是,他努力告訴自己,以前也有許多人像他一樣嘗試過,但從未成功,所以,他一定要保持冷靜,不能落出破綻被人懷疑,畢竟這是他遙遙歸鄉路的最後一步。在被中國政權一再蠻橫地抵制,被紐約中國台北辦事處毫無止境地拒絕簽證之後,他一定要在今天,終結這段漫長的違反人道的流放之旅。
安全檢查非常嚴格,每個人和每件行李都必須經過金屬探測器掃描,假如有可疑的人物,還要改由安檢人員仔細搜查。
隊伍緩慢向前移動,李映元抬起頭,仔細地打量通關之後可能面對的狀況。他看到許多排了好久才通關的旅客,扛著行李,也帶著歸鄉的喜悅,快速地從西南邊的大門離開。大門的兩側分別站了兩組航站警察,每組各有三人,另外,有四個手拿對講機的安全人員到處遊走,毫不放鬆地緊盯著每一個驗證的櫃台。在此同時,他注意到有兩個西裝革履的男子,正朝著快要通關的紅衣旅客揮手,透過行前的秘密視訊,李映元認識那兩人,他們是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擁有特權,可以申請來到這裡接機。這些人將會協助他闖關,打破禁錮許多流亡海外台灣人的黑名單。
依照原來的計畫,李映元排在三號櫃台的隊伍準備接受驗證,因為那裡離入境大門較近,而且根據他的估計,等一下大門附近的警察,應該全部都會離開,因為,他們將會有一段相當忙碌的時間。
把護照交給坐在櫃台那位綁著馬尾的年輕女子,李映元耐心地等待她核對相片和文件,雖然已經職業性地拿起核可的印章,但顯然她還是感到有一點猶豫,「柯博卿先生?從東京來的?是回來探親嗎?」馬尾女子抬頭仔細看著他,輕聲地問。
「是的,最近有開始減重,比較瘦也會比較健康。」李映元望著她,輕鬆地回答。
就在他們對話的時候,十二號櫃台那位紅衣男子,把護照丟給檢驗員之後,並未等候驗證,就快速地直接穿過櫃台,這個突兀的舉動讓櫃台的男職員大吃一驚,他接連叫了兩聲,「先生,你的護照還沒檢查!」但紅衣男好像沒有聽到,根本不予理會,繼續快步往大門走去,「非法入境,快攔住他!」矮小的男職員警覺地從後面追了出來,歇斯底里地大聲狂喊,就在大家都還搞不清狀況的時候,大門所有的警察,還有不知道從那裡冒出來的維安人員,全都湧向紅衣男子,同一時間,那兩個立委也跑到紅衣男的身邊,一左一右護衛著他,以跑百米的速度,衝向前來圍捕的安全人員。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用手指向對峙在大廳中央,糾纏在一起的兩組人馬,李映元故意這樣問。「不關你的事。」綁馬尾的女職員神色緊張地斥責他,眼睛卻緊盯著混亂的現場,不暇思索地,她把准許入境的官印蓋在柯博卿的護照上面。
「你可以先離開了。」把護照交還給李映元,她催促他趕快走開。
李映元拿著護照,從容穿過入境大門,走進桃園機場的中央大廳,許多台灣人正在這裡迎送歸鄉或出國的親人。他沒有多作停留,快速地走出機場航廈,公車站牌前面正停靠著一輛前往高鐵的接駁車,他加入等車的隊伍,沒多久,就跟著其他的旅客魚貫上車。
接駁車滿載歸鄉的遊子和興奮的觀光客,引擎馬上被發動,緩緩駛離機場大道。
透過車窗,李映元回望桃園機場,他看到航廈屋頂上三面紅色的旗幟,那是位居中央的五星旗和兩旁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正在隨風飄揚。
李映元瞬間內心激動不已,強忍著幾乎快要奪眶而出的感傷淚水。
在心裡,他大聲吶喊:「母親,我回來了!」
他終於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但是,這裡再也不一樣了。
俯瞰舊時總統府
羅大任的住處高居台北東區精華地段一棟三十層大廈的頂樓,裝潢十分典雅。
林淑媚走進客廳,看見門旁紅褐色桃花心木製成的桌子,上面的花瓶裡插著一大叢火紅的玫瑰花,在鮮嫩的綠葉襯托之下正恣意怒放。她記得一年前,羅大任初次帶她來這裡過夜,隔天醒來,他已經先行離開,陌生又孤單的感覺讓她感到非常惶恐。但當走進奢華的浴室,她發現浴池清澈的水面上,竟然灑滿了鮮艷的玫瑰花瓣,晨光之中溫暖的水霧薄薄地升起,一面碩大的鏡子映照著室內層次的光影和繽紛的色彩,那天,她一個人沉醉地浸沐其中,肌膚彷彿變得分外光潤無瑕,也讓她格外想念他。
今天他們的定情日。玫瑰花的香氣彷彿昔日,讓她感到無比興奮。把粉紅色的名牌包和白色的外套放在小牛皮的沙發上,她優雅地走向書房。
羅大任正坐在黑色的大書桌後面,聚精會神地從加密的電腦螢幕上閱讀北京傳來的指示。他背後的牆上掛著一幅特別收藏的油畫,那是五十年前一位傑出的台灣畫家的作品,畫裡的牛車正穿過翠綠的香蕉園,炎夏的太陽透過蕉葉光影交錯,灑落在黃牛和老農人的身上,坐在牛車後面有兩個小孩,一起把手伸向車旁結實纍纍的金黃香蕉串,笑得好開懷。林淑媚來自屏東鄉下,這幅畫讓她感到很親切,但卻一直不能理解為何羅大任也會那麼喜歡它,對她而言,羅大任的成長背景一直是個謎,他也從未告知,可是,看起來他就是不像會耽於懷舊的人,另一方面,由於羅大任每天處理的都是冰冷緊張的國安事務,而畫裡南台灣農村自然的景色,所呈現出來的鄉土溫暖的氣息,很明顯地,和他的神祕職務完全格格不入。
「或者,他本來就是一個難以捉摸的人物。」即使很少人知道,林淑媚卻曉得羅大任真正的身分,這是因為在交往的過程裡,有意無意中,他會炫耀他的權勢與掌控的能力,而由於他真的非常喜歡她,因此認為即使林淑媚知道也無妨,至少這樣可以讓她感受到他真心相待。表面上,羅大任的職位是中國台北特區國安局局長,也是位階最高的情治首長,然而,實際上,台北行政長官對他根本沒有指揮或任免的權力,他是由中國國安局總部直接派駐台灣的情報頭目,直接由中南海的權力核心指揮,並對其負責。
看到林淑媚走進來,羅大任本能地把電腦設定為待命狀態,人往椅背靠著,閉上眼睛稍作休息,他開始思索起來。根據情資,海外的台獨份子,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的台獨人士,最近出奇的安靜,負責監控那批人的單位屢次回報,世界各地的台獨運動正快速呈現衰退的現象。但是,他反而認為這種情況很不尋常,猜測那些台獨份子那有可能這麼容易善罷甘休,而預防這些海內外台獨異議人士,串聯起來興風作浪,一直是北京交待他的首要任務。
「難道他們真的不瞭解,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有些人就是永遠不會覺悟!」在心底,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這時候,林淑媚正走到羅大任的身旁,聞到了她最喜歡的古龍水的味道,忍不住低頭要親吻他的頸部,「我們可以暫時放下你的工作嗎?」依偎在他的耳邊,她低聲呢喃。羅大任根本沒有看她一眼,就直接伸出手臂,攬住她纖細的腰,毫無抵抗地,她整個人已經輕盈地滑進他的懷裡。林淑媚一直很享受被他緊緊摟抱的感覺,雖然已經是頗有名氣的歌手,可是,在內心裡,她還是一個鄉下的小女孩,能夠有個掌握大權的控制者與她為伴,讓她感到非常安全地受到保護。而且,每當想起自己是羅大任的親密愛人,又能替他保守這麼重大的秘密,林淑媚就更加陶醉了。
像一朵美麗的花朵為他綻放,每一次的溫存都讓她喘不過氣來。激情過後,羅大任為她在胸前佩掛一條璀璨的鑽石項鍊。不同於剛才,他的手輕柔如微風,繞過她的頸部,碰觸到她背部赤裸的肌膚,讓她忍不住甜蜜地瑟縮向他的懷抱。
「這個禮物好美,有人說鑽石代表完美和永恆。」林淑媚滿足地用左手輕輕撫摸著項鍊,臉頰貼著羅大任的胸膛。
「不,完美和永恆是無法用金錢買賣的。我們擁有的只是它的瑕疵和脆弱,所以才需要非常小心去呵護。」羅大任笑著說。
「我不懂你說的。可是,你一定會來參加我的演唱會吧?」她抬頭望著羅大任,精緻小巧的鼻子任性地微微上揚。
「不一定,你知道我很忙。還有,聽說妳的演唱會的預售票都是秒殺,除非和妳有特殊交情,否則很難買得到。全場客滿的聽眾,又不差我一個人。」
「重要的是,文化部是不是終於核准了?」他低頭故意這麼問,其實他早已知道。
「是的,多虧有你幫忙。如果沒有你,文化部那些人根本不准舉辦台語歌曲演唱會。」她滿懷感激的說。
「文化部不是經常說『台語就是閩南話』嗎?我只不過是套用相同的說法來提醒他們。語言其實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沒有必要太多意識型態。雖然音樂和政治有時會搞在一起,但現在文化部正在試圖提升開明的形象,准許妳這麼出名的歌手舉辦閩南語歌曲演唱會,對他們一定會有正面的幫助。」他輕鬆地說。
「可是,他們堅持演唱的曲目,一定要事先送審。」林淑媚還是忍不住抱怨。
羅大任不想跟她多說,有這麼多的歌可以唱,為什麼一定要跟文化部過意不去?林淑媚根本不曉得為了她的演唱會,他對文化部施加了多少壓力。羅大任也知道她只是喜歡唱歌而已,早在一年半前,兩人才剛認識的時候,他深受林淑媚樸素勤奮的鄉村氣質吸引,當時她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歌手,為了生活到處兼差獻唱,根本沒有人會料到,有朝一日,她不但被閩南語歌曲大師蔡啟村發掘,如今,在經紀公司專業團隊的協助之下,她很快成為媒體寵兒,而且名利雙收,儼然閩南語歌壇的天后。羅大任以為,兩個禮拜後在高雄,以林淑媚的號召力,加上這是幾年來唯一的閩南語歌曲演唱會,可以預料,到時候一定會吸引爆滿的票房。不管如何,羅大任還是為她感到很高興,儘管他也認為,這些全都是她的經紀人賺錢的主意。
起身離開林淑媚的身邊,披上外衣,他走到落地窗前面,俯瞰遠處清晰可見的台北特區行政公署。相較起來,他一直認為北京才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不只是因為它擁有許多宏偉的古蹟,也不是由於它承受了千百年,從西北大漠席捲而來的沙塵暴,仍然屹立至今,而是因為千秋萬世,北京從來不曾掩飾企圖睥睨全中國的雄心壯志。至於台北,眼前這棟一九一八年竣工的後文藝復興形式的建築,華麗無比,它前面的廣場,雖然也曾人聲鼎沸鑼鼓喧天,但終究只是為過往政權煙火燦爛而已。不論被叫做總督府或行政長官公署,甚至也曾被榮耀尊稱為總統府,但在台灣,任誰都知道,身居其中的歷屆總統,有多少人的記憶裡竟然只有北京,而內心完全遺忘了台北。
「這個島嶼的居民早已失去夢想,讓她唱幾首歌又能怎樣?」羅大任心裡十分感慨。
事實上,對於這塊土地和人民,他再熟悉不過了。在台灣出生,直到十九歲之前,踢足球、泡網咖、追女友,他的人生年少青春都是在這裡度過,像他的閩南話就完全學自母親,母親也告訴過他,其實她身份證的籍貫欄是在嫁給父親之後,才從台灣被改成河北。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總統大選二度挫敗之後,父親開始處理家產整理行囊,「離家六十年,老了,我想要回去了。你母親也早就不在了,命運讓我偶然來到這個島,但這裡從來不是我的家,我再也不想留下來。」父親這樣告訴他:「你是我在台灣唯一的親人,一定要跟我回老家去看看。中國將來會越來越富強,世界會對它刮目相看,別留在這裡變成小台灣人。作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你會更有出息。」
他從未告訴父親,離開台灣的那天晚上,轉身鎖上台北的家門,他是多麼心酸徬徨,他也從未詢問父親,海峽兩岸,那裡才是真正的傷心地。到了中國,考上北大政治系,在中國的第一學府裡,他發覺,即使是最開明的教授和最嚮往民主的學生,也毫無妥協地主張台灣屬於中國。後來,他被國安局總部吸收,接受特訓,當時的主任朱龍就是這樣告訴他:「今天的中國,最不能忍受要不回來的領土,不是外蒙古,不是海參威,而是位在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台灣。」
父親終於得償宿願,落葉歸根中國。而中南海,則因為他有從台灣移植過來的根,特別挑選了他。
祖國需要這個位於東南海域邊疆的島嶼,風平浪靜。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蘇培源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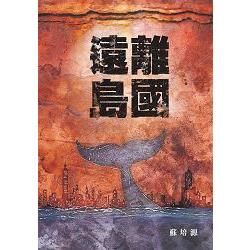 |
$ 59 ~ 270 | 遠離島國【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蘇培源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6-0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255頁/15*21cm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遠離島國
假如台灣被中國統一了,會是什麼樣子?
在機場混亂之際,長年被禁止入境、寓居在美的「黑名單」──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李映元,成功穿越了重重的關卡,重新踏上台灣土地。然而此時台灣已不再是台灣,在國共的攜手合作之下,台灣島終於在中日爆發釣魚台戰爭的騷動中被共軍溫和入侵,回歸祖國的懷抱。
在由中共決定近半數候選人的立委選舉投票之前,李映元展開了在自己土地上的流亡,以及對中共的宣戰。面對過去同為理想奮鬥,如今卻熱情不再的人們,以及同樣生於台灣土地、卻對台灣未來有著截然不同想像的人們,李映元將掀起什麼樣的政治風暴?中共擘畫大膽的「分割計劃」即將實現,台灣又將走向何方?
這是一部預設中國將會併吞台灣的小說,在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現實之中,揉雜殷鑑不遠的香港經驗,虛構了極其寫實的統一預言。在強權的侵逼之下,台灣如何自尋出路?島嶼人民該怎麼扛起建立國家的巨石,尋找屬於自己的答案?
為這個島嶼掀開歷史與認同的迷霧,是歷史的必然,也將是台灣未來的風景。
作者簡介:
蘇培源,台灣高雄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於圓山飯店參與民進黨創黨,民進黨籍國大代表,外科專科醫師。
章節試閱
闖關
霧鎖機場。
李映元搭乘的世界航空AX111客機,已經在台灣上空盤旋將近半個鐘頭,根據管制塔台傳來的消息,今天早上忽然升起一大片濃霧,籠罩桃園機場附近的區域,地面的能見度不到三百公尺,那是台灣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大霧。因為這個原因,除了AX111客機之外,還有十幾架飛機也在空中滯留,等待降落。
飛機平穩地翱翔著。閉上眼睛,李映元靠在座位的椅背上,想像著飛機破雲而出,就會有一座美麗島映入眼簾,如同一顆翠綠的寶石,閃耀在湛藍的太平洋西岸,多少年來,這種景象早已在他的腦海裡一再浮現。而由於他並不是那種故意不回...
霧鎖機場。
李映元搭乘的世界航空AX111客機,已經在台灣上空盤旋將近半個鐘頭,根據管制塔台傳來的消息,今天早上忽然升起一大片濃霧,籠罩桃園機場附近的區域,地面的能見度不到三百公尺,那是台灣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大霧。因為這個原因,除了AX111客機之外,還有十幾架飛機也在空中滯留,等待降落。
飛機平穩地翱翔著。閉上眼睛,李映元靠在座位的椅背上,想像著飛機破雲而出,就會有一座美麗島映入眼簾,如同一顆翠綠的寶石,閃耀在湛藍的太平洋西岸,多少年來,這種景象早已在他的腦海裡一再浮現。而由於他並不是那種故意不回...
»看全部
作者序
前言
這是一部預設中國將會併吞台灣的小說。在書中,我一直無法肯定台灣被統一的確實時間,它也許迫在眉睫,或許必將來到,也可能不會被實現。至於我自己,我深深瞭解,之所以在腦海裡遍尋不著那個關鍵的年代,是因為在靈魂深處,我寧願它永遠不會發生,所以,我選擇將它遺忘。
我只希望中國儘快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能對人類社會做出最正面的貢獻,成為一個真正受世人尊敬的大國。
有許多朋友一直認為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相反地,我認為中國才是一個最不正常的國家。在這個地球上,十三億人口能夠創造出那樣的一個國家,被那樣的...
這是一部預設中國將會併吞台灣的小說。在書中,我一直無法肯定台灣被統一的確實時間,它也許迫在眉睫,或許必將來到,也可能不會被實現。至於我自己,我深深瞭解,之所以在腦海裡遍尋不著那個關鍵的年代,是因為在靈魂深處,我寧願它永遠不會發生,所以,我選擇將它遺忘。
我只希望中國儘快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能對人類社會做出最正面的貢獻,成為一個真正受世人尊敬的大國。
有許多朋友一直認為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相反地,我認為中國才是一個最不正常的國家。在這個地球上,十三億人口能夠創造出那樣的一個國家,被那樣的...
»看全部
目錄
前言
闖關
俯瞰舊時總統府
西子灣的浪濤聲
美麗島站的祈禱之手
安全網出現缺口
拒絕被迫簽署聲明
回家
往島國之南祭父
報導真相
打擊樂也要非常中國
堅持報人風骨
民進黨內部的矛盾
發傳單被追趕
英雄無懼現身
女警長興師問罪
司機被捕
探病
被刑求審問
在教堂重逢
北京的通牒
被迫辭職
海灣俱樂部的演唱會
將軍帶來分割的計劃
車禍
炸彈攻擊
火燒投票所
敗選
大膽的提議
沒有歷史圖像的台灣
進入國安局總部
麗華酒店
晚宴
殺戮戰場
白鷺鷥翩翩飛起
飢餓絕食
建國的巨石
台獨幻夢
後記
闖關
俯瞰舊時總統府
西子灣的浪濤聲
美麗島站的祈禱之手
安全網出現缺口
拒絕被迫簽署聲明
回家
往島國之南祭父
報導真相
打擊樂也要非常中國
堅持報人風骨
民進黨內部的矛盾
發傳單被追趕
英雄無懼現身
女警長興師問罪
司機被捕
探病
被刑求審問
在教堂重逢
北京的通牒
被迫辭職
海灣俱樂部的演唱會
將軍帶來分割的計劃
車禍
炸彈攻擊
火燒投票所
敗選
大膽的提議
沒有歷史圖像的台灣
進入國安局總部
麗華酒店
晚宴
殺戮戰場
白鷺鷥翩翩飛起
飢餓絕食
建國的巨石
台獨幻夢
後記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蘇培源
- 出版社: 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6-01 ISBN/ISSN:978957801770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