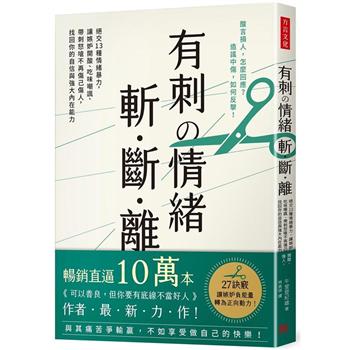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序言
我是二○一六年退休的,孩子已大,各有他們的天下,我閒著無事,與友人相約回到闊別多年的臺灣,參加老同學的姐姐、姐夫在臺東主持的巡迴兒童義工服務。在東臺灣漫漫的車程中,友人提到了二二八、提到臺北有個國立紀念館,想到父親二二八時是位憲兵營長,駐防臺南,是這歷史的一部分,回臺北後我特地走訪了這個在南海路植物園斜對面的紀念館。偌大的館內看不盡的是臺籍青年受難者的照片與他們不幸遭遇的陳述,站在這無比肅殺與悲哀的展館中,我錯愕地想,這是二二八全面的真相嗎?小時候曾聽過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救過一些人,這部分的歷史去了哪裡?
帶著這個疑問,我回到了洛杉磯年邁的母親身邊,在她的舊物中我找到了父親多年前為協助編纂憲兵史所留下的一份手稿。這份稿子我曾聽姊姊說過,但還是第一次見到。在短短的卅多頁中,我讀到了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從動亂開始到結束,前後幾天所經歷的事情,我驚訝地知道事件當時臺南情況的緊繃,也才瞭解到臺南在遭到波及後,「不擴大、少流血」,讓事件盡可能和平結束,這一路走來的不易。在舉世滔滔的今天,我與家人們覺得父親這段塵封往事有值得重溫的價值。因為在他娓娓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一位中級軍官本著良知,和臺南士紳合作,與政府援軍溝通,讓事件在臺南盡可能的平靜落幕;我們看到一群立場不同的人,他們秉持良知,凝聚善念(以眾生為念),求同存異,得到善果的故事。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冤情少有發生,冤冤相報的桎梏沒有落在後人身上,他們的事蹟值得我們後人知道、效法。
父親與臺灣結緣說來是有些偶然的,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軍投降,父親時任駐防福建的憲兵第四團第一營營長,憲四團以地緣之故,奉命接收臺灣,原定派遣赴臺的第三營營長失言,團長高維民臨時改派原定留駐福建的第一營赴臺,父親因此在同年十月率部渡海,抵達了臺灣,以臺南市為營本部所在,負責縱貫鐵路沿線秩序維護、南部及東部地區(包括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蘇澳、花蓮、臺東)戰俘遣返、日軍物資接收、國軍軍紀糾察、與警察維安協助。那年父親四十歲。
我們對父親在臺南的生活所知不多,但小時聽過父親撥軍糧支援缺糧的臺南監獄,讓繫獄的人免於飢餓,父老感念此事,將憲兵隊前的街道改名為「衛民街」。小時也聽過二二八時,有位父親的民間友人將父親寫的密函藏在他穿的日式叉腳鞋內帶出營區(母親回憶這位張姓友人在父親過世後,遠從南部來臺北,在公祭時下跪悼念父親,他們友誼的厚重可見一斑)。父親不諳閩南語,我們問母親,這有造成溝通上的問題嗎?母親說應該沒有,她說那時不少地方士紳會說普通話,憲四團又是從福建調過來的,許多士兵是福建籍,通曉閩南語,父親屬下還有好幾位士兵是東南亞華僑子弟,通曉閩南語、日語、英語,父親若需要傳譯不是困難。
我們現在回頭看,父親與臺南地方父老之間互動應是愉快的,這平時建立起來的感情應該是他在二二八時能與溫和派士紳取得共識、攜手合作的重要關鍵。手稿寫到有一天十幾位參議員來營,要求父親停止巡邏並交出營區內所收容的外省人士,父親堅拒,會談幾近破裂,最後父親聲淚俱下,數位參議員受感動也唏噓落淚,答應回去勸導青年學生,要他們不要衝動莽進,又隨後送來白米與鮮蘿蔔致意。手稿也寫到,參議員後來兩度來營,先是請父親協助,與已避居城外守軍處的市長見面,達成事件處理原則協議,後來又來營商談恢復市面秩序問題,接受了父親的建議,由徒手憲兵二十多名,每名偕同一位參議員為一組,併肩步行全市各街巷,逢人宣導,不到兩小時,臺南市面秩序就開始恢復了,營區內收容的外省人士也在第二天市長與參議員一同向市民廣播,市面恢復平靜後,陸續離營返家。
父親收容外省人士,暫居憲兵營區是有實際需要的。二二八事件從單純的取締私煙演變成民變,並迅速遍及全島,那時大陸來臺的除軍人外,還有很多公務人員與教師,他們手無寸鐵,成為激進民眾毆打、傷害的對象(我的公公婆婆那時在嘉義女中任教,有人提著武士刀到學校抓外省人,幸有學生大叫「他們是老師」,才得免受傷害,但仍被集中拘留,以飯糰沾鹽巴渡日,到政府軍抵達才獲釋)。父親應該是預先有想到這個可能,所以在事起第二天就與南市軍警首長達成協議,保護、收容大陸來臺人士。手稿寫到那時來營區「避難」的先後約有兩百人左右,包括協助接收的行政官員,如市長、警察局長、地方法院院長、地檢處首席檢察官,及部分警察、鹽務總局與其他機構的職員和眷屬。
我們現在回頭看,父親的「先見之明」與他幼年時遭遇到的家變應該是很有關係的。手稿中提到父親的母舅因響應孫中山先生二次革命討袁,在家鄉湖南臨武縣起義,殺知事(縣長)及其手下七十餘人,事敗逃亡,後被捕,遭湖南都督(省長)判殺,族戚三百多人受株連。家袓母為助弟弟逃亡,匆促典賣田產,家道中落。翌年,祖父病逝,祖母被迫改嫁,父親與弟妹三人失怙恃,依偏房曾祖母為生。我們覺得母舅慘案與二二八事件有雷同之處,父親的母舅現在看來是位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進份子」,他不分青紅皂白殺了七十餘位北洋政府人員,導致北洋政府也不分青紅皂白殺了他的族戚三百餘人。父親時年十歲,受此牽連,家道貧乏,無力升學,我們現在看來父親是「受難人家屬」。父親顯然深記著這個慘案的教訓,知道民變時,激進的民眾有可能遷怒、動手加害政府首長及員工,所以父親在亂起之初就力勸市長暫宿營部,並陸續收容大陸來臺人士,致二二八期間南市的外省人除二十餘位遭到毆打外,並無其他傷亡。
母舅的慘案也讓父親知道政府在鎮壓民變時有可能會報復、殺害無辜平民,所以在幾天後政府援軍抵達時,父親親自出城迎接,面告援軍指揮官臺南市面秩序已恢復,請他們以「和平態勢」進入市區。兩位指揮官,一位同意,一位大不以為然,主張以「攻擊前進」。父親以臺南已恢復平靜,力陳利害,並以生命擔保,援軍才同意依父親主張,由憲兵前導,和平入城,避免了不必要的傷亡。
與全島各地相比,臺南在二二八事件中算是情形緩和的一個地區,但從父親的手稿中我們可以看出臺南當時其實是暗流洶湧,事件能平靜落幕是天佑、是一群立場有別的人合作起來的結果,這群人包括手稿中提到的參議員許丙丁、陳天順,援軍指揮楊俊,還有手稿中沒有特別寫出名字的人士。父親有緣在促成這場合作上盡到心力,但能讓事件平靜落幕實在是天佑、是眾人同心的結果。說到「天佑」,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拒馬的安置。手稿提到父親責令屬下趕工完成大批拒馬,在拒馬安置好不到一小時,逾千民眾分三路向憲兵營快速集結而來,其中至少有一路是攜帶著武器的。設若當時拒馬沒有安置好,民眾衝入了營區,格鬥恐怕難免,事件和平落幕的希望可能也就沒有了。
二二八發生在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民眾因對政府不滿而走上街頭,政府採取武力應對,造成平民大量傷亡,這固然是政府嚴重的錯失,但政府那時為什麼要調派軍隊來臺鎮壓呢?我們現在回頭看,事件當時部分民眾過於激進是重要原因,他們搶奪軍警槍枝彈藥,與守軍發生武裝衝突(譬如臺中、嘉義),且民眾中混雜有共黨份子(譬如臺中謝雪紅),這讓正為國共內戰焦頭爛額的政府認定事件有叛國及奪取政權的陰謀,所以選擇使用武力,調兵來臺。換句話說,政府選擇以暴止暴,這不幸的決定後來在心存私念的各方派系角力下,演變成濫捕濫殺,深化了冤冤相報,以致二二八的悲情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仍舊未能昇華。
往者已矣,未來不可知,但世間事其實多是互為因果的,我們在無法預知未來的情況下,只有秉承為善的信念,低頭做我們該做的事,諸如將父親這段湮沒的往事保存下來,為後人留下一個和平的見證,讓後人看到秉持良知、凝聚善念、求同存異的重要,因而心生效法,共創臺灣未來。
父親的手稿以職業軍人的角度著筆,他的遣詞用字有其時空背景,未必盡合當今語彙,尚祈讀者體會瞭解。此外,父親逃難來臺,孓然一身,除了重要身分證件及簡單衣物,什麼都沒帶,手稿全憑記憶寫於事件後十七年,錯漏難免,也祈讀者見諒。
本書的出版承蒙友人轉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林孝庭博士,再由林博士轉薦喆閎人文工作室楊善堯教授、歷史作家廖彥博先生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蘇聖雄教授,對此因緣我們有無盡的感恩與謝意,謹此為記。
家屬代表廖雲門於美國加州旅次
二○二○年九月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蘇聖雄導讀的圖書 |
 |
$ 276 ~ 333 | 另一個視角下的二二八︰廖駿業營長南市手記
作者:廖駿業原著、楊善堯主編、蘇聖雄導讀 出版社:喆閎人文工作室 出版日期:2023-11-17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另一個視角下的二二八︰廖駿業營長南市手記
本書是二二八事件時,駐防臺南市的憲兵第四團第一營營長廖駿業中校所撰寫的親歷回憶。
臺南二二八事件平息後,廖駿業先生曾撰萬餘字報告呈交團部,對於事態發生、應對措施留有深刻記憶。因此在事隔十多年後(一九六三),為配合憲兵司令部編纂憲兵史時,廖氏仍能夠鉅細靡遺寫下二二八事件時的親身經歷。
由於廖駿業先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為臺南市國軍部隊指揮官,因此在事件爆發後,迅即成為各方交涉接洽之輻軸,實際處在風暴之中心,參與各關鍵場面。再者,作者為憲兵營長,因此本書亦不同於此前地方仕紳、市府官員所撰回憶文字,使吾人得以從軍事角度,呈現完全不同的觀察面向。
作者簡介:
作者廖駿業先生,湖南臨武縣人氏,十歲喪父,家道中落,然而勤奮力學,於小學擔任教員。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冬,廖氏因受國民革命風潮鼓舞,前往廣州投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憲兵團,此後由二等兵做起,勤奮吃苦,意志堅定,屢歷戰陣,先後參與北伐、抗戰諸役,至勝利後,受訓積功,升為中校營長,奉命率部調往臺灣,駐防臺南,因而親歷二二八事件。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調升憲兵十三團副團長,離開服務二十一年的憲四團,前往雲南昆明服務,隔年四月,以身體久病不癒,離開滇省,七月請長假歸湖南故里,本擬略作休養,然大陸變色,縣城陷共,於是倉促離鄉,於兵荒馬亂之中,選擇再度來臺。廖氏來臺後,短暫服務於警界,曾任臺北縣警察局海山分局分局長,之後承駐防臺南時臺籍舊識之助,受聘臺灣省總工會,服務二十餘年,以迄退休。民國六十九(一九八○)年七月,廖氏病逝於臺北,享年七十五歲。
作者序
▍序言
我是二○一六年退休的,孩子已大,各有他們的天下,我閒著無事,與友人相約回到闊別多年的臺灣,參加老同學的姐姐、姐夫在臺東主持的巡迴兒童義工服務。在東臺灣漫漫的車程中,友人提到了二二八、提到臺北有個國立紀念館,想到父親二二八時是位憲兵營長,駐防臺南,是這歷史的一部分,回臺北後我特地走訪了這個在南海路植物園斜對面的紀念館。偌大的館內看不盡的是臺籍青年受難者的照片與他們不幸遭遇的陳述,站在這無比肅殺與悲哀的展館中,我錯愕地想,這是二二八全面的真相嗎?小時候曾聽過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救過一些人...
我是二○一六年退休的,孩子已大,各有他們的天下,我閒著無事,與友人相約回到闊別多年的臺灣,參加老同學的姐姐、姐夫在臺東主持的巡迴兒童義工服務。在東臺灣漫漫的車程中,友人提到了二二八、提到臺北有個國立紀念館,想到父親二二八時是位憲兵營長,駐防臺南,是這歷史的一部分,回臺北後我特地走訪了這個在南海路植物園斜對面的紀念館。偌大的館內看不盡的是臺籍青年受難者的照片與他們不幸遭遇的陳述,站在這無比肅殺與悲哀的展館中,我錯愕地想,這是二二八全面的真相嗎?小時候曾聽過父親二二八時在臺南救過一些人...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廖雲門
序言/廖彥博
導讀/蘇聖雄
手記/廖駿業
自傳/廖駿業
年表/廖雲門
後記/我們所知道的父親
後記/父親與憲兵
序言/廖彥博
導讀/蘇聖雄
手記/廖駿業
自傳/廖駿業
年表/廖雲門
後記/我們所知道的父親
後記/父親與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