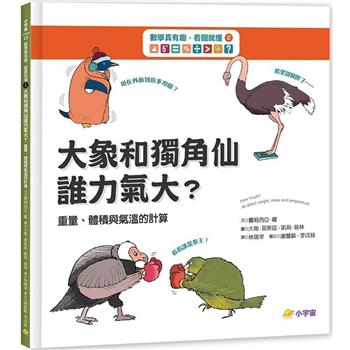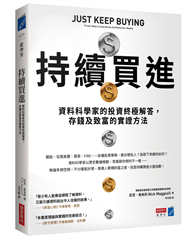《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新聞日報》三大報社年度最佳好書。
有外遇的人,請全部起立。幻想過外遇但還沒付諸實行的,也請起立。
扮演第三者還有被戴綠帽的老公、忍氣吞聲的老婆,也請起立。
還有誰是坐著的嗎?蘿拉‧吉普妮斯以十足挑釁又充滿幽默感的開場,為的就是要質疑從來沒人反對過的世界最大黨——「愛情」。愛,這神秘又強大的力量,每個人都想要得到它、都願意服從它,沒有人願意過著沒有愛情的生活(那多悲慘啊!),更沒有人質疑過愛情的偉大。妳不覺得這很奇怪嗎?任何偉大的信仰都有反抗異端,唯獨「愛情」萬民同聲,沒人挑戰過它,還心悅誠服地受它奴役。
愛情對我們的要求,除了忠貞之外,還必須用心經營。「經營你的感情」是我們早已接受的親密關係格言,表現良好並且費心討好對方(如同討好上司)、在性交中努力達到高潮(假裝的也行),才能換來幸福的青鳥。倘若如此地勞心又勞力,上班下班又有什麼區別?我們都是在做雙倍的超時工作。從這個角度,我們的親密關係不就是另外一份無給薪、只提供員工宿舍的工作?
《反對愛情》從透徹地檢查「外遇」的意義開始,在這個以愛為中心旋轉,卻充滿大量矛盾和焦慮的世界裡,觀察並質疑愛情的真正面貌,帶領我們探索一對一關係的規定和戒律(包括訂定宵禁和尋人抓猴),並且追溯在這些規定背後、操縱妳我行為的愛情神聖權威。
請坐下,並且繫好安全帶,因為《反對愛情》將會在妳的舒服座位下(或是床底下)點燃小小的火藥裝置,妳不會受傷(嗯,不會有嚴重傷害),只是要小心,妳放在掌心、百般呵護的愛情,別被震落了。
作者簡介:
蘿拉‧吉普妮斯(Laura Kipnis)
美國西北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教授,也是文化及媒體批評家,談論領域包括性別議題和當代文化。曾於2007年來台參加第七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的題目是「色情無價」。著有The Female Thing: Dirt, Sex, Envy, Vulnerability (2006),Against Love: A Polemic (2003),Bound and Gagged: Pornography and the Politics of Fantasy in America (1996)。
譯者簡介:
李根芳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所長。譯有《勘誤表》(行人)、《X世代的價值觀》(天下文化)、《神奇百憂解 ――改變性格的好幫手》(張老師文化,與陳儀莊合譯)、《無上司企業――以自我管理團隊建立高績效公司》、《領導趨勢:廿一世紀管理風格的變更》(以上由遠流出版)、《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巨流圖書,與周素鳳合譯)、《文化理論辭彙》(巨流圖書,與王志弘合譯)。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台大外文系教授 張小虹、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作家袁瓊瓊,叫好推薦。
「辛辣又令人著迷……極其有趣……以散文的犀利筆鋒,表達對婚姻迷思的精彩控訴,以及對不忠的讚揚。」《紐約客》
「該是時候有人跳出來戳破我們對愛情和兩人關係的理想主義想像了。」《紐約郵報》
「如果你認為『家庭價值』不僅僅是愛你的家人,還包括更重要、更好的東西,請避開這本書,以免讀到中風。」《華盛頓郵報》
「吉普妮斯的論述讀起來就像辛辣又脫俗的小說,敘說一樁不忠外遇的開始、中途和結束。」《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若要一個人不享受吉普妮斯帶來的震撼,大概要有一顆鐵石心腸……有趣又精明……論述有力且有根據。」《芝加哥論壇報》
「令人驚奇地慧黠,美妙的筆鋒……吉普妮斯結合記者的活力和哲學家的腦袋……無論你是否同意,吉普妮斯的論證方式讓《反對愛情》充滿震撼,同時也令人捧腹大笑……就算是最幸福的已婚者,也會喜歡這本書的挑釁味道。」《費城詢問報》
「以刀鋒般銳利的智慧和逗趣的諷刺筆調,吉普妮斯將一夫一妻制的浪漫迷思完全打破。」《出版者週刊》
媒體推薦:台大外文系教授 張小虹、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作家袁瓊瓊,叫好推薦。
「辛辣又令人著迷……極其有趣……以散文的犀利筆鋒,表達對婚姻迷思的精彩控訴,以及對不忠的讚揚。」《紐約客》
「該是時候有人跳出來戳破我們對愛情和兩人關係的理想主義想像了。」《紐約郵報》
「如果你認為『家庭價值』不僅僅是愛你的家人,還包括更重要、更好的東西,請避開這本書,以免讀到中風。」《華盛頓郵報》
「吉普妮斯的論述讀起來就像辛辣又脫俗的小說,敘說一樁不忠外遇的開始、中途和結束。」《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若要一個人...
章節試閱
譯序
七○年代的偶像明星劉文正有一首歌,就叫〈愛情〉,歌詞並不長,卻道盡了愛情撲朔迷離,令人難以捉摸的特性。披著白圍巾、身高接近180的劉文正唱著:「若我說我愛你,這就是欺騙了你, 若我說我不愛你,這又是違背我心意。」究竟什麼是愛情?誰敢反對愛情?就像是本書作者蘿拉.吉普妮斯所述,愛情可是個頣指氣使的老大,它要我們忠誠不二,我們就不敢輕易違反造次;在愛情面前,人人成了小老百姓,臣服於位高權重的帝王,受其擺佈;或是像簽了約的奴僕,任其使喚。
然而,在一切都被解構、凡事皆受挑戰的時代裡,為什麼獨獨「愛情」能繼續霸佔寶座?何以一夫一妻的專偶制度永遠受到眾人膜拜?無論是中外影視圈、台灣政壇,或是全球體育新聞,只要有人膽敢違禁,事必受到各方圍剿追殺,因此無論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時的意亂情迷」,或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當事人總要出面道歉,向社會大眾坦白認錯。或是原本形象完美的居家好男人,突然間各種代言皆被封殺,銷聲匿跡「閉門思過」,甚且得用天價來挽救一切。
但是,類似的戲碼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我們知道,只要專偶制度存在,這齣戲就一定會繼續上演。
蘿拉.吉普妮斯強調,本書所分析的專偶制度,未必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隨著同性婚姻漸受法律承認,書中援引的例子可能也適用於同志婚姻。她的重點在於專偶制,特別是「真愛永恆專偶制」的神話。這樣的神話在近世似乎成了顛破不滅的真理,若有人膽敢質疑,恐怕會立刻讓人貼上「反社會」的標籤吧。
然而,成為專偶制度的信徒才是真正的「愛」的追隨者嗎?有沒有可能這其實是打著「真愛」名號,從事種種違反真愛的行徑呢?這是吉普妮斯以悖論的角度,要讀者跟著她一起深思的問題。
我覺得全書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在於,她藉由批判理論來檢視現代親密關係與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相通性,她指出:「我們不可能拒絕愛,正是因為現代人被形塑成是渴求被滿足的存在,期望與人連繫,需要愛人和被愛,因為愛好比血液裡重要的原生質,世界上其他一切充其量只是白開水。」這樣一種對愛的信念與堅持,和現代工業社會強調效率、工作倫理,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她援用了傅柯「規訓」的概念,強調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利用「圓形監獄」的邏輯,將專偶制「愛情」歌頌包裝成至高無上的美德與幸福,因此家國機器不需要處處站崗、時時設防,卻能達到無時無刻不在監督人民的目的。我們對於工作上的表現、和親密伴侶之間的關係,都可以「努力」來達成希冀的目標,如果表現不盡如意、關係不盡美好,那就是我們努力不夠。
除了國家對婚姻關係的規範制約、工作場所對專偶制的獎「善」懲「惡」,在在鞏固這套意識形態之外,現代美國社會也透過各種兩性關係暢銷書、心理諮商,甚至是脫口秀節目,對人們進行監督與輔導,這便串連成個經濟的生產消費錬,一切都可以在拼裝線上完成。「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這些崇高的目標,就在「努力」之中得以實現。
然而,這樣的邏輯是否是為了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而服務呢?事實上,當代社會學家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貝克夫婦(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都分別探討了現代社會結構的改變,已急遽地影響現代家庭結構,也挑戰了我們傳統以來對親密關係的定義與了解。也許種種的踰越行徑,無非是挑戰僵化現況的革命行動,透過這些踰越,我們開始去探問,疆界從何而來?為誰所限?規範如何重寫?規則如何改訂?
這當然不是一本鼓吹婚外情的書,就如書名所示:Against Love,我的解讀是,專偶制度恐怕是以愛之名行反愛之實。既然是制度,自然有其生成的原因與捍衛的價值觀。就像是父權制度其來有自,但不見得是真理,前仆後繼的前人讓我們看到了爭取性別平等的成果,性別差異不該再成為限制就學或就業的理由,女性得以接受教育、發揮所長。
長期以來,專偶制度被奉為真理,但是劈腿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就像是攪亂一池春水的「雜質」,逼得我們不得不去誠實面對究竟這一切出了什麼問題?不可否認的是,人是社會動物,我們確實需要「相濡以沫」的陪伴,但是親密關係和「愛情」為什麼必須是一體的?若是追溯歷史演化,現代「專偶(婚姻)制度」其實是相當晚近的產物,我們卻被緊緊圈住,在其天羅地網下,幾乎無處遁逃(現在更有小報新聞、八卦媒體隨侍在側)。
從西方歷史觀之,古希臘文共有四個字來指涉英文的love,分別是eros,agape,philia,storge。Eros是激情的愛,往往有色慾的渴望;agape是對家人、配偶的愛,包含了尊重;philia和友愛相近,也可擴及群體;storge通常指的是父母對子女的情感,含有寵愛的意味。在現代的愛情神話裡,我們似乎要求對方要能給予這四種不同的愛,否則就是對方不夠愛自己的明證。雖然吉普妮斯講的是浪漫愛,但有時讀著讀著,我彷彿也看到許多父母對子女的愛的影子。
也許從這本書裡,我們可以從她的析論,看見自己也看見別人,在辛勤工作、努力求愛的同時,不妨停下來想想: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相信,真愛令人自由,不僅是自己,也包括對方。讀前須知
各位讀者,請繫好安全帶:我們即將遇到衝突矛盾的亂流。主題是愛,所以此行可能不太平順。
首先要問:有人會反對愛嗎?沒有。每個人都知道,愛是股神祕又強大的力量,控制著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愛是老大,而且是個嚴厲的老大:它要我們忠誠不二,我們也就甘願順從。像個小老百姓臣服於位高權重的帝王,受其擺佈;或是像簽了約的奴僕,任其使喚。這是新形式的大規模徵兵:我們絕無可能被愛徵召入伍,然後拒絕身體與心靈全面效忠。我們不可能拒絕愛,正是因為現代人被形塑成是渴求被滿足的存在,期望與人連繫,需要愛人和被愛,因為愛好比血液裡重要的原生質,世界上其他一切充其量只是白開水。我們在愛的大門前五體拜倒,急著想要進門,就像一心想出人頭地的人在某個會員專屬的俱樂部門外排隊等待,巴巴地想要進入裡面的時髦包廂,以確認自我基本價值,好讓我們覺得自己有趣迷人。
但是這全民一致的看法豈不是令人有些擔憂嗎?這是不是唯一一個沒有異議的主題,對於這個主題只有一個真相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即使是憤世嫉俗者和反浪漫主義者亦然,顯然他們才是不折不扣的真信徒)。想想最有影響力的組織宗教不時製造出狂熱份子,每種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變節者,即使是聖牛都會撞上要殺牠們的屠夫。只有愛萬民同尊。
所以非得有個論辨來挑戰它不可。論辨意在拿文化忠誠開刀,逆轉老生常談的智慧,即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主題如愛,也該拿來詰問一番。論辨作為一種散文形式,它的功用形同你安樂椅腳下小小的爆破裝置,不會傷害你(嗯,至少不是嚴重傷害);只是要攪動一池春水,動搖你的信念。請注意:論辨並未經過精心設計,所以不會面面俱到。重點在於誇大其辭,不時挑釁、偶爾嘲諷,因為論辨通常是要反駁某件事,由於面對的主題如此無可爭議又根深柢固,所以只能靠論辨對大家熟知的事最多戳個小洞罷了。現代愛情也許是個企業城──甚至還配有宿舍(亦稱為「家庭」),但是我們真的被社會擺佈到這種地步,順理成章地接受這些老掉牙的安排,而不提出半點疑問嗎?
請注意「悖」這個字也不止一個意義。論辨本身未必沒有矛盾(論辨者彼此也不是沒有歧見);修辭和情感並非一體雙生。所以,請抱著挑戰與質疑的精神來閱讀。這正是我們這個主題的本質。
緒論 (或者,「我剛好遇到了。」)
「你想跳個舞嗎?」你已經想過要儘可能聽起來很輕鬆隨意,並且很快地說服自己(自我欺騙在這種情況中並不是不常見),你的動機不過是像手上的黃金婚戒一樣純粹,你的美德就像房貸一樣永恆。這小小的冒進成功了,你的身體現在緊張地逼近這個人,整晚這人的目光一直意味深長地望著你,你慢慢意識到某種朦朧而似曾相識的情感在內心深處翻攪,遙遠的鼓聲愈逼愈近,就好像是一群大象在南非的灌木叢裡群聚……喔,天啊,這是你的性欲──曾經是著名的自由鬥士,現在則是可憐乾癟的小東西,從自信滿滿的非法之徒,搖身一變為模範公民,從詹妮斯.卓普琳(Janis Joplin)變成了巴利.曼尼諾夫(Barry Manilow),一切發生在短短幾十年間。所有狂野原初的欲求,成功地昇華成工作及家庭生活,所有效忠配偶的可用器官都成了夫妻共同財產(現在久久才會派上用場,執行了無新意的夫妻交流,伴隨而來的是──誠實面對吧──愈來愈萎靡的激情,愈來愈低落的性趣),你突然驚覺一直以來你是否失去了什麼。什麼時候「性」變得這麼無聊?什麼時候它竟變成了你要去「努力」的一件事?多尷尬啊!如果你不記得要炒飯,那麼你多久沒有炒飯了?相較那些過度演練的動作(或許「動作」比較能帶出機械式反應的感覺),還有什麼比一晚好眠更誘人呢?過去應該還不錯吧──如果回憶沒誤導的話──在那些冷言冷語出現之前,或失望,或小孩,或舊帳。
剩下的一群人則趁著假日,靠著免費酒,還有證明自己仍然能夠通宵達旦玩樂的渴望,和負責任公民笨拙地假裝成不在乎的放蕩者,任意舞動狂歡,不管第二天早上感覺可能有多糟(或許你來自學術圈,出席每年的學術年會,得以光明正大地暫時擺脫煩人的學生與用腦過度的生活──但是職業其實不重要,這可能是任何人的故事)。所以,這就是了,跟著節拍舞動(你希望如此),心中充滿著異樣的感覺。這是……快感嗎?好久沒有人對你有這種興趣了,不是嗎?各種身體的和心理的感覺,都隨著與對方的親密接觸而激動起來──家中那個不在身邊,可能是你阻止他來,或是他一開始根本就不感興趣,然後……
快別胡思亂想了。這些紛亂的念頭,那算得上是「思想」呢?。
或許不是派對的關係。或許是飛機,或是你的健身房,或者──對於那些比較喜歡當下的人──是工作。(努力想想:未來多年仍有許多難對付的遭遇等著你呢。)地點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情欲賁張地被丟到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情境,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可能有什麼事要發生了」的時刻。你覺得煥然一新,突然間自己變得很迷人,很有吸引力,從僵死的情感中甦醒過來,你以為早已不存在的欲望強烈地令你瞠目結舌。隨之而來的是第一通讓你神經兮兮的電話、喝個咖啡、小酌一杯的邀約,或者情況允許的話,一整晚聊不完的天。好久沒有人真的在聽你說話,被你的笑話逗笑,並且深深地看進你的眼底,讓你著迷。也好久沒有人讓你覺得自己迷人。你們倆「不小心」接觸到對方時,心裡和「那裡」同時有種急切渴望的刺痛,你突然意識到長久以來的空虛被填補了(或者你早已習慣用最尋常的舒緩劑來自我治療,譬如馬汀尼或百憂解等)。有時情況失控,嚴重到出乎你的意料,但這其實是你偷偷企盼的(好吧,迫不及待想要的),現在談的可是真感情了,風險也來了──你原來不打算放感情下去的,風險也令人膽戰心驚,你不應該經歷這些感受的,但同時卻又奇妙地覺得……是興奮振作嗎?
緊接著這種興奮之情是令人麻木的焦慮感及啃嚙人心的罪惡感,兩相交加彷彿點火即燃。你好像一直都在冒汗,而且是令人不快的、黏答答的汗。老天啊,這難道是疱疹嗎?你的胃也有毛病,你的良知就像是發炎的盲腸,讓你痛苦不堪,隨時要因為毒素和責怪而爆炸。奇怪的病毒似乎已潛入你平日正常的高效能免疫系統,滲透你的防衛機制,讓你脆弱不堪一擊,不時顫抖、莫名其妙地臉紅。你好像感染了危及生命的欲望病(你向來過著的生活受到了威脅,而且看起來像是欠缺了人生的重要成分,這空缺讓你醒著的每一刻都不得安寧)。你真的是做這種事的人嗎?這一切都尚未發生,這種自我折磨,正是因為你還沒有「做什麼」,但是你已經恨自己了。你決定和這個新發現的愛的對象談一談──優雅地退場。你痛苦地解釋:「我做不到,」但事實上,你明白,其實你可以。沒有任何可靠的統許數字計算出,從向對方說「我做不到」或是「這樣可能不太好」,到一段挑逗前戲開始,這之間平均時間到底有多長,不過社會語言學家倒是可以考慮調查這種語言特別的催情力量。無論如何,罪惡感本身就有舒解的效果,讓你確信自己其實真的不是壞人。壞人才不會有罪惡感。
或者……也許你已經有好幾次類似的經驗。或許甚至不止好幾次。或許你有自己一套衡量的邏輯,偶爾讓自己小小地脫離忠實的束縛,不要太認真,享受一下,不要誤導任何人,這樣才能真正地在大節上忠實,才能不顧一切地盡力維繫很久以前立下的盟誓。「一切」代表的是你原本無意做的妥協,或是種種傷害累積成你幾乎倒背如流的舊帳,或是愈來愈多次求愛被拒(每次拒絕都造成了細微而永久的創傷),或者──你自己填空吧。目前也都還好(上帝保佑),沒有什麼重大災難(雖然不時有緊張對峙,鬥嘴爭吵總免不了),畢竟你是個好人,坦誠正直,你無意傷害任何人,當然你也愛你的伴侶,或者至少是無法想像兩人分開(或者是分開後隨之而來的生活被破壞,焦慮及沒面子等問題),但是你需要──嗯,你需要什麼完全不是重點,當然也不是你想面對自己討論的問題(如果有孩子的話,最好等到孩子上大學,如果沒孩子的話,最好拖到以後再說),因為你何必自找麻煩,一旦攤開了談,可就再沒有回頭路,而你現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堆麻煩攤在眼前。你也不希望有人覺得你是混蛋或是自私的壞女人,或是聽到受威脅的社群出於道德譴責而罵的種種難聽話。
不管是什麼特別的原因,你現在置身於此,在違背這重大誡律之前,即將加入祕密的破壞婚姻地下集團(或是再犯,你這個壞蛋),這些悖離常規的欲望輕率地搗亂社會秩序。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者接下來會怎樣(對於上次的情境失憶症是必須的),但是你會儘可能讓自己感覺……活著。
而且……很有實驗性。私通之於循規蹈矩的愛情,就像是試管之於科學:實驗所須的必要容器。如此才能提出假設,隨機應變:「如果……?」或是展開概念的冒險,就像任何實驗一樣,也許這個想法根本就糟透了,也有可能是個神奇療法,令人脫胎換骨,也有可能是潛在的一發不可收拾。或者以上皆是。可能就此發明或理解了新鮮事:這也許是下個重大的典範轉移。或者只是小小的挫敗。但是你永遠不可能事先知道答案,不是嗎?
譯序
七○年代的偶像明星劉文正有一首歌,就叫〈愛情〉,歌詞並不長,卻道盡了愛情撲朔迷離,令人難以捉摸的特性。披著白圍巾、身高接近180的劉文正唱著:「若我說我愛你,這就是欺騙了你, 若我說我不愛你,這又是違背我心意。」究竟什麼是愛情?誰敢反對愛情?就像是本書作者蘿拉.吉普妮斯所述,愛情可是個頣指氣使的老大,它要我們忠誠不二,我們就不敢輕易違反造次;在愛情面前,人人成了小老百姓,臣服於位高權重的帝王,受其擺佈;或是像簽了約的奴僕,任其使喚。
然而,在一切都被解構、凡事皆受挑戰的時代裡,為什麼獨獨「愛情」...
目錄
譯序
讀前建議
續論
第一章 愛的勞動
第二章 家事集中營
第三章 愛的藝術
第四章 ……然後我們追求幸福
譯序
讀前建議
續論
第一章 愛的勞動
第二章 家事集中營
第三章 愛的藝術
第四章 ……然後我們追求幸福



 共
共  2011/09/14
2011/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