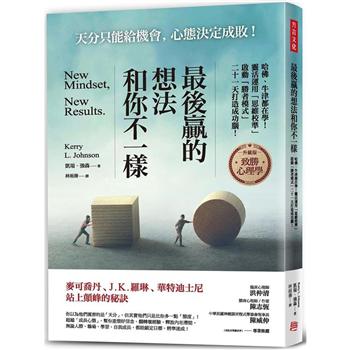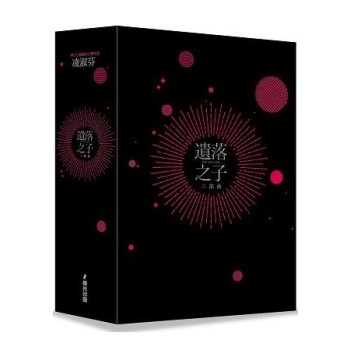厄瓜多高盧越野賽(Raid Gauloises Ecuador)
1998年9月
科多伯西火山(Cotopaxi Volcano)
海拔4,500公尺
那天大約是凌晨一點,我們在科多伯西火山海拔4,500公尺山腰處一間小屋裡待了四小時,依偎在一起,一邊休息一邊準備踏上最後1,500公尺的攻頂之路。我的隊友──羅伯特.那戈(Robert Nagle)、約翰.賀華德(John Howard)、伊恩.亞當森(Ian Adamson),以及史蒂夫.葛尼(Steve Gurney)──安穩地躺在我身旁打呼著。但是,自從我們踏入這間小屋後,我就不停地哭泣,無法自已。我哭,除了因為這是我唯一能補充氧氣的辦法,也因為我以為自己再繼續爬下去就必死無疑。
我們這支名為「所羅門─普里西度」(Salomon-Presidio)的隊伍,在海拔4,300公尺高處行進了三天,期間只睡了兩小時。而且,當我們拖著疲憊蹣跚的步履抵達轉換區時,雖然領先其他隊伍,但是法國隊緊追在後。我們抵達轉換區時,醫生和賽會主辦方已等候在那。他們看了我們一眼,便命令我們和法國隊都進入一間小屋躺下休息數小時,並要求我們在凌晨一點前都不准展開下一階段攻頂。看樣子很明顯,大家的情況都不妙。我們的身體狀況都不好,而且我是最糟的一個,不但氣若游絲,身體還因為缺氧而發青。我們即將攻上這座海拔高達6,000公尺的火山,從這裡登上頂峰,一般要花上一週的時間。這在越野賽史上算是最極限冒險的挑戰,也是一個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和想像的目標。這是一場費時九天、不眠不休的遠征探險競賽,第一階段的賽程是從海拔4,300公尺處開始,要在零下低溫的環境中行進120公里。此時,比賽才剛進行到一半。
為了安全起見,主辦方決定在我們展開下一階段攻頂之前,檢測所有選手的血液含氧量。如果有選手的含氧量低於70%,他們不但無法繼續,整個團隊還會被處以五小時的罰時。獲准繼續參賽的團隊在海拔5,500公尺處還有一個關卡,如果團隊中有任何選手無法闖過那個關卡,整個團隊不但會被處以兩小時的罰時,選手還必須像隻敗犬般,夾著尾巴垂頭喪氣地回到山下。無論如何,每一組團隊到最後至少要有三名選手留下繼續攻頂,否則整個團隊都會被淘汰。
所以,對我們而言,70%的含氧量就是一個決定成敗關鍵、甚至可能定生死的神奇數字。在現實生活中,我從事消防工作,也是個緊急醫療救護技術員,因此明白含氧量過低的危險。如果含氧量低於95%,表示身體已亮紅燈。如果含氧量已到80%,已經離鬼門關不遠了。含氧量一旦低於90%,就要緊急呼叫救護車送醫救治。如此看來,70%似乎可說是眾望所歸的評判標準。我從沒看過有人的含氧量低於70%還能站著(而且還在哭),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自己不可能低於70%。
醫生和賽會主辦方突然出現在小屋門口,帶著血氧監測儀,於是大家排好隊等著檢測。一個接著一個,每位選手都將食指伸入感應器,等待數秒後,醫生便宣布每位選手的檢測結果:「90%……88%……87%……92%……」每個人都通過了繼續參賽的資格。我排在最後一個,因為我很害怕。
醫生一面示意我上前,一面說:「如果妳低於70%,我們就不能讓妳繼續。」
我點點頭。取下手套時,我的雙手都在發抖。我伸出手指,讓他用儀器檢測我的含氧量。
約翰、羅伯特、伊恩和史蒂夫在一旁來回踱步著等待結果,而我依然在發抖。
「71%。」醫生一面宣布結果,一面搖著頭,他們沉默不語。監測儀上的數字閃閃發光,像是在大聲宣判:一旦離開這間屋子,妳可能就回不來了。這一生中,我從沒這麼害怕過。對於我這樣一個在平地長大的女生來說,這座山的海拔高度實在令人難以招架。我知道,跟全世界最厲害的團隊一起參加高地越野賽,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仍心存一絲自己有能力做到的希望。但現在,因為身體衰弱,我的希望幾乎要破滅了,儘管還是抱著一絲絲希望。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我的血液含氧量仍達71%。但是,這樣的身體狀況還能支撐多久?我自己都不太確定。
我看著隊友,希望他們有人會跳出來說:「嘿!這不值得冒險。妳就留在這溫暖的小屋裡,我們接受大會罰時五小時吧!」但是,沒有人出聲,只是默默地站著等我做決定。這些隊友都是我的英雄,他們都是體育界的傳奇人物。自從1994年開始涉足體育競賽以來,我就一直關注他們的生涯賽事。當我得知他們決定挑選我作為他們的指定女隊員時,我高興得從客廳的沙發上跳了起來,腦袋還撞到天花板。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是證明自我的機會。在選擇我作為隊員這件事情上,我要證明我的英雄做了正確的決定;而我也下定決心,絕不會讓他們失望。
我問他們:「各位,你們可以在我身上綁上繩子,把我拉到5,500公尺高處的關卡嗎?這樣,我們就只會被罰時兩小時。」
這就是我們想到的對策。這不是聰明的辦法,或甚至不是個好辦法,但是套句約翰說的:「至少這是個辦法。」確切地說,史蒂夫、約翰、伊恩和羅伯特要用登山繩索套住我的安全帶,拖著我這半死不活的身體,在科多伯西山腰處再爬高個1,000公尺,然後讓我獨自一人留在關卡。他們則繼續攻頂,如此才能保住參賽資格。
還沒反應過來時,我就已經全副武裝,準備踏上一場冰川之旅,就這樣朝著大雪紛飛的黑夜前進。由於我是全隊最虛弱的一個,所以被安排在隊伍中間的位置;如果我倒下,前後的隊友還是能竭盡全力,堅守各自崗位。當時,除了驚慌失措,我已不記得其他事情了。當你無法呼吸時,所有事情都變得更加恐慌。除了自己的身體不聽使喚、無法動彈之外,被迫完全放手依靠其他隊友,也令人感到害怕。我們花了整晚的時間攀越冰川,狂風暴雪中看不見道路,以蝸牛般的速度向上攀爬。當太陽升起、為科多伯西火山嶄新的一天揭開序幕時,我抬頭看到一群人在前方等著我們。
我們登上海拔5,500公尺處了。
抵達關卡時,我們五人全跪下了,我雙手掩面痛哭。這時,周圍颳起了陣陣旋風,像是吹起小型龍捲風,我的身體也禁不住地隨風搖晃。當時,我的內心只想著,到底要如何獨自一人下山。除了我,隊友們都要繼續攻頂,但我卻要被困在這半山腰,必須在一絲體力和一滴水都不剩的情況下獨自下山。我該怎麼辦?用屁股滑下山嗎?或是他們會幫忙推我一把,讓我用滾的下山?
這時,伊恩走向我:「妳準備好了嗎?」
「但我要怎麼下山?」問他的同時,我還在掩面哭泣。
「下山?噢,看來還沒有人告訴妳。妳要繼續攻頂,只有妳、我和史蒂夫三人。」
於是,我終於將我的雙手從臉上移開。就在剛才,我還想躲在雙手後面,以為這樣就可以逃離害怕和痛苦,以及自己正在一座活火山山腰上垂死掙扎的事實。我抬頭發現自己被一堆電視台攝影機包圍著,一個特大的黑色攝影鏡頭直逼我的臉,正在拍攝我聽到伊恩告知我消息後的反應。我試著不去理會攝影機,將注意力集中在伊恩身上,努力用缺氧的腦袋理解他剛剛說的話。還有,除了不由自主地發抖之外,似乎有其他東西在搖晃我的身體。接著,我感到有隻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那是羅伯特。
「醫生不准我和約翰繼續,因為我們有高地肺水腫之類的問題。」他臉色蒼白地說:「聽我說,妳必須繼續。妳可以辦到的,我知道妳可以做到。」
「我知道妳可以做到」。聽到這句話之前,我就只像個飽受驚嚇的聖地牙哥小女孩,只希望不要搞砸了整個團隊。但是,就在這生死一瞬間的時刻,當我看著羅伯特的眼睛聽到這一番話,也看到他確實相信我能為團隊攻上科多伯西火山頂峰,並且看到隊友們緩慢但有信心地點頭表示同意時,我已然是個世界越野賽冠軍了。全世界最棒的選手對我有信心,而且不是為了哄我開心才這麼說。隊友對我的信念,不僅當場改變了我的心境,也改變了我的身體狀況。他們的信念讓我脫胎換骨。一分鐘前,我才跪倒在雪地裡,低頭掩面哭泣;下一分鐘,我已是昂首望向山頂,頻頻點頭答應。
因為雙腳站不穩,我陷入雪地裡幾公分深,突然感到有雙手抓住我的手臂扶我一把。身旁仍有攝影機跟著我,拍下我的一舉一動。
「我可以做到。」我宣布。真的可以,就算當時雙手雙腳其實已經麻木了,就算已經出現肺炎初期症狀了。當時我已經發高燒達攝氏40度,還咳出軟綿綿、狀似拼圖的綠色異物,但我必須繼續。我會用攀山繩扣住安全帶,把自己和另外兩位隊友繫得牢牢的。我會戴好雪鏡,抓緊雪帽,攀登最後剩下的500公尺。這不僅僅是為了羅伯特和約翰,也為了那個被我扔在5,500公尺高處、飽受驚嚇的虛弱小女孩,還有我的團隊。
就這樣,史蒂夫、伊恩和我繼續攀爬。我們爬了又爬,每個人都專心一意、全心全意地攀爬著。我們側著身子,以交叉步伐的方式移動,這樣冰爪才能扣住被冰雪覆蓋的陡峭斜坡,步履維艱地以每分鐘十步的速度攀爬。我們每個人一手拿著破冰斧,另一手拿著登山杖,讓我們在雙腳逐漸不聽使喚時,還能藉助雙臂的力量繼續移動。伊恩幾乎是把我一路拖上山的,史蒂夫殿後。我努力將注意力集中在每一個蹣跚、艱難的步履,但同時還是會想到我的同伴。我不會讓他們失望,不會倒下,不會失敗,不會停下,也不會放棄。
我不允許自己抬頭往上看,害怕自己會因為看不到那遙不可及的山頭而感到失望。一次一腳步,一步又一步。但我想躺下!不行,妳不能……再一步……不能讓羅伯特和約翰失望。要堅強,但我不夠堅強。不,妳可以的。在內心交戰下,我不停地反覆告訴自己,只要再一步就好,但好像永遠走不完。從上午走到下午,還有更多山路要爬。眼前已是白茫茫一片,無邊無際。我的臉因脫水而發燙,耀眼的雪光也令人感到刺痛。加入全世界最棒的團隊,參加地球上最極限的越野賽,就像是置身天堂的同時,也承受著超乎想像的煉獄煎熬。這是比賽中的最後緊要關頭,也是選擇帶著什麼樣的心情歸營、度過餘生的一刻:是要凱旋而歸,還是抱憾終生。然而,這幾個小時下來,我還不知道答案。
幾乎要崩潰時,我仰望天空,不論是實質上、精神上或情緒上,都想要找到一個象徵一切都會好轉的徵兆,一個可以讓我活下去、結束痛苦的徵兆。就在那裡,在一片白茫茫的盡頭,是太陽,和一片漂亮的藍天,那是山頂。我還有好幾百公尺的崎嶇山路要爬,但我會做到的。隊友們相信我,我不能讓他們失望。他們無條件地信任我,在經歷三天不眠不休的賽程後,就是這股信念,將我推上安地斯山脈最高峰的頂端。
抵達海拔6,014公尺的關卡時,伊恩、史蒂夫和我互相搭著臂膀,圍成一個小圈圈為彼此加油打氣。在這無聲勝有聲的時刻,我們感謝著這趟令人心力交瘁的旅程,感謝著相信我們的朋友。一起站在世界頂端的這一刻,我們將會永生難忘。這時,我哭得更厲害了。
然後,我們轉身下山。畢竟,比賽還沒結束,還有400公里長的賽程要繼續。
接下來五天,我們繼續馬不停蹄地與法國隊互相較量,騎著越野車穿越厄瓜多叢林,在激流中泛舟、划艇,徒步跋涉到腳底起水泡。我們花了9天7小時又51分鐘抵達終點,成為第一支贏得國際越野賽的美國隊。
這是第一次和我的英雄參加越野賽,我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
我學到了,當我哭泣時,可以更大口地呼吸。所以,以後我會經常哭泣,不再因此感到丟臉。
我學到了,夥伴的信任可以將你推向任何一座高峰。
我學到了,與其抱著不要輸就好的心態,倒不如下定決心、立定心志才能成功。
我學到了,全世界最棒的團隊不只要分享彼此的優點,也要分擔彼此的弱點。
我學到了激勵隊友的方法,不是讓自己出風頭,而是要讓隊友知道他們自己有多厲害。
我還學到了,當人們從起跑點開始時就能放下自尊,一路上追求著同樣的目標,彼此建立起深厚真摯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同心協力,團結一致──就可以創造出一種勢不可擋的完美力量,足以力拔山河,任何殘酷的環境都難不倒他們。
極限越野賽教我的那些事
我是用土法煉鋼的方式,領略出自己一套對團結一心的看法,整個過程並非一趟重新瞭解這普世價值的啟蒙之旅,而是不得不忍受滿身髒污泥濘、犧牲睡眠、被寄生蟲折磨。我想要贏得全世界規模最大、最艱鉅、最荒唐的多項運動耐力賽:像是高盧越野賽和大自然挑戰賽(Eco-Challenge)。完成這項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入一個四到五人的團隊,隊上有男有女,一起參加六天到十天不眠不休的越野賽。比賽過程中,隊友彼此間的距離不能超過45公尺,所有的項目都要參與,包括競跑、騎越野單車、划舟、游泳、爬坡、叢林探險、滑行。比賽地點是在地球上幾乎渺無人跡的山頂、極度冰凍的沼澤、高溫叢林、急流冰川、熱到腦袋快爆炸的沙漠。整個賽程長達1,600公里,只能依靠地圖、指南針和團隊合作。當你在競賽過程中與隊友培養出患難與共的特別情感時,勢必會學到一些關於人際關係的功課。
參加越野賽之前,我已在1990年代初期奠定了鐵人三項的基礎,應該也是這些經歷讓我成為「越野賽的女先驅」。在《跑步雜誌》(Runner's World)上,我看到關於高盧越野賽的文章,立刻就被這項運動吸引了。這是一項較不需依靠後段衝刺和六塊肌的運動,更多時候是要仰賴腦力、技能和人文精神。記得當時我一邊讀這篇文章,腦海中一邊想著:「這就是我擅長的運動!跟一群很酷的人患難與共!」我第一場參加的,就是1994年舉辦的高盧越野賽。雖然我們那次比賽慘敗,但我從此迷上了越野賽。
越野賽就像魔術方塊,是由體育活動、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技能,以及十足的膽量所組成;若是缺少任何一個要素,就會完蛋。然而,當你的團隊很會玩魔術方塊時,那將是一場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神奇體驗。我們這支團隊之所以能贏得婆羅洲大自然挑戰賽和厄瓜多高盧越野賽,並不是因為實力比別人強,或速度比別人快。但我們的確擁有一項獨特的能力:我們會互相照顧,用集體公開討論和腦力激盪的方式解決問題。我們會拋開自尊,接受彼此的幫助,採納民主式領導作風;就像一頭狂熱的小獵犬,即使被拴著皮帶也要堅持跑在最前面。如此一來,我們凝聚了一股團結一心的力量,不僅因此成為更優秀的運動員,也成為更優秀的人。
越野賽的美妙之處在於,比賽結束後,你征服的不僅是一場艱困的賽程,也考驗了個人的極限。實際上,你已透過人生最重要的冒險活動證明你自己:成為一個偉大的人。參加越野賽,可以把每個人內在的角色帶出來,有的是英雄、戰士、醫者、領導者,有的是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在努力贏得一場越野賽的過程中,我們展現出的是最優秀、最開悟的自己。而且,在競賽過程中以及跨越終點線時,我們可以從隊友彼此的眼中看到這樣的自己。這就是我們一再報名參加越野賽的原因,因為它是全世界最能幫助你肯定生命價值的運動。
極限越野賽並不是一場體育賽事,而是一段漫長的身心冒險歷程,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終究要互相依賴。就像在人生與職場中,你和一個個小團隊一起工作,團隊中有男有女,大家共同努力闖過一連串看似永無止盡的關卡,尋找著幾乎不可能到達的終點。儘管周遭的環境變化無常,必須在不合理的期限內拚命趕工,但每一個團隊都在努力成為業界最傑出的團隊。如此形容若還無法反映出平時的工作情況,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形容的了。以我的經驗來看,參加越野賽時若無法完成比賽,最主要因素是缺乏團隊合作的能力。職場上也是一樣。
在團隊贏得的競賽中,我們之所以能連續不斷地創造一瞬間的佳績或奇蹟,除了結合個別成員的賽前訓練與經驗,更是因為同心協力讓我們團隊的表現更優秀。「連續不斷」才是最關鍵的字眼。在這裡,我要引用優秀的美式足球教練隆巴迪(Vince Lombardi)的一段話,也是我最喜歡的至理名言之一:
不要偶爾才做正確的事,而是時時刻刻做正確的事。成功是一種習慣;不幸的是,失敗也是一種習慣。
我非常贊同他的話。各個團隊之間的差別,多半不是才能,而是每一位隊員堅持同心協力到底的能力。一旦瞭解如何同心協力,就等於擁有一個裝滿有效技能的工具箱,可以在任何情況下跟任何團隊一起使用;不論是跟同事進行一項短期企劃,或是經營終身不渝的美滿婚姻。若能養成一個建立並維持同心協力的習慣,就能養成有志竟成的習慣。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蘿蘋‧班妮卡莎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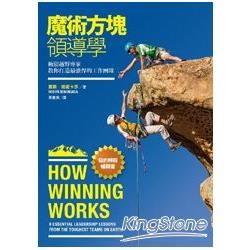 |
$ 70 ~ 279 | 魔術方塊領導學:極限越野專家教你打造最強悍的工作團隊
作者:蘿蘋‧班妮卡莎 / 譯者:黃書英 出版社: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01 語言:繁體/中文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魔術方塊領導學:極限越野專家教你打造最強悍的工作團隊
《紐約時報》暢銷書
極限越野賽就像魔術方塊,由多種團隊合作技能所組成。
作者經歷多場嚴酷賽事,將告訴你與眾不同的領導技能。
引出你內心深處的領導魂,打造最強悍帶勁的頂尖團隊。
極限越野賽就像魔術方塊,是由多種團隊合作技能所組成。
它不是一場體育賽事,而是一段漫長的身心冒險歷程,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終究要互相依賴。就像在人生與職場中,你和一個個小團隊一起工作,團隊中有男有女,大家共同努力闖過一連串看似永無止盡的關卡,尋找著幾乎不可能到達的終點。
──蘿蘋‧班妮卡莎
不論在哪個領域,班妮卡莎都能藉由戰勝最高難度的挑戰,創造出極限表現的藝術形式。她曾騎著越野單車穿越婆羅洲叢林,攀爬過喜馬拉雅山群峰,在智利的激流中漂筏,一路奪下數個世界冠軍頭銜。
體驗世上最嚴酷的挑戰,固然令人痛苦難當,卻又往往激勵人心,也經常充滿歡笑與淚水。因此,班妮卡莎領悟出獨特的「魔術方塊領導學」,幫助每個人打造最強悍帶勁的工作團隊。
在本書中,班妮卡莎分享了自身參加越野賽的故事,以及她體會到的「團隊合作八大要素」。透過這些故事,她要告訴我們,一流的團隊如何在荒野叢林、高山峻嶺中團結合作、突破困境。
不論是想用新產品打敗市場上的競爭對手,還是要在期限內完成堆積如山的工作,或者只是想讓孩子乖乖整理房間,本書將讓你體驗魔術方塊領導學的神奇力量,引導你跨越成功的終點線。
團隊合作八大要素
透過團隊合作(TEAMWORK)八大要素,可以完整組合出你的「魔術方塊領導學」:
Total commitment(全力以赴)
把最終的目標放在心裡。直到結束之前,都不算真正結束!
Empathy and awareness(將心比心)
經常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要用激勵取代批評。
Adversity management(逆境管理)
在小問題變成大災難之前,就要預先處理。
Mutual respect(相互尊重)
尊重你的夥伴。公開讚揚,但是私下指點。
We thinking(同舟共濟)
避免團隊中的互相競爭。大家一起抵達終點,而非只有一個人出風頭。
Ownership of the project(目標認同)
幫助夥伴認同團隊的目標,讓他們打造共同目標。
Relinquishment of ego(放下自尊)
團隊的成功才會滿足你的自尊。需要求救時,儘管開口!
Kinetic leadership(動力領導)
必要時,容許不同的領導者出來接手。領導階層需要不斷地交替。
作者簡介:
蘿蘋‧班妮卡莎曾是美國一家大規模製藥公司的頂尖業務員,也曾是加州聖地牙哥的消防員,兩度獲得大自然挑戰賽世界冠軍。
1994年以來,班妮卡莎和隊友一起踏遍地球上最獨特迷人的教室,探究「終極團隊合作」這門學問。這些教室包括:婆羅洲的叢林、喜馬拉雅山高峰、斐濟的激流等等。
2002年,班妮卡莎創辦了「世界級團隊」(World Class Teams),這是一家團隊諮詢公司。她以「團隊合作」為主題,激勵了數十家大規模企業的員工,包括星巴克、西門子、3M、微軟、雀巢、惠普等等,深受歡迎。
2007年,班妮卡莎進行髖關節置換手術後,成立了「雅典娜計畫基金會」,幫助許多動過手術或遭遇創傷的女性,實現冒險夢想,重新找回人生。
此外,許多知名媒體也將她的成就和故事製成專題報導,例如NBC、ABC、CNN、ESPN、Discovery、Vogue等等。
譯者簡介:
黃書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研究學士、加州州立大學聖荷西分校圖書資訊學碩士。曾任《北美世界日報》新聞編譯,目前為專職譯者。
章節試閱
厄瓜多高盧越野賽(Raid Gauloises Ecuador)
1998年9月
科多伯西火山(Cotopaxi Volcano)
海拔4,500公尺
那天大約是凌晨一點,我們在科多伯西火山海拔4,500公尺山腰處一間小屋裡待了四小時,依偎在一起,一邊休息一邊準備踏上最後1,500公尺的攻頂之路。我的隊友──羅伯特.那戈(Robert Nagle)、約翰.賀華德(John Howard)、伊恩.亞當森(Ian Adamson),以及史蒂夫.葛尼(Steve Gurney)──安穩地躺在我身旁打呼著。但是,自從我們踏入這間小屋後,我就不停地哭泣,無法自已。我哭,除了因為這是我唯一能補充氧氣的辦法,也...
1998年9月
科多伯西火山(Cotopaxi Volcano)
海拔4,500公尺
那天大約是凌晨一點,我們在科多伯西火山海拔4,500公尺山腰處一間小屋裡待了四小時,依偎在一起,一邊休息一邊準備踏上最後1,500公尺的攻頂之路。我的隊友──羅伯特.那戈(Robert Nagle)、約翰.賀華德(John Howard)、伊恩.亞當森(Ian Adamson),以及史蒂夫.葛尼(Steve Gurney)──安穩地躺在我身旁打呼著。但是,自從我們踏入這間小屋後,我就不停地哭泣,無法自已。我哭,除了因為這是我唯一能補充氧氣的辦法,也...
»看全部
目錄
起跑線
1 全力以赴
準備
計畫
企圖心
毅力
2 將心比心
換位思考
建立深厚的人際關係
指導vs.批判
我們是在為人工作,不是為了公司
3 逆境管理
挑戰vs.障礙
必勝的希望vs.失敗的恐懼
接受逆境,把握機會,學習超越
永遠不要為了追求完美而影響進度
4 相互尊重
記住「鋁罐理論」
無私的指點
團隊角色比個人感受更重要
無條件相信
把尊重他人當成贈禮
5 同舟共濟
帶大家一起跨越終點線
全體團隊一起承擔責任
患難與共
你的問題=我的問題
...
1 全力以赴
準備
計畫
企圖心
毅力
2 將心比心
換位思考
建立深厚的人際關係
指導vs.批判
我們是在為人工作,不是為了公司
3 逆境管理
挑戰vs.障礙
必勝的希望vs.失敗的恐懼
接受逆境,把握機會,學習超越
永遠不要為了追求完美而影響進度
4 相互尊重
記住「鋁罐理論」
無私的指點
團隊角色比個人感受更重要
無條件相信
把尊重他人當成贈禮
5 同舟共濟
帶大家一起跨越終點線
全體團隊一起承擔責任
患難與共
你的問題=我的問題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蘿蘋‧班妮卡莎 譯者: 黃書英
- 出版社: 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01 ISBN/ISSN:978986888553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商業> 經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