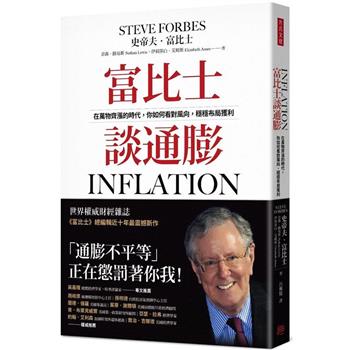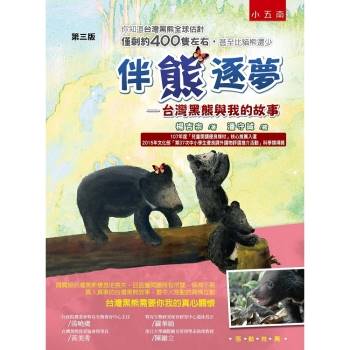腸子奈歐蜜.埃德曼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告訴我們,在鄰近於肛門到生殖器官之間的部位,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人類精神官能症的源頭。現今時日流行與佛洛伊德保持距離,抱持著「我不會那麼誇張」和「佛洛伊德當然就是對性癡迷」的看法。不過,我就是覺得有那麼誇張,而且多數的人都是癡迷於性的。
坦白說,腸子是個問題,其功能不僅神祕且令人困惑(所有體內器官幾乎都是如此),而且也讓我們難以承受。只有我們開始思考腸子的象徵意義,或許能夠了解佛洛伊德到底在說什麼。
腸子的一端是嘴巴,是產生多樣喜悅而令人歡愉的地方。然而,其另一端是肛門,會產生腐敗、骯髒和毒氣的臭屁;此外,肛門還會產出糞便,同樣氣味難聞,而且是攜帶疾病的一種黏稠味臭的棕色汙染物。這樣的東西竟然是來自於人體!不只是從我們的身體排出,其排出的洞口竟然就緊鄰在身體帶給我們極大歡愉的部位,而且這些器官的發育成長表明了我們進入能夠孕育新生命的成年時期。這就像是人類的生命形態所開的一個可怕的玩笑,要把我們從雲端高處拉到地底深淵,目的是要提醒我們,不管我們發現了怎樣的狂喜,我們其實也是無時無刻都滿肚子大便。這正是糞便讓人感到如此可笑的原因,也是我們何以必需對糞便一笑置之,因為如果不笑著面對的話,我們就會痛哭流涕。
對於普利茲得獎作品《否認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的作者厄內斯特.貝克(Ernest Becker)來說,肛門和其產生的糞便並非只是一個笑話,它們其實是恐怖的東西,其所再現的是肉體的衰敗,而那是全人類都面臨的宿命。「我是什麼呢?」孩子可能會這樣問著自己。「我是一個會把漂亮、閃亮、健康、美味、繽紛和令人興奮的食物吃下肚裡的東西。可是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呢?食物會被我變成了糞便。」這是每天都會一點一點發生的不可避免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死亡。「肛門和其無法理解且令人作噁的產物,」貝克說道,「再現的不僅是肉體的決定論和侷限性,同時也是所有肉體的宿命,那就是衰敗和死亡。」
朋友的三歲女兒問她吃下肚的食物會發生什麼事,她回道:「妳的身體吸收了食物的能量,然後食物就會被妳變成大便。」她的女兒聽完後哭喊到不可抑制,「不要,媽咪,不要,」女兒不斷地說著,「不要這樣啦!」同樣的哭喊也見於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沒有什麼好怕的》(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他在書中描述了自己的死亡恐懼症(thanatophobia),怕死的他會在半夜醒來,「孤零零一個人,孤單極了,用拳頭鎚打著枕頭,在無盡的哀嚎中大喊『噢,不要!噢,不要!噢,不要啦!』」。糞便是死亡,死亡很嚴重;我們因此只能對糞便一笑置之,我們不能過於嚴肅對待,這是因為糞便是相當嚴重的東西。
嘴巴、肛門和介於兩者之間的腸子,一起把美麗變成腐敗、美味變成噁心。就是在此真實地揭露了我們與自己身體的關係──我們每天都要在這裡面對人類最終所承繼的腐壞和衰敗。身體很神祕;我們就是自己的謎團。然而,就是在腸子部位,那顯然的神祕最為清晰可見。如果我可以把食物弄成這樣,我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在我二十歲出頭的時候,時年五十五歲左右的母親因為腸破裂而緊急送醫求診。她腸破裂的原因從來就不是相當明確,或許是腸道裂隙受到感染,或許是好幾年前在我出生時的剖腹產所造成腸子脆弱,也或許完全是其他的原因。在腸子療癒的期間,母親有十八個月的時間都必須裝帶著結腸造口袋;這是個讓整個家庭與腸子的實際運作正面相對的一個經驗。我的母親的母親在五十歲中旬時也有過某種腸破裂,我凝視著自己的肚子,不禁想像著會有什麼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事情並非僅是如此。如果是由小說家來書寫我的家庭的故事,有人可能會認為,有關胃腸和消化過程的象徵處理得稍嫌過火和稍嫌明顯。有位近親罹患先天性幽門狹窄,他的胃部有個括約肌無法打開,而使得他剛出生的時候一直出現嚴重噴射性嘔吐的情形,而他的母親則試圖說服醫師他一定真的有什麼毛病。他才沒有幾天大,就必須接受開刀治療;一個小寶貝於是就有了一條劃過腹部的長疤痕。
這些胃不合作的情形只是故事的一面,另外一面則是胃太合作、太有效率、太喜歡吸收營養。我是個胖子。我父親是個胖子。我祖母是個胖子。我的姑姑在成為「體重觀察家」公司(Weight Watchers)的領袖之前也是個胖子,現在的她則是一個以前曾經很胖的人。我們一家都是胖子,我們的家庭故事就是在吃與不吃、消化與不消化的緊密關係之中打轉,思索著要如何讓食物順利下肚或者是中斷進食。
可是我並不認為只有我的家庭是如此。從文化方面來看,我們都為著食物和飲食方式而困擾。我們用脂肪和糖做出了更多奢華食品──像是把奶油可頌炸得像甜甜圈的可拿滋(cronut),有誰不想吃這樣的糕點呢?然而,我們卻同時發明了更多累人的飲食養生法,舉凡從每周禁食兩天到切除健康的胃等等,原因不外乎是我們認為當今的文化相當排斥肥胖。我們看著電視上的名人主廚澆淋著巧克力醬、蜂蜜或奶油,而且食物跟性也被串聯在一塊,像是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主持的輕佻《原味主廚》(Naked Chef)美食節目、奈潔拉.勞森(Nigella Lawson)的打情罵俏的外表,以及高登.拉姆奇(Gordon Ramsay)在節目開始退去衣衫的《食為天》(The F Word)。與此同時,飲食失調的情況正不斷增長,這是Photoshop修圖軟體推波助瀾的結果,我們文化的美麗理想標準要的是越纖細越好,而真實的人體看起來都不夠苗條。單就去年而言,英國年輕人為了飲食失調而入院治療的人數就上升了百分之八。
我們擔心著食物、消化力和自己的胃。腸子是我們的焦慮所在之處,而我們的焦慮是有意義的;對某個事物感到焦慮,就是對這個事物癡迷。如果你會對某個話題持續出現焦慮的話,這是因為你在某程度上很喜歡思考這個話題。到底是什麼使得食物和吃東西能夠讓人想著就產生這樣的滿足感呢?
我懷疑這跟死亡本能(Thanatos,譯註:桑納托斯是希臘神話中的死神,此為其引申涵義)有著某種關聯。先前有人談到,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們迷戀死亡,但是卻不能忍受談論性,而當代的我們則剛好相反。流進、流出。我們談論著食物、青春和性,一切事物的開端。我們生活在那些開端之中,好似恨不得永遠都是春天的第一天。如果我們一直對食物有所焦慮(吃得夠不夠、是不是吃太多、吃的對不對),我們盡可用一波清水把糞便沖走,並且不再想起或思考其代表了什麼。如果我們聚焦在青春,我們就可以把老人家送到安養院,然後就不必再見到或想起他們。如果我們總是談論著性、也就是想著一切的開端,我們就沒有保留任何空間給死亡:一切的盡頭。
因此,糞便有沒有可能引起喜悅呢?如果我們可以找出來的話,對於社會或個人會不會比較好呢?我認為會的,只要我們能夠全然珍視自身可怕的糞便機器(腸子)的運作,就可以引領我們走往這個志業的正確方向。
糞便當然可以讓人喜悅,只要是曾受便祕所苦的人都可以肯定這一點。我的弟弟和弟媳最近剛生了一個女寶寶,讓我第一次成為姑姑。當小女嬰大了一條長長的健康糞便時,他們真是為之欣喜,我們也都很高興。排便表示一切運作正常。流進、流出。排便應當就是這麼一回事兒。至少在漫長有用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刻,死亡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兒。這可能是大自然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這可能是我們完全無法掌控的衰敗過程有著些許的美感。
沉思於「大自然」知道而我們不知道的美妙的事物,或許這是不錯的點來讓我引介胃的神經元和目前居住在腸道的大量細菌的本質。你知道你的肚子有腦細胞嗎?它們布滿了腸壁,而你的消化道的神經元數目就跟一隻貓的頭部神經元數目一樣多。思考一下一隻貓知道的所有東西:什麼是好的和什麼是討人厭的、誰可以信任和誰該敬而遠之、美食在哪裡和要如何追捕到。這些就是你的胃可能會知道的東西,也難怪我們會談論「腸臟本能」(gut instinct,意指直覺)了。
腸道的神經元是透過迷走神經而直接與大腦連結,而迷走神經進入大腦的部位就緊臨其主掌情緒的部分。胃似乎能夠知道一些連我們都不知道的自己的事情。曾經有過這樣的實驗,參與的人是經由管子進食,因此無法品嚐、聞嗅或咀嚼食物;然而,若是將他們最喜愛的食物導入胃部,這卻會使得他們出現預期性反應,即是會比餵食其他一些同具營養性的食物泥來得更加快樂。你的胃是知道事情的,你之所以會感到七上八下的,那是因為那裡的神經元對發生的事情有著某種反應。
「我們」的一些部分(或許該說是大部分的「我們」)是連我們自己都無法接近的。席莉.胡絲薇德(Siri Hustvedt)在其回憶錄《顫抖女子》(The Shaking Woman)裡,描述了自己在顫抖發作時所經驗到的一種雙重感受;她出現了「一個『自我』(I)和一個無法控制的他者的強烈感覺」。我們的身體充滿了智能,而我們的胃充滿了神經元,故就某種意義上,我們體內有著另外的「自我」,會與大腦溝通,但又不全然屬於大腦。
不過,我們的腸道甚至還有一個真正「難以駕馭的他者」。我們自以為裹覆於這身肉體的自己是單一個體,肌膚輪廓之內的一切就是「自己」,殊不知,腸道裡還有著「微生物群系」(microbiome),是個由微生物組成的生態共同體。這些是「好菌」,好到用來廣告益生菌優格。腸道菌群的細胞比人體組織的細胞要微小許多,小到「我們」體內實際含有的腸道菌群細胞數多於人體的細胞數。如果我在皮膚內舉行一場每個細胞都可投票的公投,「我」要掌權的勝算大概很渺茫。
這個類比其實並不如乍聽之下那般荒謬。腸道菌群會影響人的情緒和健康,因此增加腸道菌群的多樣性(我們的腸道顯然是想成為比例代表制的政體,故而種類越多越好),有助於改善從沮喪到類風溼性關節炎等狀況。腸道菌群也會釋出荷爾蒙,以便鼓勵我們多吃一些它們喜愛的食物。此外,人體只能培育既知的百分之五的腸道菌群,對於其他百分之九十五則一無所知。我們可以從益生菌飲品獲得的是那少得可憐的百分之五的好菌;至於其他的好菌,我們就只能等待尚在對未知的腸道菌群所進行的基因測序。或者,要是真的迫不得已的話,不妨考慮糞便移植,而那完全就是你可以想到的一種程序;將一個人的「黃金糞便」以點滴或糞便灌腸的方式注入另一個人的腸道,如此即可完成這種奇蹟療法。當新的細菌菌群存活下來,接受移植的人也會開始好轉;這種療程對治療如類風溼性關節炎和致命細菌困難梭狀芽孢桿菌(C. difficile)等諸多病況都有作用,可是千萬別在家自行嘗試。
以上的要點是,腸子裡發生的事相當神祕且令人訝異,當我們看著臭大便而腦中浮現「我怎麼會生出這種東西?」的時候,其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來得更加複雜且更加明智。座落於人體中心且有著迷宮般美妙配置的腸子有著一顆大腦,而其周遭的鄰居們也有自己的欲望。
而談到死亡本能這件人類大事,這也讓人感到安心。雖然我不知道如何消化食物,但是腸子知道,而且腸子也會讓我對於有人讓它感到焦慮的處境有所感受。我或許不知道該如何死去,可是我的身體知道。
法國思想家蒙田是隨筆書寫形式之父,他從馬匹上跌落得極慘,幾乎因為傷勢而死。當他的朋友驚恐地看著他抓扯著自己的衣服且顯然在極大痛苦中,蒙恬自己卻經驗了一次極樂的鬆懈感受。復原之後,他寫下了與死亡擦身而過的經驗:「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死去,不用擔心,大自然當下會毫無保留地告訴你怎麼做。大自然會為你處理得盡善盡美,因此,就別傷腦筋了吧。」
由於我們在文化上患有食物精神官能症,我們可以得知人類迷戀的是開端而不是結束。我們對顯然無止境的自身欲望感到苦惱,而消費資本主義對此更是火上加油。即使我們知道自己終將把一切化為糞便,但是我們卻拒絕去想這件事。不過,我們需要的或許是現代西方社會很少談論的東西,那就是一點信仰。我們可能不知道糞便是怎麼做出來的,但是我們的肚子知道。我們可能不了解怎麼死去,但是我們的身體會帶領我們經歷一切。我們知道的比我們認為的要來得多。「我們」其實不需要知道就可以知道。
皮膚克里斯汀娜.帕特森
「這個,」我的父親說著,「就像一顆桃子。」他剛剛撫過我的臉頰,¬¬而我這才第一次意識到將我與身外世界隔離的這身薄膜。
舔掉手指上的冰淇淋、踮腳走在沙灘和感覺海水輕拍小腿,我知道這些都讓人覺得舒服。在幼兒園玩溜滑梯溜得太快而一臉撞上冰冷的金屬邊,我知道原本滑順的地方猛然就會有道裂傷。當母親掀開膠布時,她不禁嘆息地說希望我不會留下疤痕,可是我還是留了疤,現在疤也還在。即使發生了這件事,我望著被鐵絲網劃破而長出如同甲蟲殼般的褐色硬皮的膝蓋,以及重重撞上磚頭而從白色轉為紫青斑點的手肘,我依然不曾對這個人體內外分界的東西有什麼想法。
後來,因為游泳的關係,你的身體會長出叫做疣的東西,那意味著你必須到專門診所去把它們燒掉。還有因為輕輕碰到蕁麻,或者是試著要追逐一道浪而碰上了不好的水母,你可會出現紅腫,實在有太多東西都會造成擦傷、切傷或刺傷了。但是唯有等到父親摸著我的臉頰並說它像個桃子,我那時才意識到父親覺得漂亮的這一層叫做皮膚的東西。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孩童的皮膚跟成年男女的皮膚不同;我不知道孩童的皮膚比較柔軟、比較滑順而且更好觸摸,而箇中緣故是因為孩童皮膚底下有更多脂肪組織,而且皮膚外層仍是厚的。我當時也不了解,這層柔軟、滑順且點綴著一層細毛的東西會讓一個大人快樂和感傷;它可以讓一個成年人因為喜悅和想要保護的衝動而心跳加快,但是也會讓人因為害怕而揪心。當你還是個孩子,你不知道有個成年人稱為「純真」的東西,而那必然會失落在人生之中。
當你是個孩子,你不會了解新鮮的年輕皮膚被認為是漂亮的東西,而且是因為青春在人的眼中是漂亮的,漂亮的東西就會受到獎賞。不過,你確實學到醜陋的事物就不會如此。例如,你可能聽到了聖經中的痲瘋病人的故事。你可能聽過,有位被譽為彌賽亞的人觸碰了一個痲瘋病人,並告訴他要「保持乾淨」。他之所以告訴對方要「保持乾淨」,那是因為一旦有了這種疾病,你的皮膚會產生鱗屑、手跟腳的趾頭會因之變形,而人們就會覺得你很骯髒。你從中學到,痲瘋病患要離群索居,有時還需要搖鈴以便提醒他人自己的到來。
如果你真的聽過聖經的故事,那你大概也聽過約伯(Job)的故事。聖經提到神對於約伯的試煉。神允許撒旦屠殺了約伯的牛隻、駱駝、驢子和羊群,神也允許撒旦殺害了約伯的兒女,並且允許撒旦用癤瘡來「折磨」約伯。約伯的癤瘡嚴重到毀損他的形體,連他的三個最好的朋友都認不出他來。而當他們終於認出他的時候,他們驚嚇到有一個星期都無法開口說話。
從聖經的故事,你學習到皮膚病是讓人感到羞愧的東西。然而,正當你開始想著自己有多麼想要觸碰他人的肌膚,以及自己有多麼想要他人的雙唇碰著自己的嘴唇;事實上,每當通過血管的體內荷爾蒙讓你不禁想著,自己最想要的就是能夠與人赤裸相貼,於是你開始端詳著鏡中的自己,但是卻看到身上出現了小紅點。
如果你夠幸運的話,可能是冒了青春痘,不過就算是青春痘,也能夠打擊正徘徊於孩童和甩開童年之間的人的脆弱自信心。正當你擔心著怎麼所有朋友都好漂亮,而自己卻太胖或太瘦,或者是太高或太矮的時候,你可能發現自己的臉上接二連三出現了小膿包。說起這種情況的人似乎都覺得很逗趣;書籍、電影和電視節目似乎覺得青少年長痘子很逗趣。可是當你覺得自己好醜,醜到不想出門的時候,這似乎就不是真的那麼逗趣了。
當青春期過去了,可是痘子卻沒有消失,那就根本不會讓人覺得逗趣了。我對此非常了解,因為我就是這樣。臉上有痘子對我來說已經夠糟了,可是我二十三歲的那張臉卻是糟到像在打仗。當我到醫院治療皮膚病的時候,臉部的糟糕程度讓諮詢師邀請了一群學生進場呆視觀摩。醫師開立處方要我進行「長波紫外線光化治療」(PUVA),這意味著我每天都要去醫院,躺在像直立式棺材般的鐵箱裡被特殊的紫外線轟炸臉部。幾個星期過後,紫外線光燒掉了大部分的痘子和幾層皮膚,但是就是沒有燒掉痘疤。
當我的臉部狀況益發嚴重、流膿,而且還正因深沉紅色腫塊就要冒出大黃痘頭而翻騰不安,我偷偷望著車子側後視鏡,鏡中映照的景像讓我感到噁心,心想這大概是最糟糕的情況吧。我現在則知道,發生在我身上且嚴重到要轉診看國內最頂尖的粉刺專家的粉刺狀況,只不過是皮膚所能出現的問題的冰山一角。
比方說,在英國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的高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裡,你可以發現許多的臉、手臂和腿,但是看起來卻不怎麼像是臉、手臂和腿,那是因為它們都布滿了鱗屑,或是腫塊,或是疙瘩,或是腫脹如角的大肉瘤。有些確實是角;館長說這些是「皮角」(Cutaneous horns),並且不帶情感地告訴我,皮角是由「軟組織」所組成。在玻璃標本罐裡,你可以看到癌瘤(carcinomas)、黑色素瘤(melanomas),以及看起來像是蜥蜴皮般的人類皮膚。有個玻璃罐裡,你可以看到一顆婦女的頭;那是個年老的女人,有著亮紅色的頭髮,可是比起那頭頭髮更駭人的是從她的眉頭長出的巨大鱗屑增生物。
如果你對這個博物館收藏所留存的故事想太多的話,你可能會發瘋;例如,倘若你思索著那個有著巨大腫脹的腳的男子,可是那隻腳看起來卻不像是人腳。館長說那是「戰壕腳」(Trench foot);然而在所有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和詩歌中,戰壕腳至少還會讓你想到看起來像是腳的東西。或者是想想那些動手術前先為自己畫張肖像的中國病患,他們的巨形腫瘤看似多出來的肩膀或背部;他們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切除腫瘤;奇蹟似的,他們都存活了下來。
再來是館裡的一個小嬰兒,人們稱之為「斑色魚鱗孩」(harlequin baby)。「harlequin」這個英文字讓人想到了小丑,可是當你看著蜷曲在罐中的小嬰兒,你絕對不會想到喜劇。當你看著裹覆在其身上的菱形鱗屑,皮膚龜裂分離,你不禁想著生出這個小嬰兒的母親,想著她短暫地把嬰兒抱在懷裡的感受。
當我換過一個又一個皮膚科醫師,用過一種又一種的乳液,並且嘗試了各種醫師可以想到的藥物,我並不知道皮膚有可能出現的所有可怕狀況。不過,關於皮膚的運作,我倒是學到了不少。我買了《粉刺治療》(The Acne Cure)和《超級皮膚》(Super Skin)這類的書。我也買了一本書名為《粉刺:清潔肌膚的建議》(Acne: Advice on Clearing your Skin)的書。「粉刺,」這本書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話寫著,「是我們依舊需要研究的一種皮膚病。」換言之,這是還無法治癒的一種疾病。書中有圖解展示「堅韌的外層皮膚」叫做「角質層」(stratum corneum,又稱horny layer),書上說這就像是一層「保護塗層」;其下方是「表皮」(epidermis),表皮製造的細胞會向上移至「角質層」,而表皮之下則是含有血管和神經的「真皮」(dermis)。「一個表皮細胞,」該書寫道,「大概要花上二十八天才能夠從表皮的底部上移到頂部而形成角質細胞。」換句話說,皮膚只要二十八天即能汰舊換新;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你就有了新的皮膚、新的自己。
麻煩的是,大多數的皮膚病都不會在一個月內痊癒。我的皮膚科醫師組成了一個粉刺病患支持團體;你是不會為了一個月內就消失的事物而經營支持團體的。我買的另外一本書是《學習與皮膚疾病共處》(Learning to Live with SkinDisorders),而在皮膚出現小碎片、鱗屑和剝落的情況,該書並沒有告訴你應該要打開小藥盒吞顆藥丸。對許多人而言,皮膚病症會跟著一輩子。「為什麼我這麼早婚呢?」從六歲起就有乾癬(psoriasis)的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寫道,「箇中原因是,當我找到了一個不會嫌棄我的皮膚狀況的秀麗女子,我可不敢冒著失去她而要再找下一個人的風險。」他在著作《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中的一篇名叫〈與我的皮膚打仗〉(At War With My Skin)的隨筆中如此寫道。
不過,科學日新月異。例如,在「幹細胞與再生醫療中心」(Centre for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生物學家正在觀察皮膚細胞回應環境的方式,以及幹細胞於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皮膚、表皮、毛囊和皮脂腺都有各自的幹細胞。倘若你出現傷口,幹細胞會開始進行平常不會做的事。事實上,幹細胞可能是我們的救星,而對於身有皮膚病的人,有誰會不想得救呢?
我不知道是什麼讓我戰勝了這場皮膚的戰役,可能最後是時間的關係吧。然而,在歷經治療、順勢療法、自然療法、針灸治療和藥草治療通通失敗的年歲裡,我學到了皮膚通常可以表達我們表達不出來的東西。當我們悲傷、憤怒、失落或孤單之際,皮膚就會起泡、發癢或流汁。我們可以吞下藥丸和塗滿藥劑,但是用消聲器掩住一個人的嘴,那只能讓人不要聽到那些話罷了。有一半的時刻,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或許應該說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如此。我們只知道自己是怎麼過日子的,像是工作、家庭、住處或心靈,而就是這些讓我們的皮膚百般不舒服。
若不相信心靈可以直接影響到皮膚的話,請參看一下研究資料。在一份關於接觸性皮膚炎的日本研究中,所有參與人都要觸碰無害的葉子,但是他們會被告知自己碰的是會產生類似毒藤作用的葉子,結果所有的人都對無害的葉子出現了反應。許多研究也顯示,當摯愛的人過世的時候,人的皮膚會出疹子。「皮膚病,」心理分析師達瑞安.里德(Darian Leader)寫道,「通常是象徵性的,但是其中涉及了組織的變化。」在《人為何會生病?》(Why Do People Get Ill?)一書中,他描述了一名年輕士兵的案例;該士兵出現了看似被鞭打過的紅腫皮疹。他在九歲的時候,因為從女生宿舍的窗戶向內偷窺而受到了鞭打,十年之後,當他被人發現在軍隊駐紮地的護士宿舍外頭流連徘徊的時候,就又全身起了疹子。他當時希望見到某一位女護士,但是卻被一位軍官攔住並叫他離開,後來不到一個小時之內,他就出現了紅腫狀的疹子。
皮膚是設計來讓我們免受外在世界的影響,也難怪我們通常覺得皮膚不夠厚。我們說,我們需要多長出一層皮膚;我們說,我們想要在這身皮囊中感到自在,至於我們不想要的,就是讓自己的傷悲或恐懼全寫在臉上。
或許是這樣的奇蹟:大多時候,情況都非如此。大多時候,對於我們多數人而言,皮膚這個人體最大器官並不會布滿紅疹或潰爛。大多時候,對於我們多數人而言,皮膚執行著份內的工作。它包住了一切。它讓身體維持適當的溫度以利生存。它在需要的時候能夠伸縮自如;它保護你免受危險,並且向你提出疼痛的警告。它也能讓你感受到陽光煦煦,以及愛人撫摸所帶來的觸電般的喜悅。
隨著日升日落、月的盈虧,以及四季遞嬗,皮膚製造著大量的新細胞;不論生命有什麼變化,它還是繼續生產那些細胞。當你出現新的傷口,皮膚會將之療癒;儘管可能留下了疤痕,但是確實是痊癒了,而這樣過後可能不會看起來像顆桃子。當你真的活過一陣子,你的皮膚就不會看起來像顆桃子;當你真的活過一陣子,介於你和世界之間的那道有彈性的屏障會顯露出某些你奮戰得勝的戰役痕跡。我們因而應該看到那些疤痕所透露的美麗。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衛爾康收藏館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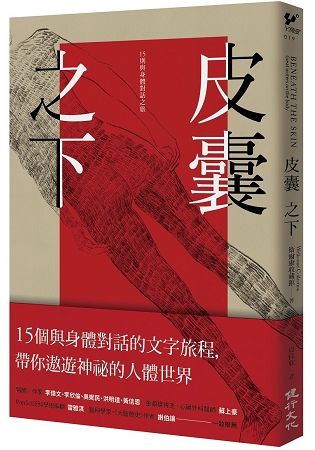 |
$ 190 ~ 288 | 皮囊之下: 15則與身體對話之旅
作者:衛爾康收藏館 / 譯者:周佳欣 出版社: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5-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24頁 / 14.8 x 21 x 1.2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皮囊之下:15則與身體對話之旅
★ 探索身體奧祕和啟發讀者對自身身體的關注
醫師∕作家 李偉文、李欣倫、吳妮民、洪明道、黃信恩
金鼎奬得主、心臟外科醫師蘇上豪 一致推薦
文學與醫學結合之作,探索人體奧妙!
我們自以為裹覆於這身肉體的自己是單一個體,肌膚輪廓之內的一切就是「自己」,殊不知……——奈歐蜜.埃德曼(Naomi Alderman)
當你真的活過一陣子,你的皮膚就不會看起來像顆桃子;當你真的活過一陣子,介於你和世界之間的那道有彈性的屏障會顯露出某些你奮戰得勝的戰役痕跡。我們因而應該看到那些疤痕所透露的美麗。
——克里斯汀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
由於膽囊或闌尾對我們早已失去象徵或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決定要捨棄它們就相對容易些。到底在醫學上、心理上和情緒上不可或缺的是我們的哪些部分?我是我的身體嗎?可是又有多少部分是我想要或需要的呢?
——奈德.包曼(Ned Beauman)
詩其實是個身體事件。一首詩會改變讀者對於自身肋骨和橫膈膜的經驗。詩可以幫助創造胸膛的一種空氣顫動,而肺部將會因之冷靜或衝動。完成的詩作、歷久不衰的詩作、一次呼吸的勝利!……所以到了最後,就在呼吸的氧氣和二氧化碳的交換系統,我們領略了絕望、堅忍及喜悅,來自於歌、來自於詩。
——達爾吉特.納格拉(DaljitNagra)
埋在我們皮膚和骨骼下有不同的器官,從泵血的心臟、肺部的膨脹到腎臟的過濾,這些和其他的器官是我們生存所必須的,然而,我們對它們知之甚少,本書將告訴你更多關於它們的故事。
多位世界頂尖的作家聯同醫學專家,為讀者展示身體各個器官的特質。包括二○○六年柑橘文學獎新人獎得主娜歐米.愛德曼揭示了腸子以及我們對食物的沉迷;湯瑪斯‧林區讚揚了子宮的奇蹟;A.L.肯尼迪探究了鼻子召喚記憶的驚奇能力,至於菲力普.克爾則是追溯了腦部手術的非凡歷史;毛姆文學獎得主奈德.包曼探討闌尾並不如我們所認為是沒有用的器官。
十五位作家聯手奉獻這本旨在探索身體奧祕和啟發讀者對自身身體的關注。希冀透過檢驗人體的獨特部分來釐清人的境況。雖然每篇文章的作者不同,但是都圍繞著一個相同的主題:究竟這些不同的人體部分(器官和腺體)是如何讓我們成為了現在的自己呢?他們與醫學專家一起,分別選擇了不同的器官,以優美迷人的文字,將生澀的醫學知識娓娓道來:人類的胃內包含許多貓大腦內發現的腦細胞;肺的重量等同一條麵包;創傷的記憶能展示在皮膚上等。
《皮囊之下》將是一次動人、幽默、迷人的文字旅程,有時更令人意想不到,跟隨著本書的腳步探索的人體神祕景觀,讀者將會歷經一趟令人嘆為觀止的旅程。
作者簡介:
衛爾康收藏館(Wellcome Collection)
一家博物館和圖書館,收集各種關於人們對健康的想法和感覺,館內展示亨利.衛爾康(Henry Wellcome)收集的醫學工具和奇怪的收藏品,有科學、醫學、生活和藝術等不同層面,每年舉辦不同主題的展覽,包括意識、解剖、情緒、性科學和死亡。
譯者簡介:
周佳欣
自由譯者,愛爾蘭三一學院戲劇博士候選人。旅居愛爾蘭與美國近十年,口筆譯工作不輟,深愛翻譯文字的那份心靈平靜感,現亦從事口筆譯教學與戲劇創作。喜愛藝術、旅行和瑜伽。譯有《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讓阿育吠陀重啟消化力:通暢淋巴系統、完全消化麩質和乳製品》等。
章節試閱
腸子奈歐蜜.埃德曼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告訴我們,在鄰近於肛門到生殖器官之間的部位,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人類精神官能症的源頭。現今時日流行與佛洛伊德保持距離,抱持著「我不會那麼誇張」和「佛洛伊德當然就是對性癡迷」的看法。不過,我就是覺得有那麼誇張,而且多數的人都是癡迷於性的。
坦白說,腸子是個問題,其功能不僅神祕且令人困惑(所有體內器官幾乎都是如此),而且也讓我們難以承受。只有我們開始思考腸子的象徵意義,或許能夠了解佛洛伊德到底在說什麼。
腸子的一端是嘴巴,是產生多樣喜悅而令人歡愉的地方。...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告訴我們,在鄰近於肛門到生殖器官之間的部位,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人類精神官能症的源頭。現今時日流行與佛洛伊德保持距離,抱持著「我不會那麼誇張」和「佛洛伊德當然就是對性癡迷」的看法。不過,我就是覺得有那麼誇張,而且多數的人都是癡迷於性的。
坦白說,腸子是個問題,其功能不僅神祕且令人困惑(所有體內器官幾乎都是如此),而且也讓我們難以承受。只有我們開始思考腸子的象徵意義,或許能夠了解佛洛伊德到底在說什麼。
腸子的一端是嘴巴,是產生多樣喜悅而令人歡愉的地方。...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湯瑪斯.林區
「擁有身體是為了學習哀悼」,麥可.赫弗南(Michael Heffernan)在詩作《讚揚它》(In Praise of It)中如此寫道;他現在出版了許多詩集,這是第一本的倒數第二首詩的開頭詩句。如同大多數的輕薄詩文書籍,這樣的詩集在五大洲都不受重視,而且世界上也沒有什麼人認識這個作者,可是儘管如此,他卻偶然揭露了一項真理:只有這副軀體得以留駐我們的想望、我們的悲傷和我們的喜悅。當我們心碎了,心就藏在胸骨之下、偎依在包膜之中、跳動著抑揚的旋律。在我們的骨頭裡,大多數是我們對他人擁抱的想念,或是舊傷、老損和戰...
「擁有身體是為了學習哀悼」,麥可.赫弗南(Michael Heffernan)在詩作《讚揚它》(In Praise of It)中如此寫道;他現在出版了許多詩集,這是第一本的倒數第二首詩的開頭詩句。如同大多數的輕薄詩文書籍,這樣的詩集在五大洲都不受重視,而且世界上也沒有什麼人認識這個作者,可是儘管如此,他卻偶然揭露了一項真理:只有這副軀體得以留駐我們的想望、我們的悲傷和我們的喜悅。當我們心碎了,心就藏在胸骨之下、偎依在包膜之中、跳動著抑揚的旋律。在我們的骨頭裡,大多數是我們對他人擁抱的想念,或是舊傷、老損和戰...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Introduction 湯瑪斯.林區(Thomas Lynch)
腸子 Intestines 奈歐蜜.埃德曼(Naomi Alderman)
皮膚 Skin 克里斯汀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
鼻子 Nose A.L.肯尼迪(A. L. Kennedy)
闌尾 Appendix 奈德.包曼(Ned Beauman)
眼睛 Eye 阿比.柯提斯(Abi Curtis)
血液 Blood 卡優.欽戈尼(Kayo Chingonyi)
膽囊 Gall Bladder 馬克.瑞文希爾(Mark Ravenhill)
腸子 Bowel 威廉.范恩斯(William Fiennes)
腎臟 Kidney 安妮.佛洛伊德(Annie Freud)
大腦 Brain 菲力...
腸子 Intestines 奈歐蜜.埃德曼(Naomi Alderman)
皮膚 Skin 克里斯汀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
鼻子 Nose A.L.肯尼迪(A. L. Kennedy)
闌尾 Appendix 奈德.包曼(Ned Beauman)
眼睛 Eye 阿比.柯提斯(Abi Curtis)
血液 Blood 卡優.欽戈尼(Kayo Chingonyi)
膽囊 Gall Bladder 馬克.瑞文希爾(Mark Ravenhill)
腸子 Bowel 威廉.范恩斯(William Fiennes)
腎臟 Kidney 安妮.佛洛伊德(Annie Freud)
大腦 Brain 菲力...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