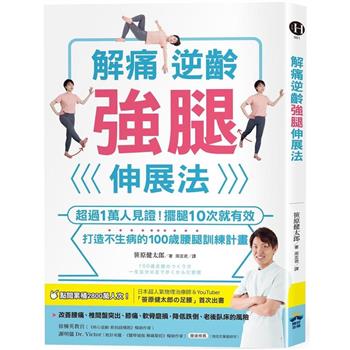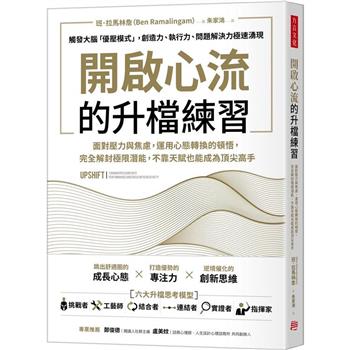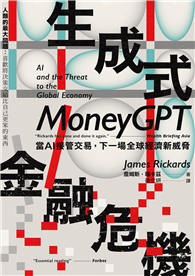☆ 青少年圖書期刊「最佳青少年小說」提名
☆ 好讀網每三人就有一人評價滿分五星!
未來的世界裡,魔法是真實存在的。
全球暖化、海水倒灌……使得人類生存的空間越來越狹窄。即將被淹沒的曼哈頓市裡,權貴住在高樓大廈「凌霄居」中,貧賤的人民則與擁有魔法的魔巫同住在低窪髒亂的「深淵」,苟延殘喘。
一覺醒來,艾麗雅‧羅斯發現自己的記憶滿是漏洞。她有個未婚夫,對方是父親的政敵之子,不顧家人的反對,兩人愛得難分難捨。至少,別人是這麼告訴她的,儘管她連對方的臉都想不起來。
偶然間,艾麗雅邂逅了英俊迷人的叛逃魔巫亨特,以及他的好友特可。在他們的幫助下,她漸漸尋回遺失的記憶,更對謎一般的魔巫動了心。
但,那些記憶真的是她所想要的嗎?或許,得回了記憶,將讓她失去更多……
「打從翻開第一頁我就停不下來。這是場讓人熱血沸騰的狂野冒險。」──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蘿倫‧迪史蒂芳諾
「宛若羅密歐與茱麗葉般立場對立的男女主角,在一連串欺騙、陰謀、戰鬥之下,萌發更美麗而浪漫的愛,克服一切。」──《柯克斯書評》
「西奧所描繪的《深淵迷城》世界讓人著迷……本書獻給喜愛鬥智、背叛、心痛與陰謀的讀者!」──《今日美國》部落格「從此幸福快樂」
「儘管只是初出茅廬,西奧‧勞倫斯的文筆無庸置疑。」──《出版者週刊》
「彷彿加了化學藥劑般,這個故事吸引人注意的能力非常強大,它的反烏托邦冒險瞬間就將人帶入情境中。」──《書單雜誌》
「這個故事將背景設定在未來的曼哈頓,情節推展飛快,角色設定卻很完整,種種呈現太令人難以置信!」──《校園圖書館期刊》
作者簡介:
西奧‧勞倫斯Theo Lawrence
生於1984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與朱利亞德學院。曾得過美國總統藝術獎的歌唱獎,並在卡內基音樂廳、甘迺迪中心與外百老匯演出。勞倫斯正在福坦莫大學攻讀文學碩士,住在曼哈頓上西城,公寓裡擺滿臘腸狗的照片。
譯者簡介:
朱崇旻
曾在美國居住九年,以閱讀為樂,現於台北讀生化科技。喜歡翻譯時推敲琢磨的過程,並認為無論是什麼題材的書,譯者都應忠實表達出作者的立場。興趣包含寫小說、武術、室內布置和冬眠。年齡是個謎。
章節試閱
序章
時間所剩無幾。
「拿著。」他將掛墜置於我手心,那玩意彷彿有生命似的,顫動著並散發淡淡白光。「讓妳這樣身處險境,真的很抱歉。」
「就算從頭來過,我還是會選擇這條道路。」我對他說,「重來一千次也不會變。」
他在我脣上印下一吻,一開始動作輕柔,到後來幾近窒息地激烈。雨水從天而降,滲入我們的衣衫,嘩啦嘩啦地傾入這座既酷熱又黑暗的城市中蜿蜒的運河。他的胸膛隨著喘息起伏。警笛及槍響在一幢幢斑駁、潮溼的建築間迴盪。
我的家人正在逼近。
「快走吧,艾麗雅。」他懇求,「趁他們還沒來,趕快走吧。」
腳步聲從後方襲來,話語聲灌滿我的雙耳,無數隻手掐進我的手臂將我扯離他身邊。
「我愛妳。」他柔聲說。
隨即,他們將他強行押走,我抗拒地尖聲叫喚,但一切為時已晚。
我父親自暗影中走出,令人心寒的槍口瞄準我的頭顱。
內心,有什麼東西,炸裂了。
一直以來我都明白,這個故事將徹底粉碎我的心靈。
第一部
沒有勇氣觸碰荊棘者,
從一開始便不應渴望那薔薇。
——安妮‧伯朗特
第一章
我到場時,派對早已開始。
沿著豪華公寓主梯的優雅弧線,我緩緩走下,步入滿是貴客嘉賓的會客廳。房間兩側擺放一瓶瓶瓷質高花瓶,每瓶皆滿溢各式各樣的玫瑰:非洲單瓣白玫瑰、荷蘭的粉紅色洋薔薇、中國的淡黃色香水月季,以及曼哈頓自產的、以魔力染色的玫瑰,其豔麗奪目的色彩幾乎脫離現實。無論望向哪裡,映入眼簾盡是玫瑰、玫瑰、玫瑰──比人還多的玫瑰。
我向後伸手尋求支持,好友琪琪捏了我的手一下,隨即伴著我鑽入人群。我的視線在會客廳中來回找尋湯馬士的身影。他在哪裡?
「希望妳媽不會發現我們遲到。」琪琪邊走邊說,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她那身華麗的及地金色長裙。她的黑色秀髮精緻地燙捲,披於肩後。亮粉色眼影使她的棕色雙眸熠熠生輝。
「她忙著在那邊閒聊,才沒心思管我們呢。」我說,「順帶一提,妳看來美極了。」
「妳也是!可惜妳已名花有主。」琪琪雙眼掃過房裡眾人。「不然我都想把妳娶回家了。」
紐約州參議員、州議會及最有權勢的法官幾乎都到齊了,更別提那些欠我父親──強尼‧羅斯(註1)、或是他先前的政敵喬治‧弗斯特人情的商賈與社交大佬。但他們都不是今晚的重點。今晚,我才是主角。
「艾麗雅!」
我迅速找到聲音的主人。「妳好,迪斯蒙法官。」我朝一名高大的女人點頭致意。她一頭金髮如龍捲風般盤在頭頂。
她對我露出笑容。「恭喜妳!」
「謝謝。」我說。聽說,自從訂婚的消息傳出,整座城市都在歡慶湯馬士家族與我家化干戈為玉帛,時報雜誌甚至要寫一篇關於我這個「政治界名媛、聯合兩派勢力之大家閨秀」的報導——聽我說這件事後,琪琪的嘲笑就一直沒停過。這是我的摯友,政治界名媛。她每次都模仿新聞主播的語調,害我得擺出鬥雞眼、用力拍她叫她停下。
琪琪陪著我四處打招呼,我彷彿開啟自動模式在派對中遊蕩。「謝謝您們賞光。」我對格林龍市長、參議員特瑞克‧傑利頓與瑪里沙卡‧雷諾及他們的家眷說。
「真是場不凡的訂婚派對。」傑利頓參議員舉杯致意,然後說:「不過,妳也是個不凡的女孩!」
「您過獎了。」我回覆。
「聽到妳和湯馬士‧弗斯特的消息時,我們所有人都驚呆了。」格林龍說。
「我這個人就是個大驚喜呢!」彷彿說了什麼幽默的笑話,我笑出聲,他們也客氣地發笑。
從出生以來,我被教養得視交際應酬為家常便飯:練習閒聊、記誦名字,大方地邀請參議員的女兒來家中留宿或參加生日派對,就算她們那些滿臉痘痘、超級討厭的哥哥假裝撞到我、偷吃我豆腐時,依然保持滿臉笑容。我嘆氣,所謂政治界名媛的生活就是如此,琪琪想必會這麼提醒我。
我們沿著人潮外圍行走,路上閃過不少賓客,還有端著一盤盤開胃小菜與喝不完的香檳、穿梭會客廳內的白衣侍者。我再次搜尋湯馬士的身影,卻仍然一無所獲。
「妳很期待嗎?」琪琪問我。她隨手從一個侍者的盤子取了塊迷你羊肉堡,拋進嘴裡。「期待見到湯馬士嗎?」
「如果妳所謂的『期待』是『想吐』的意思的話,那沒錯,我是。」
琪琪笑了,但我是認真的──我全身上下都緊張得發抖。兩週前,我醒來發現自己躺在醫院裡,而且失去了部分記憶,從那天起我就沒見過未婚夫。至於為什麼會在醫院?因為那件「意外」。
遠遠望去,賓客們顯得十分開心,羅斯家的親信與弗斯特家的追隨者相處得很融洽。不過當我仔細觀察,發現幾乎所有人都緊繃不安地四處瞟著,彷彿會客廳裡的客套與禮節隨時會被扔到九霄雲外、兩家人隨時會回到之前的狀態。
敵對。
我們家鄙視弗斯特家,從我曾祖父出生前便是既定事實,作為羅斯家族的一員,就是憎恨弗斯特家及他們的擁護者。
至少,過去是如此。
「艾麗雅?」一名年輕女孩跑到我面前。她大約十三歲,頂著一頭蓬鬆紅髮,額頭灑滿雀斑。「我想跟妳說,妳和湯馬士實在是太高招了!」
「喔……呃,謝了?」
她貼得更近。「那麼多次幽會你們是怎麼做到的?聽說他打算搬到西城來住,是真的嗎?妳──」
「夠──啦。」琪琪移過來,將那個女孩擠到房間角落。「妳的問題比妳的雀斑還多,某方面來說也是滿強大的。」
「那是誰啊?」女孩走後,我問琪琪。
「不知道。」琪琪呼出一口氣。「不過天啊,這年頭女生怎麼都這麼小隻?而且好圓,她根本是顆馬鈴薯,絕對是弗斯特家的支持者。」
我蹙起眉頭,雙手不由自主緊握成拳。這些我從來沒遇過的人似乎對我和湯馬士的熱戀一清二楚,而我卻連我們的初次見面都不記得,更別提自己是如何愛上他的。
我出院回家後才得知訂婚的事,我問母親為什麼湯馬士沒有來我們家、為什麼他沒去醫院探望我。「妳很快就能在訂婚派對上見到他了。」她說,「醫生說妳仍有可能恢復記憶──也許見到湯馬士就全湧上來了。」
於是,我在這裡等待,一次又一次地尋找湯馬士,等待回憶填滿心中的空白。
琪琪大概感受到我的迷惘。「艾麗雅,慢慢來沒關係,船到橋頭自然直。妳之前願意為了湯馬士違抗一切——現在,妳必須相信自己的感情。」
我點點頭,她說的不無道理。但是我無法「慢慢來」,婚禮預計在夏末舉行,眼下已近七月。
賓客在我四周遊走,女性身著豔麗衣裙,大方展現身上的珠寶首飾、刺青與魔力施展的花紋,男性多半身材魁梧、面相粗獷,頭髮向後梳並用髮膠固定。
一位陌生的出眾男士朝我走來,伸出粗糙的手。「阿特‧薩克榮尼。」他自我介紹道。
我頷首,微笑。「艾麗雅‧羅斯。」
他較我年長,臉龐英俊但顯然歷經風霜,頸項的藤蔓刺青向下延伸,左眼上方以藏青色刺了弗斯特家族的家徽──一顆五芒星。「艾麗雅,願妳和湯馬士幸福快樂。」
「我也如此希望。」我半真誠地回答。
他身後站著兩名抬頭挺胸、異常高大的男人,一個黑人一個白人,喉頭的領結一副快繃斷的模樣,頸邊也刺了相同的藤蔓。
「美麗的公主與白馬王子締結良緣,這可不是每天都遇得到的幸運。」薩克榮尼說。
這種說法實在很狗血,但我真心希望他說得是對的──希望,一旦我親眼見到湯馬士,一切記憶都會如泉湧般恢復,我也會滿心歡喜地期盼我們的婚姻。
而不是畏懼。
我回想先前曾吸食過量斯帝嗑──提煉魔力製成的違法藥品,據說能體驗魔巫的感覺,在短暫的瞬間得到巨力、神速以及與世界的和諧。
他們告訴我,父母發現我的時候,我倒在房間地板不省人事,全身宛如上千隻蜜蜂在內部橫衝直撞,不停震動。我到現在還不懂當時自己是怎麼弄到那些藥丸的,明明沒有一個朋友會嗑藥。反正我一定是用了某種方法將藥弄到手,然後立刻搞砸了。真的超級丟臉!凌霄居的有錢人整天都在嗑斯帝嗑,真不敢相信我第一次──第一次!──就倒楣又笨到毀了一切。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還記得,例如上個月某天的午餐(父親從西岸空運過來的牡蠣),還有吃完的隔天早上我做了什麼事(花兩個小時捧著馬桶狂嘔)。那為什麼,我對湯馬士一點印象也沒有?
幸好這件「意外」沒有傳出去,除了我的家人、弗斯特家、琪琪與少數幾個醫生和護士外無人知情。據說在我住院時,湯馬士向我父母坦承我們數月以來的祕密戀情,以及共結連理的計畫。
現在,我就這樣站在自己的訂婚派對上。我理應開心,理應欣喜若狂。可是我能感受到的只有……困惑。我的父母得知這種消息後,怎麼會有如此正面的反應?
「原來妳在這。」父親說。他領著我走到母親身邊,她正與琪琪交談。「親愛的克蘿蒂亞,」母親說,「妳今天美極了,讓人不忍心移開視線。」
「謝謝您,羅斯夫人。」琪琪說,「您才是,隨時隨地都美得沉魚落雁。」
母親緊繃地微微一笑。她的長髮用法式造型盤在腦後,平時金色的髮絲現在以魔力染成鮮豔灼目的紅,臉上濃妝豔抹,成功地引人注目、令人讚嘆。
相較之下,我打扮得十分樸素:淡施脂粉、棕髮吹直後簡單地順在耳後。
「妳看起來不錯,艾麗雅。」父親說。「很體面。」
我低頭一瞥身上的長裙:奶油黃絲綢,露出鎖骨的領口以藍色與粉色小玫瑰裝飾,後側則露背至腰際。我當然看起來很體面,我想對父親說,我是羅斯家的千金啊。不過在他人視線下,我只能有禮地道謝,他點點頭,沒有露出笑容。我父親從來不笑。
母親的眼眸掃視會客廳,瞟過平台鋼琴、幾幅畢卡索藍色時期的畫作,再看向窗簾敞開秀出城市夜景的窗戶,而後雙眼一亮,歌唱般喚道:「湯馬士!到這兒來。」
我的「未婚夫」。
湯馬士是個燦爛迷人的少年,乾淨的古銅色肌膚、旁分的棕色短髮、飽滿誘人的雙脣、與我相像的深色瞳眸,和電子專欄及社交網站上的照片一樣,但本人比起任何觸控式螢幕上的相片更具魅力。他對女孩子的吸引力宛如磁鐵,無可抗拒,凌霄居裡哪個女孩不想和他結婚?湯馬士可說身價上億,甚至未來有機會成為市長。
我胸中開始小鹿亂撞。短暫的一剎那,腦海中閃現了──與另一人手牽手、輕觸嘴脣的吻、一種……溫暖的感覺。
然後,消失。
湯馬士朝我自信地眨眼。現在注視著他,我想我可以喜歡他,即使失去記憶也「應該」喜歡他。於是我戴上面具,露出與父母、湯馬士、賓客們無異的笑容,因為這名少年「一定」是我所選擇的未來──否則我過去怎麼會為了他撇開所有?
「羅斯先生、羅斯夫人。」湯馬士先是與我父親握手,再輕吻我母親的面頰。
這情景怪得不可言喻,小時候我只要說出「弗斯特」三個字,就會被念一頓、關在房裡,但現在……
我長長吁氣。這一切進展得好快。
「艾麗雅。」湯馬士熱切地說。他在我脣上輕輕一啄。「妳感覺如何?」
「很棒!」我回答,將緊緊抓著手提包的雙手挪到身後。我的手在顫抖,我不想讓湯馬士牽住我的手。「你呢?」
他瞇起雙眼。「很好,不過我並沒有像妳一樣──」
「吸毒。」我替他說完,「我知道。」
就這樣嗎?我的回憶呢?我不是應該想起我們的初次會面、戀愛過程還有……可惡,到頭來,我對湯馬士仍是一無所知。
我父母交換了微妙的眼神,無疑在揣測我的思緒。這時候,情況變得更加詭異:湯馬士的父母出現了。
「艾莉卡!喬治!」父親彷彿呼喚最親密的友人,上前擁抱湯馬士的父親。
「這派對@美極了@。」湯馬士的母親對我的母親說。艾莉卡‧弗斯特的長裙與脖頸那串精緻的圓圈刺青是相同的寶石綠。「太令人驚豔了。」
「謝謝妳。」母親硬是擠出笑容回應。
父親從侍者手中接過裝滿香檳的高腳杯,舉杯。「諸位嘉賓!煩請注意這邊。」
父親說話時有種魅力,令人忍不住側耳傾聽,來賓紛紛靜下來轉向我們,角落裡的弦樂四重奏也停止演奏。湯馬士摟住我的腰,我想起自己正在演戲給整座城市最有權勢的一群人看──同時,也演給我自己看。
「我和喬治、我們兩家人向來關係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事。」爸爸說,「不過,這全都即將改變。」賓客們知道他接下來會說什麼,期待地一陣鼓掌。「我跟玫琳達很高興能為各位帶來好消息──我們的女兒艾麗雅,將與這位年輕有為的湯馬士‧弗斯特成親,今日敬邀諸位,與這對深愛彼此的佳偶一同歡慶他們的訂婚!」
這次的鼓掌喝采久久不歇,直到父親揮揮右手示意大家安靜,這莫名地給人一種排演過的感覺。我意識到湯馬士置於我手臂上的掌心,當他用拇指摩挲我的手肘下方,我不禁心跳加速。
「相信大多數的人聽到他們訂婚的消息都相當驚訝,畢竟小倆口一開始是瞞著所有人交往的。但是,他們勇敢坦承相愛,這個舉動對我們產生十分正向的影響:他們的戀愛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兩家之間的恩怨。」
「我們決定放下過去,握手言歡,從此不再相互怨懟。艾麗雅和湯馬士用了最經典、最古老的力量使原本對立的兩家人合而為一──真愛。所以,謝謝你,湯馬士。還有,也謝謝妳,我最寶貝的女兒艾麗雅。」父親俯身在我眉間落下一吻,我在眾人的注目下飄飄欲仙。
這回的掌聲持續得更久,聲音強到如海潮般一波波襲向我和湯馬士。我們高舉十指相扣的雙手,引發無比熱烈的喝采。湯馬士的手心都是汗水。
父親的演說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個詐欺師、恐嚇者、一群匪徒的老大,是掌控半個曼哈頓的政黨領袖,對他來說,「愛」是用以操控弱者的工具。
而現在,他竟然說真愛能戰勝一切。真可笑。
「言至此,我不得不提起接下來這件事。」父親在掌聲逐漸轉弱時接續道,「在外頭,存在比我們任何家族都棘手的敵人,對付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效仿這對年輕人──團結!近來,有個名叫薇蕾‧布魯克斯的激進派魔巫正逐漸擴大勢力,那些住在深淵的非魔巫貧窮家庭,以為她能為他們提供待遇更好的工作,而那些已登記的魔巫自然支持她──因為她是他們的一分子。這個女人威脅到我們在凌霄居建立的生活制度,大家都曉得,自『大災厄』過後,市長選舉便從未有過第三方候選人。」
「所以,今晚除了宣布訂婚的消息,我和喬治‧弗斯特還想讓各位知道,我們將在政治上聯手,在這個受到魔巫威脅的時刻,我們必須團結一致。現在格林龍市長的任期即將結束,喬治與我將在此次選舉支持同一位候選人:格蘭‧弗斯特。」
湯馬士的兄長格蘭在我們一旁現身,向聽眾自信滿滿地揮手。他的長相像成熟版的湯馬士,不過他的頭髮是金色而非棕色,臉龐較為瘦削、陰沉。格蘭現年二十八,比湯馬士年長十歲,但以政治家來說尚稱乳臭未乾。他纖弱的妻子法蘭西絲卡站在斜後方,纖細的手輕搭在他肩頭。
「恭請在場諸位同胞,」父親總結道,「舉杯敬美好未來的開端──敬我的家人、敬弗斯特家、敬這座壯麗蓬勃的城市!」
弦樂四重奏再次演奏悠揚樂章,父親領著母親到會客廳中央開舞,隨之而來的是喬治‧弗斯特與艾莉卡,他們在清空家具的會客廳裡翩翩起舞。
父親的話語不斷迴響於腦海:受到魔巫威脅。
曾經致力使這座城市更加絢爛富強而受人們讚嘆的魔巫,今日卻變成恐懼的對象。一名強大的魔巫若力量不受控制,光是觸碰就足以使普通人類死亡。
我個人無法理解,為何所有人都如此戒備魔巫。二十年前的母親節大災厄──導致眾多無辜民眾喪生的魔巫炸彈攻擊事件──過後,已有法律強制每年兩次抽取魔巫的魔力,讓他們無害於正常人。大多數魔巫與貧民一同居住在城市的低層地帶:深淵,是個太過混亂危險、以致任何凌霄居居民都不會想涉足之處。來凌霄居工作的魔巫則是傭人、侍者或對權力與叛亂沒興趣的公務員,這些人只在乎掙錢糊口。
然而我也明白,並非所有魔巫都對人無害,有的拒絕依法登記及抽取魔力、選擇躲藏在深淵的某個角落。等待、觀察,密謀。
湯馬士的手臂離開我腰間。「我還沒看見凱爾呢。」他說。
「我也是。」我哥哥凱爾最厭惡受人矚目,他絕對不可能出現在派對這種場合,現在大概和女朋友班妮窩在一起。
「想跳支舞嗎?」湯馬士問我。他看來真心想跳舞,況且在這麼多人關注我們的情況下,我也不好拒絕,我將手提包交給琪琪後走至會客廳中央。
湯馬士的手似乎不熟悉我的身體,動作稍微笨拙。我忽然發現自己竟然不知道我們是否看過彼此的裸體,頓時兩頰羞紅。
「那件事之後……我實在對妳放心不下。」他說,帶著我跟隨舞步前後搖擺,他的古龍水帶有杉木清香,以及微乎其微的香草味。四重奏正在拉作曲家葛瑞茲基的曲子,既緩慢又優美。「妳把自己傷得那麼重。」
「除了偶爾頭痛之外,我完全沒事。」──如果忽略未婚夫是個陌生人這個事實。我硬是將那絲念頭埋進腦海深處,任由悠揚的樂音充填我的心靈。若是我一直與湯馬士跳舞,總會憶起第一次與他共舞的情景吧?我們應該一起跳過舞吧?我內心的期盼——這是期盼的感覺嗎?——使肌膚彷彿有電流竄過般微微震顫。湯馬士是個帥氣又明顯對我有好感的單身年輕男子,假若我如眾人所說地深愛著他,那我鐵定非常幸運。
「我們是如何相遇的?」我以旁人聽不見的音量輕聲詢問。
他稍微後退,凝視著我。「妳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搖搖頭。
從小到大,愛情一直是我的夢想,像電視上或者書本中描述的戀愛: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歸宿、真命天子,一生就圓滿了。這就是父母描述的、我和湯馬士的愛情。但是,為什麼湯馬士碰觸我時,我感受到的僅僅是尋常的碰觸?
我一直以為,真愛會燒灼我的身心。
母親出現在我們身邊,一手滑到我們兩人之間。「艾麗雅,請出借妳未婚夫的一點時間,伯克州長想跟他談談。」
湯馬士在我額頭印上純潔的一吻。「我很快就回來。」
我默默目送他們離開。這就是我與湯馬士的未來嗎?正事、開會、兩方父母?我陡然感到胸口太過壓抑,好似禮服尺寸太小。
我需要離開這裡。
我匆匆沿著牆壁走到陽臺門邊,按下觸控面板,它讀取我的生物資訊後,門從我面前消失並重現於我身後。室外熱得猶如隨時會燒起來,我的手臂、頸項與雙腿立刻泌出汗水。
據說造成這種酷熱的,是一場全球氣候危機,全世界的冰雪都在融化,不斷上升的海平面吞噬了南極大陸及全太平洋洲。全球暖化也造就深淵中,那四通八達的運河——曾經是低窪街道的區塊被海水淹沒。科學家說,不久後,海水將淹蓋這整座島嶼。
沒有人知道,所謂「不久」是多久。
我走到陽臺邊緣,放眼望去是華美的凌霄居,距離下方的地面遠得彷彿漂浮海面的城市,不受陸地拘束。下方數十層樓處是光電車的行駛區,一輛又一輛的流線型白色車輛進出車站,在高樓大廈的陰影間看似一點一點的亮光。在魔力尖塔的照耀下,城市映在天際的鋸齒輪廓壯觀非常。這些路燈是一座座聳入雲端的琉璃尖塔,內部盛裝整座城市的能量來源:魔力。父親說,這是那些怪胎唯一有用處的地方。
尖塔的光輝按照某種頻率一明一暗,宛若視覺音樂,幾乎能以「生機蓬勃」形容──至少,比今晚的那些賓客來得生機蓬勃。
我小心翼翼地捲起裙襬,踏上陽臺的鐵欄杆,隨即翻身到另一邊。年幼的我不時會這麼做,放鬆身心。高樓間的強風吹亂我的長髮、干擾我的視野,我雙手緊握身後的欄杆,緩緩、再緩緩地向前傾。下方的黑暗中,一條又一條銀色運河流動著,熾熱狂風不停襲來,提醒我:我為了真愛奮鬥過,並獲得勝利。
再來,只需要找回這段記憶便行了。
我試圖想像湯馬士拉著我的手、我奔進湯馬士懷裡、湯馬士在黑暗的角落或陽光明媚的房間裡親吻我,卻無論如何都做不到。我回首望向會客廳內的派對,從這個距離看去,只能透過掛滿凝結水珠的玻璃門,勉強瞥見一團深色西裝與亮麗長裙。
一陣旋風撩起我的裙襬,布料於我周身飄揚的感覺惹得我笑出聲來。夠了,是時候翻回陽臺上,回到安全的地方。
此時,我赫然瞄見了他——角落裡一張臉。我嚇了一跳。
牆上的燭臺幾乎沒照到他,我認不出他的身分。「哈囉?」我喊道,「是誰在那邊?」
我移動一條腿想跨過欄杆,另一隻腳卻猛然滑落。
就這樣,我從陽臺墜落。
我感受到膝蓋敲到陽臺邊緣時突如其來的疼痛、下顎碰撞欄杆的衝擊、身軀受重力向後拉扯──在最後一刻,我單手搆到一根欄杆,死命抓著。
身體擺動撞上建築側面,我差點鬆手,但我不能放開,我全身懸吊在夜晚的城市上空。我死死捏著欄杆,唯一避免我摔死在數千英呎下的地面上的,就是這五根抓著這鐵條的手指。
手汗使我逐漸滑脫,我的心臟在胸中奮力跳動。我無聲禱告:拜託別讓我死。拜託別讓我死。
然後,那名少年出現了。眼前的淚水模糊了視界,令少年幽魂般忽隱忽現。
「抓住我的手。」他伸手對我說。
「我做不到!會掉下去!」
「我不會讓妳掉下去的。」他告訴我。我眨開眼中的淚水,但依然看不見他的面容,只聽見他呼吸的聲音、語調中的惱怒與恐懼。「妳必須相信我。」
我一手緊緊抓著鐵欄杆,另一手奮力甩向那名神祕少年,他即時撈到我的手將我往上拉起,但我雙腿依舊踩不到陽臺的邊緣。少年與我相觸的肌膚出奇地溫熱,指尖似乎要燙傷我的手。
「很好。」他說,「現在換另外一隻。」
「我覺得我不行了。」我從頭到腳都無比痠痛。
「妳比自己想像還要堅強。」他告訴我。
我迫使自己不向下看,深深吸氣後鬆開緊握欄杆的右手,將它交給眼前的少年。他手腕內側刺了一個星輝圖樣。然後,我的身體上升、上升,越過欄杆。
雙腳接觸到陽臺時,我抽抽噎噎地啜泣起來,整晚積累於內心的淚水泉湧般溢出。「好了,好了,沒事了。妳安全了。」少年輕聲說,即使戶外溫度不知道幾百度、即使我最漂亮的裙子就這樣毀了……我發現自己相信他所說的話。
最終,我感受到他鬆開抱著我的雙手,聽見他離去的足音。這位救了我一命的少年──到底是誰?
我驀然回首,視線四處尋找那名謎樣少年,他卻已然消失,宛如魔法。
這時,一個熟悉的聲音喊道:「艾麗雅?是妳嗎?」是琪琪。
「妳在外面做什麼?」她邊問邊朝我走來,「這地方熱到我快融化了。」
我選擇暫時將適才的經過保密。「只是在想些事情。」我回答。
「那別想了,快來跳舞吧!湯馬士在找妳呢,說你們的曲子開始了。」
「我們有曲子?」我傻傻地問道。
「看樣子有囉。快來。」琪琪催促道。她交還我的手提包。
快走到門邊時,我突然聽見包包裡傳出未曾聽過的碰撞聲,我打開包包一看──包包裡躺著一條我從未見過的掛墜項鍊,雖然銀光閃閃,質感卻老舊。我取出掛墜,忽地一股能量竄上我的手臂,類似記憶的直覺在腦中一閃而逝:這是我的掛墜。
裡頭還有一小張紙條,我將它攤開。上頭的字跡十分陌生,僅有四個字:
回想起來。
序章
時間所剩無幾。
「拿著。」他將掛墜置於我手心,那玩意彷彿有生命似的,顫動著並散發淡淡白光。「讓妳這樣身處險境,真的很抱歉。」
「就算從頭來過,我還是會選擇這條道路。」我對他說,「重來一千次也不會變。」
他在我脣上印下一吻,一開始動作輕柔,到後來幾近窒息地激烈。雨水從天而降,滲入我們的衣衫,嘩啦嘩啦地傾入這座既酷熱又黑暗的城市中蜿蜒的運河。他的胸膛隨著喘息起伏。警笛及槍響在一幢幢斑駁、潮溼的建築間迴盪。
我的家人正在逼近。
「快走吧,艾麗雅。」他懇求,「趁他們還沒來,趕快走吧。」
腳步聲從後方襲來...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