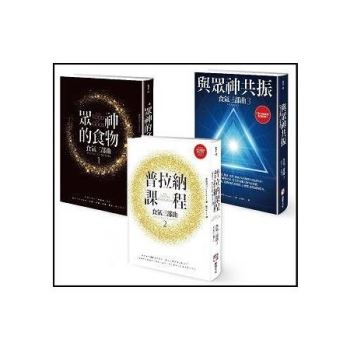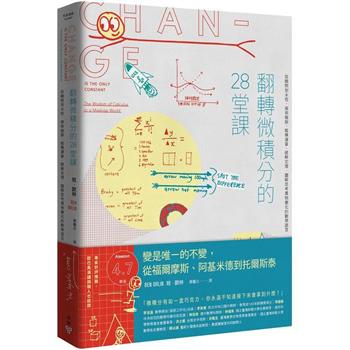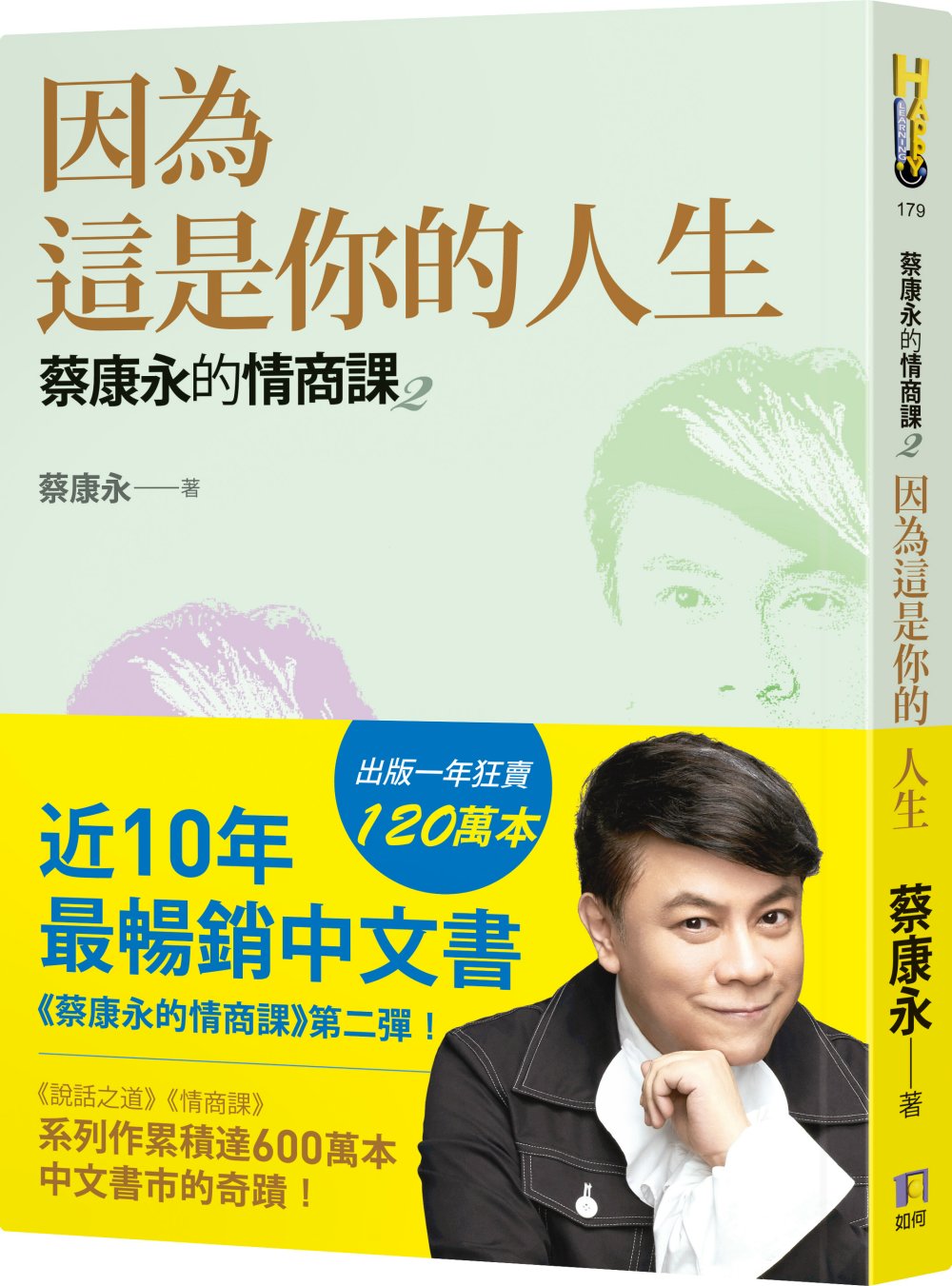對於人權的理解與實踐,
我們落後法國豈止兩百年……
《論特權》是一本改變歷史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催生了著名的《何謂第三等級?》,也推動了法國大革命。本書作者西耶斯提出的口號:「平民是什麼?是一切!」被寫進了《國際歌》。今天的法國中學生,還會在歷史課、哲學課堂上,學習西耶斯的思想。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論特權》明白地指出,特權的本質,是與平民對立的。兩百多年前,這份對於特權的思索,改變了當時的法國;如今,也要翻轉現在的台灣。
不管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都不該回避對於「特權」的討論。因為,你不去影響特權,特權就會反過來影響你。
*
他們用憤怒對待人民,卻把溫柔給了特權階級。
西耶斯觀察到的特權者們,有以下症狀……
• 年輕的特權者們,一長大成人,就可以享有地位與薪俸,有人還抱怨得到的太少!
• 特權者們無法想像,別的家族會跟自己家族一樣優越,因為自己身上這種特殊的品質,只有某些特定的種族才可能擁有。
• 特權者們真誠的認為,人民需要他們和他們的後代,而不是需要處理公共事務的公務員。
• 因為階級的偏見,不斷慫恿著特權者去揮霍金錢,另一方面,特權者又放不下身段,使得他們不能循和一般人一樣的管道來賺錢。
• ……
是時候了!特權者們,退散!
西耶斯是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神父,深諳特權階級的思考模式,因此針對特權階級的思維,批判得鞭辟入裏。他發現,特權者的心態,並沒有因為國難當前而有所轉變,反倒得寸進尺,變本加厲。
西耶斯指出,沒有任何特權的平民,卻肩負讓國家繼續延續命脈的重擔,還要負擔教士、貴族階級所撇下的責任與義務,實在很不公平;平民至少應該與他們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比例相當的民意代表在議會中為自己發言,並有推翻專政與制憲的權力。
當時民意的風向,對於由教士、貴族、平民(亦即前兩個特權階級以外,剩下的人)所組成的三級議會,十分反感。因此西耶斯抓緊這個趨勢,陸續出版《論特權》、《何謂第三等級?》這兩本小冊子,引起社會廣泛迴響,沸騰整個法國。
作者簡介:
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 1748 – 1836)
西耶斯在一個宗教氛圍濃厚的環境長大。父親是稅務官,薪水微薄。家族有一點貴族血統,但過的是平民的生活。他原本希望當個軍人,不過因為體格不好,從軍之路受阻,於是轉為進入教會服務。他在教會工作時發現,由於自己並非貴族,沒有特權加持,所以升遷困難重重,因此開始檢視特權在社會中的作用與影響。
西耶斯是法國大革命的推手,他的政論小冊子《論特權》(Essai sur les privilèges)催生了《誰是第三階級?》(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後者被公認為真正的革命宣言。他在革命期間,也參與了《網球場宣言》和《人權宣言》的起草,與1791年的制憲,在思想或行動上,他都可說是大革命的推手。在經歷過議會議政與行政官職務後,他又與拿破崙合作,發動霧月政變,結束了法國大革命,完整見證了革命的起落。
譯者簡介:
梁家瑜
1978年生於國境之南,未及而立之時歐遊經年。翻譯之餘,偶記雜感,並從事紀錄片拍攝工作。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柯P:「就我觀察,這個社會的病灶在於特權跟黑箱。也就是說,想要這個社會有所改變,就要從這兩點下手。這絕對不是靠誰當選就可以改變的,而需要全民一起,先瞭解到底什麼算是特權,而什麼不算特權,才有可能進一步把它消滅......」
馮光遠:「兩百多年前,他們就注意到特權。特權以各種變貌出現,可是逃不過這些有智慧的眼睛。也瞞不過這些透徹的心。他們追究的精神,讓最冠冕堂皇的特權都無所遁形。兩百多年後,看這小書還是津津有味。總之,你知道越多特權之事,或人性,這本書PH值越低。」
蕭美琴:「特權特權,多少罪惡伴汝以行。欣見紅桌文化將法國大革命的宣導小冊《論特權》重新中譯在台上市;希冀讀者於閱覽本書時,能和我一樣,對平等及人權有更深的體會與省思。」
名人推薦:柯P:「就我觀察,這個社會的病灶在於特權跟黑箱。也就是說,想要這個社會有所改變,就要從這兩點下手。這絕對不是靠誰當選就可以改變的,而需要全民一起,先瞭解到底什麼算是特權,而什麼不算特權,才有可能進一步把它消滅......」
馮光遠:「兩百多年前,他們就注意到特權。特權以各種變貌出現,可是逃不過這些有智慧的眼睛。也瞞不過這些透徹的心。他們追究的精神,讓最冠冕堂皇的特權都無所遁形。兩百多年後,看這小書還是津津有味。總之,你知道越多特權之事,或人性,這本書PH值越低。」
蕭美琴:「特權特權,多少罪惡伴...
章節試閱
說到特權,大家都認為,特權就是給與某些人優惠減免,教剩下的人大失所望。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那麼我們必須承認:特權真是一種可悲的發明!想要摧毀一個社會非常簡單,假設這世界上真的存在一個安和樂利、組織完善的社會,我們只要讓一小撮人不必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再把因這些人而產生的負擔,加到其他人身上,讓他們意冷心灰,就能破壞原本的秩序。這不就清楚說明了,特權的存在,足以摧毀一個社會?
不是我不願意去考察特權的起源、性質與作用,而是這種談法雖然比較有條理,卻很容易老在幾個相同的概念上面打轉。再者,一旦論及起源,不免又要落入「如何證明所言為實」的爭辯,不但枯燥乏味,而且沒完沒了。更何況,大家都知道,只要有心,有什麼「證據」找不出來?如果一定要照這樣談的話,那我寧可替特權假定出一個最純粹的起源。這樣一來,我想就算是特權的擁護者(也就是所有從中獲益的人),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好挑剔的了。
所有特權都是一樣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人豁免於法律的管束,或是得到某些法律未禁止之事的專屬權利。特權的本質,就是要讓某些人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權利,而特權者也就是藉由上述的兩種手段所造就出來的。因此,大家應該能同意,從這兩個面向來掌握主題,最後研究出來的結果,理論上可以將所有的特權種類涵蓋其中。
首先,我們要問:訂定法律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並不是因為一時興起而制訂法律的。法律的目的,無疑是要保障個人的自由及財產,免於受到侵犯與傷害。由這點看來,那些沒有實際的用途,卻剝奪公民自由的條文,已經違背了當初制訂法律的初衷,必須要盡快廢除。
所有法律都出自一條母法,那就是:不要傷害他人(ne fais point de tort à autrui)。立法者把這條偉大的自然法。自然法概念在歐洲思想中源遠流長,通常被視為在主權人民與統治者之上的「更高的法律」。)運用在各式法律條文中,並將其分門別類,使社會能運作得井然有序。這些法律條文也就是所謂的實證法(編註:實證法(loix positives)是人為訂定、且在特定社會內可實行的法律,又稱為人定法。與自然法是相對的概念。)。能夠防止損害他人權益的法律,我們可稱之為善法。但是如果法律不能直接或間接防止損害他人的權益,那麼就算條文中沒有表現出惡意,仍舊是屬於惡法。因為,這些法律條文先是造成許多不必要的限制,因而妨礙了自由;再來,它也擠壓了本來該屬於善法的空間,就算沒有,多少也削弱了善法原有的力量。
法律之外,凡事皆為自由;除了受法律保障的個人事物,其餘皆為公有。
只不過,當權者長期禁錮人民的心智,使得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在社會中真正的地位,也不認為自己有權力廢除惡法。這種狀況實在可悲。人民甚至受到誤導,相信自己不能替自己做主;除非法律有明文規定(不論善法,抑或惡法),否則一概不能插手管事。人民似乎沒有概念,不懂原來「自由」與「財產」是最至關重要的,也是一切的基礎。人類之所以相互連結,是為了長期保護自身的權利,避免遭到惡人算計,以期身體與人格能夠在這樣的保障之下,更積極、更全面的發展,並享受豐富的人生。只是,人民也忽略了一件事,這些因自己勤奮開創出的新風貌,所累積的財富與贏得的社會地位,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屬於自己,絕不能夠當成是由外在權力來施予個人的賞賜。為此,人民建立了監護機構(l’autorité tutélaire)。這個機構的存在,不是要給予人民本來就擁有的一切,而是為了保護人民所擁有的一切。簡言之,每位公民,除了擁有法律明文規定之事的權利,還擁有一項不容被質疑的權利,那就是行使一切法律所未禁止之事的權利
說到特權,大家都認為,特權就是給與某些人優惠減免,教剩下的人大失所望。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那麼我們必須承認:特權真是一種可悲的發明!想要摧毀一個社會非常簡單,假設這世界上真的存在一個安和樂利、組織完善的社會,我們只要讓一小撮人不必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再把因這些人而產生的負擔,加到其他人身上,讓他們意冷心灰,就能破壞原本的秩序。這不就清楚說明了,特權的存在,足以摧毀一個社會?
不是我不願意去考察特權的起源、性質與作用,而是這種談法雖然比較有條理,卻很容易老在幾個相同的概念上面打轉。再者,一旦論及起源...
推薦序
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
:《論特權》推薦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並不是在短暫的瞬間裡,人們就能改變自己的內心,變得盡可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唯有當平等是一輩子的日常現實,而不是少數時刻的遊戲之時,人們才會如此[相互扶持合作]。」
——西耶斯《論特權》
一
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 被思想史家稱為「法國大革命的化身」,因為他在1788-89年間出版的幾本政論小冊子,特別是《論特權》(一七八八)和《何謂第三等級?》(一七八九)這兩篇傑作,不僅預示了法國舊政權(ancien regime)下封建等級制秩序的瓦解與民主平等的新秩序之形成,同時更亦步亦趨地介入了這個過程,成為新興的第三等級革命家在從教士與貴族手中奪回主權,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國民議會中宣布廢除封建等級制,重構法蘭西民族行動的指導藍圖。
如果《何謂第三等級?》排除封建統治階級,確立了第三等級(布爾喬亞)做為唯一民族主體之地位,那麼《論特權》則摧毀了封建秩序的根基,也就是基於身份等級制的特權體系。
舊政權時代的法國社會,基本上是以等級身份或地域區隔的團體(corporate bodies)所組成,而構成每一個身份等級或地域團體認同的核心要素,就是每個團體所獨佔享有的「特權」。在舊政權體制下,這些特權是連結國家與社會的機制,也是政府統治的重要工具。每一新王朝發軔之際,甫登基的國王會發佈詔書重新承認治下各省與各等級擁有之特權,而做為交換,各地域與等級團體則默認新王朝統治之正當性。前密西根大學歷史系教授David. Bien指出,這種封建的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體制發揮了類似英格蘭憲政主義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王權。然而在另一方面,這種基於特殊主義的特權體制也將法國社會切割成不同的身份、等級與地域群體,並且排除了絕大多數的平民,同時也嚴重限制了國家向社會汲取財政資源,進行重分配的能力。大體上,革命前夜的法國是一種建立在社會分裂與間接統治的前現代國家型態,而「特權」就是一種有限度的黏著劑,用利益交換連結了寄生的統治階級,但卻疏離了真正從事生產勞動、創造社會財富的平民。這個社會與政治形構不可能產生盧梭所說的「總意志」 (Volontè générale),只能仰賴君主發揮象徵的統合功能。
二
十八世紀八〇年代大革命前夜,法國國家財政危機迫使路易十六政權思考廢除教士與貴族階級的免稅特權,此舉導致了貴族與教士階級之反彈,而他們維護特權的舉動則促使法國輿論開始重估國家的性質與意義:到底「國家」是一群寄生特權集團的集合體,還是由共同紐帶與理念所結合的共同體?特權在政治共同體中的角色,於是成為這波政治反思的核心問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公共討論的方向就從承認特權作為一種國家治理的原則,轉變為拒絕特權,認為它破壞了共同體的團結。由於辯論導火線是法國財政危機,所以公共討論焦點遂集中在財政特權,並且逐漸形成「特權」與「民族/國民全體(nation)」二元對立的討論圖式。「Nation」一詞成為「共同利益」的代名詞,並且逐漸取代了舊有的「王國」,成為法國人政治認同的核心。最終,一個要求法律之前平等享有權利、負擔義務,並且接受全國統一性施政的公民的民族(civic nation)觀念逐漸在論述交鋒中形成。在這場革命前夜的國家願景辯論中,西耶斯的幾本小冊子,有如美國獨立革命中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一般,點燃了新的法國民族想像之火焰。
新的想像誘發了新的革命性行動,因為平民革命者渴望依照新的願景形塑自己的共同體。要解決財政問題需要召開三級會議投票,然而涉及自身利益的教士與貴族是否應該擁有投票權立即受到質疑。教士與貴族雖然願意放棄財政特權,但卻仍想保有封建政治特權,也就是在三級會議內不成比例的代表權與投票權,而這當然遭致了第三等級的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新生的法蘭西Nation必須在平等、普遍的基礎上才能真正達成整合,繼續維持身分等級制只會造成切割與分裂。做為一個上升的歷史集團(historic bloc),第三等級終究取得了霸權地位,於是依據理論家西耶斯的劇本,在一七八九年六月十日至十七日之間,第三等級單獨召開的會議取代了三級會議,變成了全體國民的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新生的國民會議正式廢止一切封建特權,宣告以平等基礎將全體國民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完成真正的民族整合。做為平等的泉源,以及公民崇高理想與行為之投射對象的「nation」,於是成為克服舊封建典範所造成的切割分裂之統一性理念。這是西耶斯做為法國大革命前期─一七八九年五月到七月的「法律革命(révolution juridique)」─的思想工程師(intellectual architect)事業的高峰。
三
美國政治哲學家沃林(Sheldon Wolin)在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經典《政治與願景》(Politics and Vision)一書中,曾指出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政治思想中蘊藏的未來想像,誘發了政治行動者試圖以行動實現這個想像的熱情,而他們的行動又反過來型塑了下一世代思想家的政治想像。Wolin稱這種政治想像為「建構性願景」(architectonic vision)。西耶斯在革命前夜的幾本小冊子中描繪的舊社會崩解與新秩序誕生的圖像,就是一種典型的建構性願景。不只如此,西耶斯的建構性政治思想所召喚出的現實政治行動(至少到一七八九年六月國民會議成立為止),構成了一種幾近完美的對應關係,而他自己更參與其中,成為第一線的行動者,因此才有論者將他譽為法國大革命之「化身」(personification)。
當然,這種理論與行動的完美合致未必是思想家—行動者所預見或意圖的結果。研究西耶斯的當代名著《資產階級革命的修辭》(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作者蘇威(William Sewell)就指出,西耶斯攻擊的對象其實主要是貴族的特權,並不包含他認為具有一定社會政治功能的教士階級與部分富裕第三等級所擁有的特權,然而八月四日第三等級主導的國民會議卻廢除了所有的特權,遠遠超出了他的原始構想。Sewell認為,這是第三等級對現實的誤認所致:啟蒙運動的功利主義思想使他們將具有一定社會功能的封建特權(如教士與部分第三階級)視為合理,乃至於遺忘其存在,以致於他們竟然誤以為八月四日的決議所廢止的,只是特別顯著而惡劣的貴族階級特權而已。正是在這個集體失憶(general amnesia)的脈絡中,西耶斯有限度的特權廢除論,才如此強有力地捕捉了一七八九年夏天法國人的公共想像,非預期地促成整個封建秩序的廢除。Sewell稱此為「失憶的修辭學」:從舊政權裂縫中探出頭的反叛思想的溫和火苗,經由啟蒙精神的折射,竟然加速擴大燃燒,爆裂出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平等」時代的來臨。
四
然而在二〇一四年的臺灣,在一個後現代的民主社會,如此著意重譯、並且刻意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論特權》—一篇出版於兩百二十六年前法國大革命前夜,批判舊政權封建特權體制的政治論文—到底有什麼用意呢?被大革命魅惑了兩百年以上的西方智者不是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宣告「再見,革命」(Farewell, Revolution)了嗎?
那場激動人心、開創了所有現代政治想像的大革命確實已老——事實上,大革命所開創的一長串現代革命系譜都已逐漸老去,只剩下「What is Left?」的聲音迴盪在所有夢想解放者的靈魂深處。然而歷史無非永劫回歸,終點之後又是起點,一個新的革命情境正在醞釀,這條我們曾以為終於找到的道路開始分岔,終於看到的光亮正在熄滅,終於生根的土地在點滴流失,終於奪回的記憶在日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崎嶇,新的黑暗,再一次的失落,再一次的遺忘,以及漫天的惡業與戰火。
而戰火已經蔓延到臺灣—再度蔓延到臺灣。昔日黨國體制的官僚資本主義所孕生的封建權貴階級,如今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中獲得新生、更加茁壯,並且跨出島嶼,形成「兩岸三地」的跨國權貴資本集團,然後向母體反噬。在形式民主的新遊戲規則下,新生的權貴集團以權養錢,再以錢買權(選票),於是權力生身份等級,身份等級生階級,階級鞏固權力,權力鞏固身份等級,如此權與錢結合,身份等級與階級合體,彼此循環,世代相傳,生生不息,社會流動降低,乃至完全停止,於是déjà vu!—貴族與教士(體制意識型態的生產者)轉世,特權重生。或許我們可以稱這個正在展開的驚人歷史過程為臺灣—以及這整個世界—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臺灣的再封建化,意味著三十年民主化過程形成的社會團結開始因階級與身份等級分化而解體,民主體制受金權世襲腐蝕而倒退,所有進步價值逐步崩解流失…。於是兩百二十六年前大革命前夜法國人激辯的課題,重新浮現在今天的臺灣,質問我們苦惱的靈魂:何謂臺灣?是一塊新買辦特權階級掠奪弱者、剝削自然的不義之地(land without justice),還是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多元、友愛,並且永續保有她美麗自然身影,擁有無窮生命力的,道德的共同體─我們的家園?
這個時候,請讓我們翻開《論特權》陳舊而嶄新的書頁,在字裡行間細細尋找辨識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之路。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晨二時於南港四分溪畔
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
:《論特權》推薦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並不是在短暫的瞬間裡,人們就能改變自己的內心,變得盡可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唯有當平等是一輩子的日常現實,而不是少數時刻的遊戲之時,人們才會如此[相互扶持合作]。」
——西耶斯《論特權》
一
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 被思想史家稱為「法國大革命的化身」,因為他在1788-89年間出版的幾本政論小冊子,特別是《論特權》(一七八八)和《何謂第三等級?》(一七八九)這兩篇傑...
目錄
論特權
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論特權》推薦/吳叡人
譯後記
論特權
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論特權》推薦/吳叡人
譯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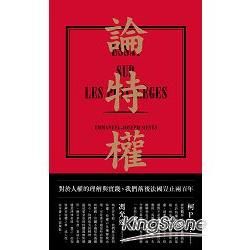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