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色
生命仍有事情值得認真
如我的濕潤也曾吻合你的嘴唇
讓許多簡單譬喻
成為連接世界的卡榫
讓物與物成為意識的延伸
為連綿夜空鑲嵌指引的星辰
在一些悲傷時刻
祈禱彼此的眼底有神
微調節氣的運行
暮春深於想像
剛下過雨的黃昏
風景流連於草木之上
而山川是否永恆
相愛的人又該擁有多少相似成分
甚麼才足以稱為完整
或許無須過問
只須安靜凝視自己的掌紋
二○一七年三月八日
致胡塞爾
所有火焰已指向你
彷彿受罰的普羅米修斯與巨石
而流動的風與我
被置入彼此凝望的眼神間
諸多明滅的事物
難以言說的經驗
一任冬雪覆蓋針葉林端
人們依循林中足跡往內在顯現
難以言說的經驗
諸多明滅的事物
被置入彼此凝望的眼神間
而流動的風與我
彷彿受罰的普羅米修斯與巨石
所有火焰已指向你
二○一五年一月一日
旅
就反覆燃燒散熱
成為黑洞後
才開始試著理解自己的
過去何以是恆星
關於引力,時間從不
等同於記憶
誰將被牢牢抓緊
源於另一個人選擇放棄
而你曾說撫摸
會鑿開體內的渾沌
關於停留
心畏懼孤獨
但同樣需要祕密
在宇宙逆行需要幾倍光速
摺疊兩個座標
唇與唇,愛是痛
最短的距離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獨立
也許只有你在意
淋濕世界的雨是否密集
設想悲傷只是偶然
在我們身上相遇
他們曾經隸屬不同的雲
一起活著的卻未必
能夠一起死去
眼前搭載戀人的長程客運
不知即將前往哪裡
沿途有水花濺起
也許只有你哭泣
確保窗面水滴持續生成
擴散的漣漪
回想那些說過的情話
頻繁依偎的押韻
如今讀來覺得生疏
許多意義來自我們開始學會斷句
神為降生的同類預留空隙
看似相仿卻擁有
各自的核心
二○一七年三月十九日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許嘉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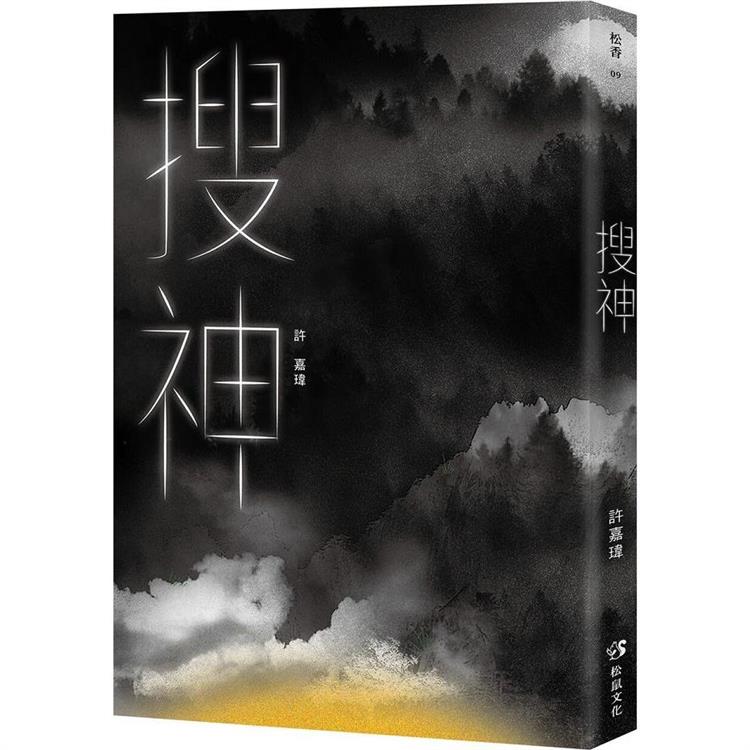 |
$ 276 ~ 315 | 搜神【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許嘉瑋 出版社:松鼠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5-03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搜神
神是恆久,忍耐
又有恩慈神似
不嫉妒。神是不做
害羞的事,自誇不張狂
是我與我們的綜合
神是匱乏也是你
搜索未得者
搜是動詞,神是名詞,在詞彙組成的結構上,與寫詩、度日,並無二致。
《搜神》為許嘉瑋第二部詩集,收錄二○一四至二○二一年的部分詩作,若自前次集結出版算起,與前作已相隔八年有餘。儘管此次詩作皆標注創作時間,彷彿可按圖索驥,然而語言的符號體系本就可能被鬆動,不足為奇。看似斜槓的人與讀來歪斜的詩,是他的日常,既屬時代的產物。
至於字詞間的說與不說,只是提供一種思考與感知的方式,此外無他。
輯一 有意味的形式
對文學而言,如果形式是重要的,那麼萬物之形或許都是神存在的形式。
輯二 眼與心
真正重要的事物,如果眼睛看不到,或許可以用心檢視:詩人之心,包括宇宙。
輯三 詞與物
當我們感知世界,命名便是一種區分物與我的方式。每個字詞,都潛藏足以獨立展開的時空。
輯四 人與天及其他
天何言哉?人們便為仰望和理解的事物發聲。這便是我想向你說明的。
作者簡介:
許嘉瑋
新竹中學畢,先後就讀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現任教於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領域以古典詩詞、中國文學批評為主,近年嘗試跨足至現代詩與網路玄幻小說研究。
興趣廣泛,不務正業,專長是發臉書廢文。曾發表一些學術論文,得過幾個文學獎,自費出版武俠主題詩集《七.武.海》。現階段的任務是在時間夾縫中順利升等。
章節試閱
物色
生命仍有事情值得認真
如我的濕潤也曾吻合你的嘴唇
讓許多簡單譬喻
成為連接世界的卡榫
讓物與物成為意識的延伸
為連綿夜空鑲嵌指引的星辰
在一些悲傷時刻
祈禱彼此的眼底有神
微調節氣的運行
暮春深於想像
剛下過雨的黃昏
風景流連於草木之上
而山川是否永恆
相愛的人又該擁有多少相似成分
甚麼才足以稱為完整
或許無須過問
只須安靜凝視自己的掌紋
二○一七年三月八日
致胡塞爾
所有火焰已指向你
彷彿受罰的普羅米修斯與巨石
而流動的風與我
被置入彼此凝望的眼神間
諸多明滅的事物
難...
生命仍有事情值得認真
如我的濕潤也曾吻合你的嘴唇
讓許多簡單譬喻
成為連接世界的卡榫
讓物與物成為意識的延伸
為連綿夜空鑲嵌指引的星辰
在一些悲傷時刻
祈禱彼此的眼底有神
微調節氣的運行
暮春深於想像
剛下過雨的黃昏
風景流連於草木之上
而山川是否永恆
相愛的人又該擁有多少相似成分
甚麼才足以稱為完整
或許無須過問
只須安靜凝視自己的掌紋
二○一七年三月八日
致胡塞爾
所有火焰已指向你
彷彿受罰的普羅米修斯與巨石
而流動的風與我
被置入彼此凝望的眼神間
諸多明滅的事物
難...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絕地天通的虛構時代──《搜神》自序
◎如果,這裡沒有神
無論哲學或宗教,神的存在形式往往透過文學為載體,但閱讀與創作的人們又有多少曾見過神呢?何況,詩只是諸多文學體製之一種,欲藉此手段「搜神」,未免有點不切實際。儘管不知為何,在這個資訊爆炸、科技掛帥的時代,各種媒體上多的是夸夸而談的「神人」,彷彿我們仍在尚未絕地天通的上古時期。不過「神人」二字終究與「人」沾到邊,人心就是江湖,沾染七情六慾後,或許沒那麼純粹的事物反而更趨近真理。
詩集名為《搜神》,典出東晉干寶《搜神記》。雖說直接忽...
◎如果,這裡沒有神
無論哲學或宗教,神的存在形式往往透過文學為載體,但閱讀與創作的人們又有多少曾見過神呢?何況,詩只是諸多文學體製之一種,欲藉此手段「搜神」,未免有點不切實際。儘管不知為何,在這個資訊爆炸、科技掛帥的時代,各種媒體上多的是夸夸而談的「神人」,彷彿我們仍在尚未絕地天通的上古時期。不過「神人」二字終究與「人」沾到邊,人心就是江湖,沾染七情六慾後,或許沒那麼純粹的事物反而更趨近真理。
詩集名為《搜神》,典出東晉干寶《搜神記》。雖說直接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絕地天通的虛構時代──《搜神》自序
序詩 搜神
輯一 有意味的形式
形式
一隅
水湄
言意
分身
前夕
牆草
可能
容器
物色
三月
水的可發生性
定音
輯二 眼與心
過渡 ...
序詩 搜神
輯一 有意味的形式
形式
一隅
水湄
言意
分身
前夕
牆草
可能
容器
物色
三月
水的可發生性
定音
輯二 眼與心
過渡 ...
顯示全部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