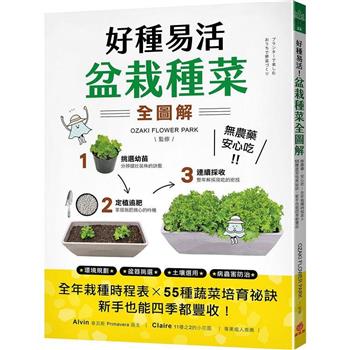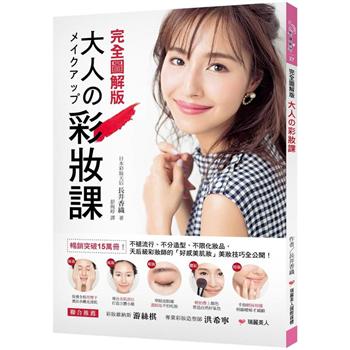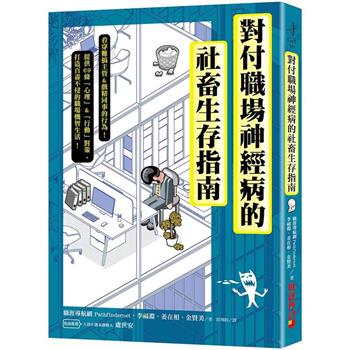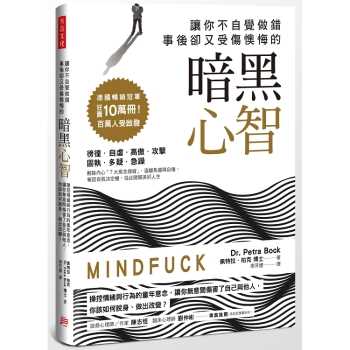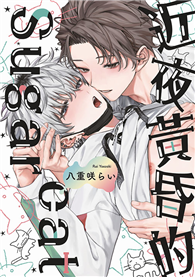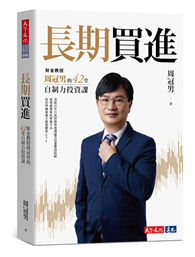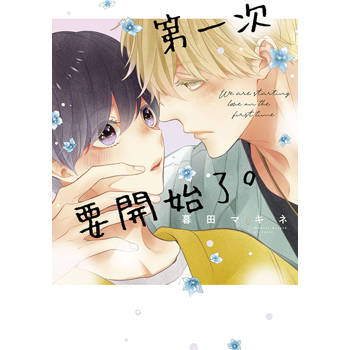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立二十週年了!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學會精心策劃出一趟時間之旅。
旅途中,我們將能一起學習精神分析中關於時間的各種樣貌。
首先是有情的人間在無情的時間中如何遭遇到未知與不可知的驚悚;
接著從網路遊戲的迴圈與文學創作的變遷中,
觀察人們身在其中的時間感知與必然重覆的心智狀態;
再來是透過全球化視野,
從當紅動畫題材與原住民民族誌的角度來探討跨文化的情感與認同;
最後透過文學與精神分析的對話,從佛克里斯到普魯斯特,
解答學會與學不會的時間之謎,將扁平困頓的時間牢籠,轉化為綿延開放的時間。
我們誠摯邀請您一同進入時間的流與轉。
作者簡介:
蔡榮裕
精神科醫師、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督導、《薩所羅蘭》顧問
許宗蔚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英國倫敦 The Tavistock Clinic 兒童青少年實習心理治療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訓練分析師
崔秀倩
殷建智精神科診所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美國麻州綜合醫院精神分析研究中心進修
吳易澄
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暨主治醫師、馬偕醫學院醫學系助理教授、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樊雪梅
英國精神分析學會訓練並認證成人分析師(fellow)、訓練督導級成人分析師(IPA)、兒童分析師(IPA)、兒童青少年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Tavistock)、兒童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博士(Tavistock & UEL)
白美正
Mass. Mental Health Cente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ternship以及Fellowship、Austen Riggs Center Clinical Fellow / Medical staff、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亞太區域籌備會主席、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師、Taiwan Provisional Psychoanalytic Society 會員及訓練精神分析師、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臨床心理學博士
林建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榮譽會員、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楊明敏
精神科專科醫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訓練精神分析師、前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巴黎第七大學精神分析博士
章節試閱
今世輪迴 : 直到一個記憶回來了. /樊雪梅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 T. S. Eliot, 1935, Burnt Norton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 余華,2008
2023年,有個朋友寄了一篇余華的散文給我。我很震驚地發現我居然不認識,也未曾讀過這位已被翻譯成四十幾種語言的華文作家。即便年輕時,透過報章雜誌,熟知張藝謀導的同名電影「活著」,我亦未曾展開閱讀余華之旅。
朋友寄給我的這篇散文〈一個記憶回來了〉,深深地打動我。它述說了歷史創傷帶給人的影響,余華的經驗呼應著我的經驗,它同時也述說了我在精神分析裡的體會,以及我感興趣的、與我切身相關的東亞近代史。
這篇省思自身創作風格之轉變的散文深具情緒力道,同時也強而有力地支持了佛洛依德對驅力的觀察:驅力具強迫重覆之特質。此種強迫特質在人處理創傷時,一覽無遺,即:無法消化及新陳代謝的創傷經驗,如同異形,封存於心智中,以不斷重覆的方式證明其存在。時間的流逝對這樣的經驗,毫無影響力,它無視於過去、現在及未來。也可以說,時間以迴圈的方式進行,「過去」、「現在」及「未來」堆疊,在每一個時刻並存運行著,人的心在其中不間斷地承受已經過去、同時正在發生的苦難,因而影響著個人對自身未來的感知。
首先,要與各位分享余華的這篇散文。
2008年余華寫於臺灣版《呼喊與細語》(麥田出版社)的序文裡,談他十多年來在接受訪談時,不時地被問到的,其寫作風格的轉變;事實上,根據這個問題而出版的期刊論文,及碩博士論文不計其數,每位研究余華的學者、文學愛好者,根基於不同的假設提出不同的分析與暫時性的結論。余華寫道,
「潘卡吉.米什拉(Panjak Mishra, 印度作家)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余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余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的都寫了,不該寫的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我覺得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余華打聽另外一個余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余華為何失蹤了?」
試圖分析余華創作風格之轉變的,還包括許多臺灣的研究生、文學研究者、評論家,王德威是其中之一。王德威為余華在臺灣出版的《許三觀賣血記》寫序文,標題為「傷痕即景、暴力奇觀」。文章從余華在1986年於《北京文學》發表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寫起,也談其創作風格於九零年代的改變,他寫道,「九零年代以來,余華創作了數部長篇,如《呼喊與細雨》(1991)、《活著》(1992)等,在其中他對暴力的辯證執迷如故,殺氣卻逐漸退去,新作《許三觀賣血記》(1995)尤其顯現了此一特徵。」
王德威好奇,已經被余華作品養成了嗜血胃口的讀者,面對他的轉變要如何因應?
我這個讀者,是先被余華的散文〈一個記憶回來了〉吸引,而開始閱讀《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及《呼喊與細雨》。被這三部長篇小說感動的我,則完全無法閱讀余華早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因為其中的血腥和暴力如此真實而令人難以忍受,更無法消化。
在他1988年出版的短篇小說《現實一種》裡,余華描述兩個兄弟,山峰與山崗,和妻子與兒子兩家六口,與老母親同在一個屋簷下過日子。一日,兩對夫妻去上工了,家裡只剩兩個小孩和一個只在意身體痛楚的老人。兩個小孩,堂兄弟,一大一小,大的四歲,小的是個還待在搖籃,但已會笑、會與人互動的嬰兒。余華描述大小孩百無聊賴之下,捏了堂弟豐腴的臉頰,惹得堂弟大哭,因而興奮起來,想起見過父親打母親巴掌的場景如何讓他興奮,於是開始賞他堂弟巴掌,堂弟放聲大哭,讓他更加興奮,狠狠地連續打了堂弟幾個巴掌。但嬰兒的哭喊漸漸出現重覆的樣貌,不再新奇,所以大小孩走出屋外閒望,看見了有趣的事物,想起堂弟,想讓堂弟也看看;於是進屋把堂弟抱到屋外,一起閒看著有趣的事物,看著看著,他覺得手酸,忘了手上抱著嬰孩,把手一放,輕鬆了,又端看了一會兒,就回屋裡去。沒多久才想起堂弟,出門找,看見堂弟躺在地上,頭旁有一攤血,他看見螞蟻走過,被血困住,他看見一隻螞蟻爬進了血流出來的洞......。
接著是余華詳細地描繪孩子的奶奶看見嬰兒躺在地上流血的反應,孩子的母親上班回來的反應,他的父親回來後的反應,最後,意外殺了堂弟的四歲小孩的父親 —— 山崗,在抵擋無門後,把自己的小孩交給了死了小孩的父親 —— 山峰處置。死了小孩的父親要求這失手殺了人的小孩把地上的血舔乾淨,山崗要他照做,於是四歲小孩上前,跪在地上舔血,而余華以全知觀點描述著小孩舔血的感受......。
我是看到這兒就沒辦法再往下看了,甚至開始想像,也許三十多年前的我也曾試著要閱讀余華吧?也許是我遺忘了,之所以沒有成為余華的追隨者是因為其噬血的程度,遠超過我能承受的吧?三十多年後的我,還是無法承受這樣魔幻寫實般的故事。
王德威則列舉數則余華的短篇小說,說明余華的這個時期的短篇小說「暴力不需要藉口,它以一種純淨的形式存在於生活實踐中,彷彿就是吃飯穿衣的一部分。一種佛洛依德式的『家常的恐怖感』(uncanny)縈繞不去。」
中國文學評論家洪治綱教授於200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了余華於1986至1989三年間創作的八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多達二十九人。
這個血腥暴力的余華於九零年代轉型而成為堅忍的余華。究竟這個「血腥暴力」的余華到哪兒去了呢?眾說紛云。連余華自己也能發想出「眾說紛云」的答案,甚至擔心自己是否忽略了某種可能的解釋,而沒完沒了地生出族繁不及備載、無窮無盡的可能答案......,直到2008年的這篇散文 —— 《一個記憶回來了》,余華提出了「不具權威性」的「正版」解答。文中,他說,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童年、青少年時期,因身處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漫延時,所親眼目睹的「暴力血腥」說起。不過,在說故事之前,他強調,
「所有關於我的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逕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和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給予了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了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更多的作者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接著他提出不具權威性、純屬個人的發言,說明八零年代血腥暴力的余華為何轉成九零年代堅忍溫暖的余華。首先,他的父母是外科醫師,他與哥哥在醫院裡長大,經常目睹蒼白的臉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也習於沾滿血跡的紗布。連他們的父親也時常穿著沾有血跡的白袍,呼喊著他們兩兄弟去吃飯。
然後,他相信在八零年代寫下了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主要源自於童年及青春期時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結束時,他高中畢業。這段期間,他目睹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他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小鎮裡,不斷地上演著公開批鬥、公審、判決,以及槍決。
當小鎮有人要被處決時,所有小孩與上千的小鎮居民興奮地趕到刑場(杭州灣的北沙灘或南沙灘)等著觀看。有時跑錯刑場還覺得遺憾。孩子們被這些殘忍血腥的現場吸引著,目不轉睛地看著、看著、看著。看人的手如何被手銬扣在背後直到發紫壞死,看著即將被槍決的人跪在地上,在一顆小小子彈穿過其腦袋後,倒在沙灘上......。
執行槍決的軍人,為了確定犯人已死,還會走上前去,將死去的人翻成正面。於是余華目睹那被子彈毀成一片血肉模糊的臉。血淋淋的、令人驚懼的場面,讓人無法將視線轉開,興奮與恐懼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身體經驗。這是余華從七歲到十七歲的日常。
1986年,余華26歲,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
「小說裡的敘述者『我』獨行在山區的公路上,天色已暗,投宿無門。強搭上一部載滿蘋果的卡車,沒走多遠,車又拋錨了,正在一籌莫展之際,附近的農戶開始出現,搶走了蘋果還打傷了敘述者。運蘋果的司機非但不為丟掉的蘋果操心,反而趁火打劫,把敘述者的小紅背包搶了就走。故事末了,敘述者,『我』,躺在動彈不行的汽車裡,想起那個『晴朗溫和的中午』,父親準備了個小紅背包讓『我』出門。」
人生莫明其妙之無意義、無章法、無目的,充份展現於余華筆下。殘酷的命運顯得如此雲淡風清,讓人不由地想到佛洛依德對人生和人性的悲觀看法。
接下來的三年,余華寫下了大量的血腥和暴力,難以自拔。他寫道,
「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睡著後,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我在夢裡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臟狂跳,半晌才回過神來;謝天謝地!原來只是一個夢。可是天亮之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
如此周而復始,余華感覺到夜裡的「夢是白日在文字裡殺人的報應」(也是一種願望實現 —— 作者覺得自己罪有應得)。如此三年。他感覺到「自己的精神狀態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
就在此時,他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他說,「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真實的記憶回來了。夢裡的他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他中學操場的主席台前沿,台下人群烏七八糟,他聽見喇叭裡響著批判的聲音,控訴著他的種種罪行,最後的判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語音剛落,一支步槍就對準了他的腦袋,砰地將他擊倒。但他卻站了起來,他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敲破的雞蛋,蛋黃和蛋清都流出來了,可是他竟向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他衝著對方喊叫:「他媽的!都還沒到沙灘呢!」
他從夢中驚醒,大汗淋漓、心臟狂跳。他不再慶幸這只是個夢,他開始想起一段記憶。中學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慘白的雙手,載著軍人和犯人的卡車,沙灘上的槍決,被擊碎的腦袋,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他眼前重複展現。余華自問,為何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他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
這天之後,他告訴自己:以後不要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余華告訴我們,他相信當時的自己已走到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這個夢,如果沒有想起那段記憶,他會仍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
「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複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複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
昇華後,帶來毀滅的藝術創作
大多數人會同意,文學創作本身是一種昇華。但余華在1986 – 1989 之間的小說創作,似乎是毫無昇華效果的藝術創作;反覆地在小說裡殺人,更像是他目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之創傷的再現,甚至是「以暴治暴」,將暴力血腥家常化、極端化到異常歡快(perversion)而形成一幅不再被暴力血腥宰制而恐懼不安的幻像。
人命渺小如螻蟻,任人蹂躪宰割;人命渺小如螻蟻,任余華蹂躪宰割。
余華在早期創作裡的殺人無數,是人的心智企圖處理那無法消化的身體經驗的一種方式。王德威說,余華不只是在書寫血腥及暴力,他的文字本身就是暴力。這是一種更直接了當的成為攻擊者,作者認同攻擊者,重覆地以文字殺人,為的是取得掌控權。同時,他於這段時期所做的被追殺的夢顯示他的受害身分 —— 目睹血腥暴力者所承受的創傷不亞於直接受到暴力對待的人,就如同目睹家暴的小孩,其所承受的創傷不亞於直接受到暴力對待的人。在這個過程裡,作者被封存在文革的創傷經驗裡,過去、現在、未來堆疊成此時此刻,以現在進行式同時發生。噬血的讀者似乎在閱讀中,處理著人性深層的暴力與血腥衝動,追殺者與被追殺者是同一人,是自己的一部分殘害著另一部分,同時慶幸著,「沒死!」如此輪迴著潛意識裡偏執分裂的幻想。創傷未曾停歇,只是呈現或未呈現,及如何呈現的差別。
作家 Al Alvarez 於1990年出版的《野蠻的上帝:對自殺的探究》(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一書中思考他的詩人朋友Sylvia Plath 自殺身亡帶給他的沉痛衝擊時,如此寫道:
「對藝術家本身而言,藝術不必然具有療癒效果;表達幻想並不必然帶來情緒疏緩。相反地,因著某種創作的倒錯邏輯,正式地表達(即,藝術創作)本身可能只會讓被挖掘出來的(創傷)素材更垂手可得。而在藝術創作中處理這些材料可能讓他又再次經驗該創傷。對藝術家而言,自然(或譯為「事物的本質」)常常模仿藝術。或說,當藝術家舉起鏡子面向自然時,他發現了自己是誰、自己為何;然而發現自己是誰、自己為何,可能徹底改變了他,以致於他成了那映照出來的影像。」
“For the artist himself art is not necessarily therapeutic; he is not automatically relieved of his fantasies by expressing them. Instead, by some perverse logic of creation, the act of formal expression may simply make the dredged-up material more readily available to him. the result of handling it in his work may well be that he finds himself living it out. For the artist, in short, nature often imitates art. Or, to change the cliché, when an artist holds a mirror up to nature, he finds out who and what he is; but the knowledge may change him irredeemably so that he becomes that image.”
藝術家、詩人在昇華其慾力後,毀滅力量可能被釋放,因而走向暴力攻擊與毀滅 —— 毀滅自我。讀者可能會很意外,Freud早於1923年就如此分析昇華可能帶來的後果之一:
「面對兩股本能驅力,自我的態度不是中立的。透過認同與昇華,自我協助了本我當中的死驅力,讓死驅力控制了力比多/慾力。自我因而有可能變成死驅力作用的對象,而導致自己的滅絕。」「透過昇華,自我將生、死驅力鬆綁,釋放了超我中的攻擊驅力,自我隨之掙扎對抗慾力,這使得自我陷入被不當對待及死亡的危險。自我因而面對被自己的作為所摧毀的命運。」
“Towards the two classes of instincts the ego’s attitude is not impartial (neutral). Through identification and sublimation the ego gives the death instincts in the id assistance in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libido. This makes the ego at risk of becoming the object of the death instincts and of itself perishing.” ….“By sublimation, the ego defuses the instincts and liberates the aggressive instincts in the super-ego, it then has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libido and this exposes it to the danger of maltreatment and death. The ego therefore faces the fate of being destroyed by its own product.”
「我們內在所成就的,將會改變外在現實。」(What we achieve inwardly will change outer reality.)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如是說。同樣地,人心內在未能消化整合的破碎,亦將使自身所處的外在世界持續破碎。
「我相信,藝術是醒著時做的夢,想像能橋接夢與現實,並讓我們透過不真實的窗鏡以一種新的方式望見並理解真實。」
“I believe that art is a waking dream, and that imagination can bridge the gulf of dream and reality and allow us to understand the real in a new way by seeing it through the lens of unreal.”
余華早期的短篇小說是「醒著時作的夢」,頑強地重覆著封存的創傷經驗,以渲染的手法,傳遞情緒經驗裡的真實。然而,此種頑強、誇大地重覆,無法成就任何救贖。真正的救贖來自一個結束輪迴的夢。
余華究竟為何能有這樣一個夢來結束其心智世界裡的創傷輪迴?在不斷地殺人與被追殺的歷程中,究竟是什麼樣的機制,讓余華做了一個讓記憶回來的夢?我們大概永遠也無法知曉。潛抑的心智,終究是找到了出路。也許,不斷書寫的過程雖然呈現了心智的頑強重覆,也還是營造了「逃脫輪迴」的機會? (“The inner causes of repression and sublimations are quite unknown to us.”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p.239)
九零年代開始,余華改變了,1991年出版的《細雨與呼喊》呈現了改變後的樣貌。自傳體的小說情節裡,陳述著暴力血腥的源頭。一個成長中的小男孩,在兩個家(生父與養父)之間,無家可歸;一個尋找父親的男孩在兩個父親之間,不斷地失去父親。追溯童年生活裡親子之間、手足之間,鄉里內人我之間的詭譎人際,似乎提供了作者(與讀者)不同的情緒環境,讓心智可以展開對創傷的新陳代謝。
……(待續)
今世輪迴 : 直到一個記憶回來了. /樊雪梅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 T. S. Eliot, 1935, Burnt Norton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 余華,2008
2023年,有個朋友寄了一篇余華的散文給我。我很震驚地發現我居然不認識,也未曾讀過這位已被翻譯成四十幾種語言的華文作家。即便年輕時,透過報章雜誌,熟知張藝謀導的同名電影「活著」,我亦未曾展開閱讀余華之旅。
朋友寄給我的這篇...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