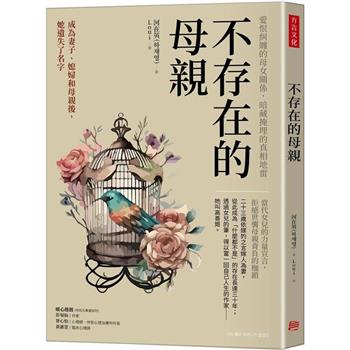所謂「互斥」,就是「互相排斥」,這是依不同文化系統中,藝術發展的可能表現形式來分辨,因此它也涉及影像、文字與終極信仰彼此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從作品的角度來說,此一模式站在「思想意念」的延展觀點,探究讀者透過相互矛盾或相互解構的圖文關係,重新建構意義或主題的過程。(陳意爭,2008:219)
與影像相比,聲音(字幕)可以對比使用(矛盾的組合)。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的聲音和影像的內涵是對立的。訊息是隱藏的,要較深入了解,觀眾的注意力收到刺激或強化(震撼效果),想像力受到激發,就一定會有反應(「半開放」式訊息)。其危險的是,在詮釋可能發生誤解,觀眾可能只了解兩種語言中的一種。事實上,同時刺激兩種感官是比較難以處理的(特別是當兩種同時發出的訊息不一致時)。(G. Betton,2006:47)
當影像與對話間有矛盾時也製造奇特的效果:如在《帶瘡疤的人》(L’Homme à la Cicatrice)一片中,一個人物敘述他的過去(用旁白方式),但映出的畫面與他的敘述卻是兩回事:謊言被拆穿了。(G. Betton,2006:49)
在老掉牙的愛情片中,常常可以聽到男主角或女主角對對方說「我對你(妳)沒感覺了」這麼一句話,當此話一說完,通常劇情不外乎兩種發展:第一種,說者是發出內心的肺腑之言,鐵了心的要離開對方,然後沒有任何遺憾地頭也不回的走了,這種沒有任何虛假,說跟做(想法、行為)也沒有絲毫衝突,屬於此章第二節論述過的「互證」部分,就不多作探討;第二種情況則是,劇中角色雖說了此話,但畫面中的他(她)轉身或離開後,不禁淚流滿面,內心十分不捨,但可能是為了替對方利益著想等目的,不得不讓對方對自己死心,寧可自己悲痛欲絕,也要出此下策,嘴巴雖說沒感覺,但內心還是依舊牽掛著對方,這種口是心非或者說一套做一套的劇情就是「互斥」最簡單易懂的例子。
電影《驢子巴達薩》中有一段是這樣表現的:
吸吮母奶的驢頭近景,一隻雪白的手從上而降入鏡並撫過整個頸鬃時,鏡頭逆向朝手的主人小麗莎往上移動,直到我們看見她的弟弟和父親。伴隨這個鏡頭的對白(「我們必須這樣做」──「把牠給我們」──「孩子們,這是不可能的」),一直不讓我們看見道出這些字詞的嘴巴:小孩轉頭被對觀眾和父親說話,而回話時他們的身體則擋住父親的臉。接下來熔接到另一個鏡頭,呈現出與這些話與內容相反的鏡頭:同樣被對鏡頭,父親與兩個小孩帶著驢子輕快地下山。隨後則熔接到施洗驢子的鏡頭,一個讓我們只看到驢頭、男孩倒水的臂彎和手持大蠟燭的小麗莎半身的近景鏡頭。(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2011:34~35)
從布烈松的「影像」來看,重點不在於那一隻驢子、兩個小孩和一個大人,也不只是近景景框的技術和攝影機運動,或是擴大這技術效應的熔接;而是連接或切離可見與其意指、話語與其效應的各種操作,它們製造期待也偏離期待。這些操作並非源自電影媒介的性質,它們甚至與慣用手法之間保持著某種系統性落差。(洪席耶,2011:35)這種落差給予觀眾一種不按牌理出牌的無限的想像空間,就像心理學家皮亞傑(Piaget)提到的失衡與平衡的概念:人們收取到的新經驗倘若和舊經驗有所衝突,無法同化時,內心會感到失衡狀態,基模(認知結構)需經過調適歷程後,達到新的平衡,這種「平衡作用會產生需求,激勵個體解決新舊知識的不一致,提高知識的層次。」(程薇,2010:2-8)如此一來,反而更能抓住觀眾的胃口。
中國禪宗始祖《達摩祖師傳》故事中的某天下午,四位僧人要入靜室靜坐三日三夜,進去之前,帶頭的師兄還先聲明入了靜室不能說話的規定。打坐到了半夜,忽然油燈滅了……
僧人甲:啊!油燈滅了。
僧人乙:你為什麼說話?
僧人丙:我們不能說話。
僧人丁:嘿嘿!只有我沒說話。
這時達摩磨起瓦來……
僧人丁:大師在做什麼?
達摩:你們在做什麼?
僧人丁:我們坐禪成佛!
達摩:我磨瓦成鏡。
僧人丙:磨瓦豈能成鏡?
達摩:既然瓦不能磨成鏡,那坐禪又豈能成佛呢!
僧人乙:那怎樣才能成佛?
達摩:要知道佛並無一定的形態,而禪也並非坐或臥,你們只知道打坐而 不知道為何打坐,這樣便永遠不見大道。
僧人甲:那怎樣做才能見大道呢?
達摩:從根本上修。
僧人甲:什麼是根本?
達摩:心為根本。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一切善惡,皆由心生,如果連這個道理都想不通,只在表面上下工夫,徒然浪費時間。
從這段簡短的對話當中,可以發現兩個互斥的地方:第一,當僧人丁聽到其他人開口說話破了功而沾沾自喜的說「只有我沒說話」的同時,其實自己同時也違反靜室不能說話的規定了;第二,四位僧人既然要打坐靜心,何必執著於打坐之相的坐或臥?既要修練成佛,就要能夠放下對於一切事物的執著,才能解脫,否則一心欲要藉由打坐成佛其實是在殺佛了。
另一幕是梁武帝召見達摩要討論佛理的場景……
梁武帝:自朕登基以來,修佛寺,造佛像,抄寫經卷,供養僧侶無數,敢問大師,朕有何功德?
達摩:無功無德。
梁武帝:啊?
達摩:這好比隨形的影子,說是有,實際上卻是沒有。
梁武帝:那麼做什麼樣的事,才算有功德?
達摩:潔淨圓滿的得道者,才算有。這種功德世上是求不到的。
梁武帝:請問大師,這世上有沒有佛?
達摩:沒有。
梁武帝:身為僧人你可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達摩:不知道。
梁武帝:真是話不投機,來人,送客!
從梁武帝一開口,詢問達摩自己做了這麼多善事有無功德的同時,就違背了修行成佛的真正宗旨,要知道行善是要無所求的,更不是拿來說嘴,一但有所執著而起心動念,成佛也就離你越來越遠。
還有一幕是空智大師與其師弟們步行街上,路人紛紛向其行禮問好……
師弟:師兄大名遠揚,真是德高望重。
空智:我們潛修佛法,不應有得失之心,貪圖名聲,就會有喜怒哀樂,出家人應超越善惡得失,才可四大皆空。
此時路經達摩所處的客棧,聽到路人談論達摩佛法高深莫測,起了比較之心,前往拜訪達摩討教佛理……
空智:這位是達摩大師是吧!貧僧空智,佛理膚淺,想請大師指點!
達摩看其一眼,不發一語,只是微笑……
空智:心、佛以及眾生,三者都是空,現象的直性是空,無聖無凡,無施無受,無善無惡,一切皆空,對不對?
達摩突然拳打了空智的頭一下……
空智:你為什麼打人呀?
達摩:你既然說一切皆空,那何來痛苦?看那看不到的東西,聽那聽不到的聲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
從這段畫面來看,雖然空智大師嘴上說不應有得失之心與貪圖名聲,但卻表現出一臉驕傲得意的面容,可見是多麼享受高高在上受人朝拜的喜悅,明顯與自己言論相違背,也就是因為有得失之心,才會故意到達摩面前討教佛理,說了一大堆佛理,無不就是要向大眾展現自己對佛法的了解深厚,殊不知禪宗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凡事都不能執著,才能「解脫成佛」。從《六祖法寶壇經‧定慧品》中的一段文字,關於觸發領悟佛境界的意識作用說明,會有更清楚的了解: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往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往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往,即無縛也,此事以無往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清靜,此是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佈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所以立無念為宗。(宗寶編 ,1974:353上)
相較於禪宗式的互斥,佛教式的《春去春又回》也有這麼一段互斥表現。在《春去春又回》的春階段中,調皮的小和尚分別將魚、青蛙與蛇都綁了小石頭,並開心的笑了,老和尚只是站在高處看待事物發生,並沒有立即阻止。隔天,睡醒的小和尚身上被老和尚綁了一塊石頭而寸步難行,老和尚要求小和尚須放了動物們才能將身上的石頭卸下,並告訴小和尚:「要是有任何一隻動物死了,這塊石頭將壓在你心上,直到你死為止。」最後,青蛙還活著,但魚死了,蛇也死了,小和尚難過的哭了。
在這段劇情裡,從小和尚開始調皮的將魚绑上石頭,背景聲音傳來清楚的誦經聲,直到小和尚虐待完蛇結束,誦經聲也才一併結束,隨然從頭到尾沒有看到字幕,但誦經是一種口說語言,經文也有其文字,所以在此將其同等於文字;而這種誦經的文字不外乎是用來勸人向善,是一種正面的能量,與虐待動物甚至最後導致動物死亡的負面行為形成「互斥」對比,且使觀眾對於虐待動物這種行為有更強烈的反感。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許瑞昌的圖書 |
 |
$ 180 ~ 216 |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關係探討
作者:許瑞昌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5-04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電影影像與文字的關係探討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關係探討
隨著人們越來越注重休閒娛樂的同時,電影產業也跟著不斷蓬勃發展。當我們欣賞電影時,除了影像與聲音的雙重刺激外,電影字幕的輔助認知作用也不容忽視,但對於電影編導來說,字幕還具有布局的作用存在,這是一般大眾鮮少關注的。
本書建構一套電影影像與文字的關係理論,以深入淺出方式帶領讀者對《羅生門》、《送信到哥本哈根》、《小活佛》、《暗戀桃花源》、《班傑明的奇幻旅程》等多部電影中的影像與文字的關係有另一層面的認知:分析影像與文字間的四種定格關係,以及流動影像與文字間的三種辯證的關係;並進一步比較其在三大文化系統與學派審美類型的差異;最後,將探討所得成果,提供給語文教育、電影編導、電影交流另一項參考方針。
作者簡介:
許瑞昌,1986年出生,臺灣澎湖人,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畢業,對於電影藝術有種莫名的熱愛。電影讓人哭、讓人笑,彷彿自身經歷了一場非凡的人生旅程。對我來說,一部好電影除了百看不厭外,還得具有讓人再三回味的特質。
章節試閱
所謂「互斥」,就是「互相排斥」,這是依不同文化系統中,藝術發展的可能表現形式來分辨,因此它也涉及影像、文字與終極信仰彼此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從作品的角度來說,此一模式站在「思想意念」的延展觀點,探究讀者透過相互矛盾或相互解構的圖文關係,重新建構意義或主題的過程。(陳意爭,2008:219)
與影像相比,聲音(字幕)可以對比使用(矛盾的組合)。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的聲音和影像的內涵是對立的。訊息是隱藏的,要較深入了解,觀眾的注意力收到刺激或強化(震撼效果),想像力受到激發,就一定會有反應(「半開放」式訊息)。...
與影像相比,聲音(字幕)可以對比使用(矛盾的組合)。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的聲音和影像的內涵是對立的。訊息是隱藏的,要較深入了解,觀眾的注意力收到刺激或強化(震撼效果),想像力受到激發,就一定會有反應(「半開放」式訊息)。...
»看全部
作者序
1985年第一部無聲無字的黑白電影一上映,就造成人類的大轟動。隨著時代的進步,電影工業也跟著蓬勃發展,從無聲到有聲,黑白到彩色,甚至傳統平面影像進化到這幾年3D電影的熱銷,都不難看出電影的無窮魅力。電影字幕的出現,原本只是輔助我們對影像的理解,到後來變成布局的手段工具,為一重要現象,但卻很少有人關注。因此,本研究願意率先來探討此一課題,試為分析出定格影像與文字間的互證或互釋或互補或互斥的關係,以及流動影像與文字間的唯物辯證或唯心辯證或互相制約辯證的關係;並進一步比較其在三大文化系統與學派審美類型的差異...
»看全部
目錄
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其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影字幕
第二節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關係
第三章 電影影像與文字定格的多重關係
第一節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定格範圍
第二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證關係
第三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釋關係
第四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補關係
第五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斥關係
第四章 電影影像與文字流動的辯證關係
第一節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流動範
第二節 流動影像與文字的唯物辯證關係
第三節 流動影像與文字的唯心辯證關係
第...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其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影字幕
第二節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關係
第三章 電影影像與文字定格的多重關係
第一節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定格範圍
第二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證關係
第三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釋關係
第四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補關係
第五節 定格影像與文字的互斥關係
第四章 電影影像與文字流動的辯證關係
第一節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流動範
第二節 流動影像與文字的唯物辯證關係
第三節 流動影像與文字的唯心辯證關係
第...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許瑞昌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2-05-10 ISBN/ISSN:978986221946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