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擇也許能解釋「適者生存」,但無法解釋「適存者的到來」。
大師級科學家華格納提出「創新力法則」,揭開演化令人震驚的隱藏結構!
大師級科學家華格納提出「創新力法則」,揭開演化令人震驚的隱藏結構!
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的百餘年後,始終存在耐人尋味的一道難題:
自然界中的「創新」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他的天擇理論解釋了有用的適應性如何隨時間被保存下來,但同時也製造了演化的最大疑問:「生物的適應性是怎麼出現的?」
地球上第一個生命誕生至今,三十八億年間發生的隨機突變,真的可以為翅膀、眼球、偽裝、乳糖消化、光合作用,以及其他自然創造的驚奇負責嗎?假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演化的速度和相對效率背後的機制又是什麼呢?
當年達爾文不知道什麼是突變、基因、DNA雙螺旋、轉錄與轉譯作用、DNA定序,也缺乏遺傳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甚至處理大量資訊的知識和技術,但他早在一百六十年前提出的遠大洞見開啟了生物學百家爭鳴般的精采發現──如今,我們終於有能力朝「生物適應性的出現」這個巨大謎團靠近了!
全球知名的演化生物學家安德里亞斯.華格納憑藉超過十五年的研究,呈現出達爾文理論遺失的拼圖。利用早期科學家意想不到的實驗性及計算性技術,他發現驅動適應的不只是偶然,而是一套法則,允許大自然在隨機變異上花費的小部分時間裡,發現新的分子與運作機制。
一絲不苟地研究、仔細地論證、充滿感召力地寫作,並列舉了五花八門又迷人的實例,《生命如何創新》獻上生命豐富多樣性謎團的最後一片拼圖。
▍《金融時報》2015年度選書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黃貞祥_策劃、審訂、導讀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丁照棣_專文推薦
▍同聲推薦
李文雄(中央研究院院士,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林仲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李壽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蔡怡陞(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鄭國威(PanSci泛科學總編輯)
顏聖紘(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
▍媒體書評
★ 華格納的書迷人而討喜,將使你對創新的謎團大開眼界。他的見解令你著迷又吃驚,並改變你思考的方式。
──《從叢林到文明,人類身體的演化和疾病的產生》作者 丹尼爾.李伯曼
★ 《生命如何創新》揭開演化令人震驚的隱藏結構。生物學家長久以來都沒有看到這個結構,但它終究讓達爾文偉大的想法得以存活,同時讓生命看起來比你所想的更加富裕非凡。達爾文應該會喜歡這本書,我想你也是。
──《自然》前編輯暨《自製的掛毯》作者 菲利普.鮑爾
★ 若有個主題比「才智的演化」更具爭議性,那就是「演化的才智」。安德里亞斯.華格納針對生物演化中由細節到總體的才智,提出一個引人入勝、有權威性而且最新的論點,這個論點也堅持住了。
──《圖靈的大教堂》作者 喬治.戴森
★ 安德里亞斯.華格納是少見有才智能看見演化真實本質的科學家,並有勇氣對抗用無神論否認事實的人,這些人和宗教狂熱者用相同的荒謬怒斥使達爾文沉默。
──《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作者 法蘭克.佛杜錫克
★ 華格納切進生命系統創新的核心,基本、有趣,而且卓越。
──《思考的藝術》作者 魯爾夫.杜伯里
★ 《生命如何創新》用閃爍的文學散文訴說嶄新的科學洞察。這本書是座里程碑,結合了獨創性或可能是革命性的想法,並優雅地解釋它們。特別是基因型網絡的概念(有數千種方法能改變代謝路徑而不會使它停止運作),允許能解決一道不朽的難題:天擇如何成為那股創新的力量。
──《紅色皇后》作者 麥特.瑞德里
★ 安德里亞斯.華格納的《生命如何創新》一書,優雅地探索一條精巧的捷徑,大自然用這條路來抵達看似不可能前往的地方。
──《週日泰晤士報》
★ 驚人的觀點、富有洞察力的光芒、巧妙的熱情,這本書從無機的頁面,將知識傳遞到我們有機的大腦。
──《科克斯書評》星級評論
★ 這本書對當今的研究有適宜的描述和清楚的分析,那些想更加了解演化機制的人將會深感有趣。
──《圖書館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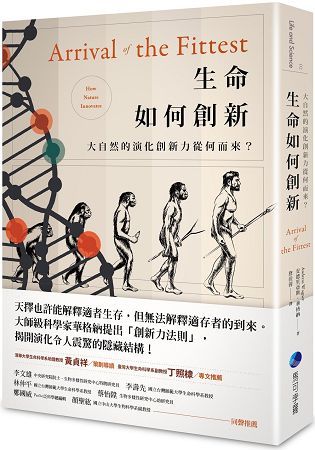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