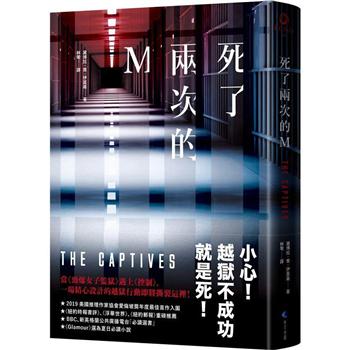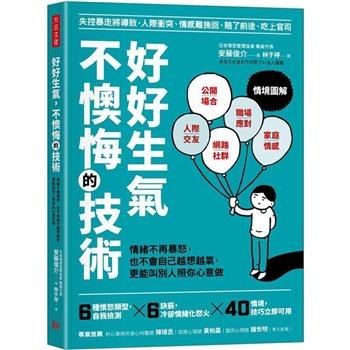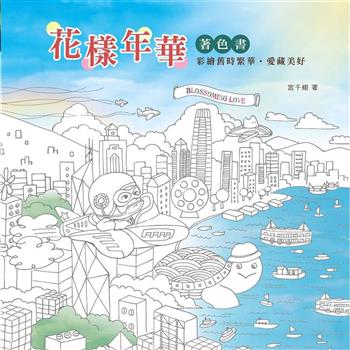花園裏的獨角獸 【美國】詹姆斯‧瑟伯
從前,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有一個男人坐在廚房角落的小飯桌旁,剛從他的炒蛋上抬起眼來,就看見花園裏有隻潔白頭頂上長著金色角的獨角獸(獨角獸相傳與馬相似,前額正中長有一角,性溫和有「神獸」之稱,象徵吉祥。),在安詳地囓嚼著玫瑰花。這個男人上樓到臥室去,見妻子還在酣睡,他叫醒了她。
「花園裏有隻獨角獸在吃玫瑰花呢。」他說。
她睜開了一隻眼睛,不高興地看了看他。「獨角獸可是神獸。」她說完就又轉過身去。
男人慢慢下了樓,走出屋子來到花園。獨角獸還在那兒,正在鬱金香花叢中慢騰騰地嚼著。
「來這兒,獨角獸。」男人說,他拔起一枝百合花給牠,獨角獸悠然自得地把它吃了。
由於花園裏有隻獨角獸,這個男人喜出望外,又跑到樓上叫醒妻子。
「那隻獨角獸吃了一枝百合花。」他說。
他妻子從床上坐了起來,冷冷地看著他。
「你真是個神經病,」她說,「我要把你關進瘋人院裏去。」
這個男人從來都不喜歡「神經病」和「瘋人院」這種字眼,在這陽光燦爛的早晨,花園裏還來了隻獨角獸的當兒,聽來就更不入耳了。
他想了想說道:「等著瞧吧。」他走到門口時又對她說,「牠前額當中還有一支金色的角。」說罷,又回到花園去看那隻獨角獸了。但是,這時獨角獸已經走開,這個男人就坐在玫瑰花叢中入睡了。
妻子等丈夫一離開屋子,就飛快地起了床,穿好衣服。她興奮激動,眼裏閃出幸災樂禍的亮光。她打了個電話給警察局,又給一位精神病醫生打了個電話。她叫他們馬上來她家,再帶上一件給瘋子穿的緊身衣(這是一種白色緊身衣,有很長的袖子,可綁在瘋人身後,使其動彈不得。)。
警察和精神病醫生來到她家,坐在椅子上,頗感興趣地看了看她。
「我的丈夫,」她說,「今天早晨看見了一隻獨角獸。」
警察瞧瞧精神病醫生,精神病醫生瞧瞧警察。
「他對我說,牠吃了一枝百合花,」她說。
精神病醫生瞧瞧警察,警察瞧瞧精神病醫生。
「他對我說,牠的前額當中還有一支金色的角。」她說。
這時,警察見精神病醫生發出的一個正式暗號,便一躍而起抓住了那個妻子。
他們費了好大的勁才制服了她,因為她拼命掙扎,但是最後還是把她鎮住了。就在給她穿上緊身衣的時候,她的丈夫走進了屋子。
「你對你妻子說你看見一隻獨角獸了嗎?」警察問道。
「當然沒有啦,」那丈夫說,「獨角獸可是神獸。」
「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精神病醫生說道,「把她帶走吧。很對不起你,先生,可是你的妻子瘋得跟一隻#鳥一樣。」
於是,她罵著、喊著,就被他們帶走了。
他們把她關進了瘋人院。從此以後,這個丈夫過得很快活。
【品味】
《花園裏的獨角獸》是一篇寓言體的喻義小說,但我們也可以當做普通家庭小說來閱讀。象徵吉祥的獨角獸的闖入,竟然使這一完整的家庭遭到破裂,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由於花園裏突然來隻獨角獸,丈夫喜出望外,連忙叫醒正在酣睡的妻子,想讓妻子也欣賞一下這一神奇的動物。哪知妻子不僅不感興趣,反而罵他是個「神經病」,聲稱「要把他關進瘋人院裏去」。並且立即採取行動,企圖把誓言變成現實。
丈夫呢?向來就不喜歡「神經病」、「瘋人院」之類的字眼,這次在陽光燦爛的早晨,花園裏還來隻獨角獸的當兒,聽到此類字眼更為反感,「等著瞧吧」。一語點出了丈夫的惱怒和伺機報復的心理。正因為如此,當警察詢問情況時,丈夫隱瞞事實真相,致使沒有發瘋的妻子被當做瘋子,關進了瘋人院。可見,這一對夫妻的感情基礎早已破裂,其家庭只不過剩下了一個外殼而已。獨角獸的到來,為他們相互擺脫對方提供了可利用的時機。
小說的結局是妻子被關進了瘋人院,丈夫從此過得很快活。其實,換一個結局,丈夫被關進瘋人院,妻子也會從此過得很快活。因為這個家庭的破裂是必然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獨角獸的確是吉祥的象徵。但這是針對勝利者而言的,對失敗者,牠則變成了災禍的預兆!
女巫的麵包 【美國】歐‧亨利
瑪莎‧米查姆小姐是街角那家小麵包店的老闆娘(那種店鋪門口有三級臺階,你推門進去時,門上的小鈴就會叮零叮零響起來)。
瑪莎小姐今年四十歲了,她有兩千元的銀行存款,兩枚假牙和一顆多情的心。結過婚的女人真不少,但同瑪莎小姐一比,她們的條件可差得遠多啦。
有一個顧客每星期來兩三次,瑪莎小姐逐漸對他產生了好感。他是個中年人,戴眼鏡,棕色的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的。
他說英語時,帶著很濃的德國口音。他的衣服有的地方破了,經過織補,有的地方皺得不成樣子。但他的外表仍舊很整齊,禮貌又十分周全。
這個顧客老是買兩個放得較久的麵包。新鮮麵包是五分錢一個,舊麵包五分錢卻可以買兩個。除了舊麵包以外,他從沒有買過別的東西。
有一次,瑪莎小姐注意到他手指上有一塊紅褐色的汙跡。她立刻斷定這位顧客是藝術家,並且非常窮困。毫無疑問,他準是住閣樓的人物,他在那裏畫畫,啃麵包,呆想著瑪莎小姐麵包店各種各樣好吃的東西。
瑪莎小姐坐下來吃肉排、麵包、果醬和喝紅茶的時候,常常會好端端地嘆起氣來,希望那個斯文的藝術家能夠分享她的美味的飯菜,不必待在閣樓裏啃硬麵包。瑪莎小姐的心,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是多情的。
為了證實她對這個顧客的職業猜測得是否正確,她把以前買來的一幅畫,從房間裏搬到外面,擱在櫃檯後面的架子上。
那是一幅威尼斯風景。一座壯麗的大理石宮殿(畫上這樣標明)矗立在畫面的前景——或者不如說,前面的水景上。此外,還有幾條小平底船(船上有位太太把手伸到水面,帶出了一道痕跡),有雲彩、蒼穹和許多明暗烘托的筆觸。藝術家是不可能不注意到的。
兩天後,那個顧客來了。
「兩個舊麵包,勞駕。」
「夫人,你這幅畫不壞。」她用紙把麵包包起來的時候,顧客說道。
「是嗎?」瑪莎小姐說,她看自己的計謀得逞了,便大為高興。
「我最愛好藝術和——」(不,這麼早就說「藝術家」是不妥的)「和繪畫。」她改口說,「你認為這幅畫不壞嗎?」
「宮殿,」顧客說,「畫得不太好。透視法用得不真實。再見,夫人。」
他拿起麵包,欠了欠身,匆匆走了。
是啊,他準是個藝術家。瑪莎小姐把畫搬回房間裏。
他眼鏡後面的目光是那麼的溫柔和善啊!他前額有多麼寬闊!一眼就可以判斷透視法——卻靠舊麵包過活!不過天才在成名之前,往往要經過一番奮鬥。
假如天才有兩千元銀行存款、一家麵包店和一顆多情的心作為後盾,藝術和透視法將能達到多麼輝煌的成就啊——但這只是白日夢罷了,瑪莎小姐。
(最近一個時期,他來的時候往往隔著櫃臺聊一會兒。他似乎渴望著瑪莎小姐的愉快的談話。他一直買舊麵包。從沒有買過蛋糕、餡餅,或是她店裏的可口甜點。)
她覺得他彷彿瘦了一點,精神也有點頹唐。她很想在他買的寒酸的食物裡加上一些好吃的東西,只是鼓不起勇氣來。她不敢冒失。她瞭解藝術家高傲的心理。
瑪莎小姐在店裏的時候,還穿起那件藍點子的綢背心來了。她在廚房熬了一種神秘的榅柏子和硼砂的混合物,有許多人用這種汁液美容。
一天,那個顧客又像平時那樣來了,把五分鎳幣往櫃檯上一擱,買他的舊麵包。瑪莎小姐去拿麵包的當兒,外面響起一陣嘈雜的喇叭聲和警笛聲,一輛救火車隆隆駛過。
顧客跑到門口去張望,遇到這種情況,誰都會這樣做的。瑪莎小姐突然靈機一動,抓住了這個機會。
櫃檯後面最低的一格架子裏放著一磅新鮮的牛油,送牛奶的人拿來還不到十分鐘。瑪莎小姐用切麵包的刀子,把兩個舊麵包都拉了一條深深的口子,各塞進一大片牛油,再把麵包按緊。
顧客再進來時,她已經把麵包用紙包好了。
他們很愉快地扯了幾句。顧客走了,瑪莎小姐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可是心頭不免有點著慌。
她是不是太大膽了呢?他會不高興嗎?絕對不會的,食物並不代表語言,牛油不象徵有失閨秀身分的冒失行為。
那天,她的心思老是在這件事上打轉,她揣摩著他發現這場小騙局的情景。
他會放下畫筆和調色板。畫架上支著他正在畫的圖畫,那幅畫的透視法一定是無可指責的。
他會拿起乾麵包和清水當午飯。他會切開一個麵包——啊!
想到這裏,瑪莎小姐的臉上泛起了紅暈。他吃麵包的時候,會不會想到那隻把牛油塞在裏面的手呢?他會不會——
前門上的鈴鐺惱人地響了。有人鬧鬧嚷嚷地走進來。
瑪莎小姐趕到店堂裏去。那兒有兩個男人。一個是叼著菸斗的年輕人——他以前從沒見過,另一個就是她的藝術家。
他的臉脹得通紅,帽子推到後腦勺上,頭髮揉得亂蓬蓬的。他握緊拳頭,狠狠地朝瑪莎小姐搖晃。竟然向瑪莎小姐搖晃。
「Dumm kopf!(笨蛋!)」他拉開嗓子嚷道;接著又喊了一聲「Tausendonfer(千雷轟頂的!)」或者類似的德國話。
年輕的那個竭力想把他拖開。
「我不走,」他怒氣沖沖地說,「我非跟她講個明白不可。」
「你把我給毀了。」他嚷道,他的藍眼睛幾乎要在鏡片後面閃出火來。「我對你說吧,你是個討厭的老貓!」
瑪莎小姐虛弱無力地倚在貨架上,一手按著那件藍點子的綢背心。年輕人抓住同伴的衣領。
「走吧,」他說,「你也罵夠啦。」他把那個暴跳如雷的人拖到門外,自己又回來了。
「夫人,我認為應當把這場吵鬧的原因告訴給你,」他說。「那個姓布盧姆伯格的,他是建築圖樣設計師,我和他在一個事務所裏工作。」
「他在繪製一份新市政廳的平面圖,辛辛苦苦地幹了三個月,準備參加有獎競賽,他昨天剛上完墨。你明白,製圖員總是先用鉛筆打底稿的。上好墨之後,就用舊麵包屑擦去鉛筆印。舊麵包比橡皮擦好用得多。
「布盧姆伯格一向在你這裏買麵包。嗯,今天——嗯,你明白,夫人,裏面的牛油可不——嗯,布盧姆伯格的圖樣成了廢紙。只能裁開來包三明治了。」
瑪莎小姐走進廚房。她脫下藍點子的綢背心,換上那件穿舊了的棕色的嗶嘰衣服。接著,她把榅柏子和硼砂煎汁倒在窗外的垃圾箱裏。
【品味】
歐‧亨利是美國著名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世界三大微小說大師之一。他善於捕捉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而富於哲理的戲劇性場景,用漫畫般的筆觸勾勒出人物的特點。作品情節的發展很快,在結尾時,突然出現一個意料不到的結局,使讀者驚愕之餘,不能不承認故事合情合理,進而讚嘆作者構思的巧妙。
他的文字生動活潑,善於利用雙關語、諧音和舊典新意,妙趣橫生。他還以準確的細節描寫,製造與再現氣氛。《女巫的麵包》就充分體現了作者的這一風格。
瑪莎小姐開了一家麵包店,她很富有。有一個顧客,他每星期來三兩次,每次只買兩個舊麵包,有一次,瑪莎小姐發現那個顧客的手上有一塊紅褐色的汙跡,瑪莎小姐斷定那個顧客是一個藝術家,是那種在閣樓上啃舊麵包的藝術家,於是,就在兩個舊麵包裏各夾了一大塊牛油,等到那個顧客來時,瑪莎小姐把夾了牛油的舊麵包給他。
沒想到,他是一個建築圖樣設計師,舊麵包擦鉛筆印比橡皮好,而用了那個夾了黃油的舊麵包後,建築圖就成了廢紙!
有時候生活就是這樣——好心辦錯事,瑪莎小姐在麵包裏放上牛油,完全是對這位先生的同情和愛,卻誤解了它的用途,結果反倒使那男設計師感到十分生氣,也把他長久以來的心血給毀了,這是多麼不應該啊。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詹姆斯.瑟伯等的圖書 |
 |
$ 135 ~ 179 | 花園裏的獨角獸【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詹姆斯.瑟伯等 / 譯者:盛文林 出版社: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8-2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320頁/15*21mcm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詹姆斯
詹姆斯,法譯雅姆,西譯海梅,葡譯雅伊梅,義大利語賈科莫,愛爾蘭及蘇格蘭語謝馬斯或謝穆斯,是一個西方社會常見的人名。英、西、葡等語文中「James、Jaime、Giacomo、Séamas」的名稱則來自於古法語,最終源於粗俗拉丁語中Iacobus至Iacomus的一個演變,前者演變為雅各布及其變體,均為希伯來語的雅各之意。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花園裏的獨角獸
大千世界裏,無奇不有,充滿了各種你想得到的和你想不到的事,
而人性的光明與黑暗面,更無時不考驗著我們的心,透過黑色幽默,看盡人生百態。
花園裏的獨角獸是怎麼回事?
是先生的謊言還是妻子的幻想?
神秘的魔盒中裝的是什麼?
是珍奇的珠寶還是家的味道?
能讓人幸福的奇妙禮物是什麼?
一枚鑽戒、一棟房子,還是一朵玫瑰花?
神秘、幽默、驚奇,
令人回味無窮的故事盡在其中!
◎有著超神準預測能力的主播,反而面臨了無人敢接近的窘境?
◎情侶間看似公平的各自付賬,然而事實上果真如此嗎?
◎小嬰兒怎麼會非法入境?無助的母親該怎麼辦?
◎可惡的小偷偷走了什麼?是珍貴的珠寶還是純潔的人心?
◎不小心拿到破損的鈔票時,你會拿去銀行換一張新的,還是夾在完好的鈔票中偷偷用出去?
章節試閱
花園裏的獨角獸 【美國】詹姆斯‧瑟伯
從前,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有一個男人坐在廚房角落的小飯桌旁,剛從他的炒蛋上抬起眼來,就看見花園裏有隻潔白頭頂上長著金色角的獨角獸(獨角獸相傳與馬相似,前額正中長有一角,性溫和有「神獸」之稱,象徵吉祥。),在安詳地囓嚼著玫瑰花。這個男人上樓到臥室去,見妻子還在酣睡,他叫醒了她。
「花園裏有隻獨角獸在吃玫瑰花呢。」他說。
她睜開了一隻眼睛,不高興地看了看他。「獨角獸可是神獸。」她說完就又轉過身去。
男人慢慢下了樓,走出屋子來到花園。獨角獸還在那兒,正在鬱金香花叢中...
從前,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有一個男人坐在廚房角落的小飯桌旁,剛從他的炒蛋上抬起眼來,就看見花園裏有隻潔白頭頂上長著金色角的獨角獸(獨角獸相傳與馬相似,前額正中長有一角,性溫和有「神獸」之稱,象徵吉祥。),在安詳地囓嚼著玫瑰花。這個男人上樓到臥室去,見妻子還在酣睡,他叫醒了她。
「花園裏有隻獨角獸在吃玫瑰花呢。」他說。
她睜開了一隻眼睛,不高興地看了看他。「獨角獸可是神獸。」她說完就又轉過身去。
男人慢慢下了樓,走出屋子來到花園。獨角獸還在那兒,正在鬱金香花叢中...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詹姆斯‧瑟伯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8-21 ISBN/ISSN:978986580317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