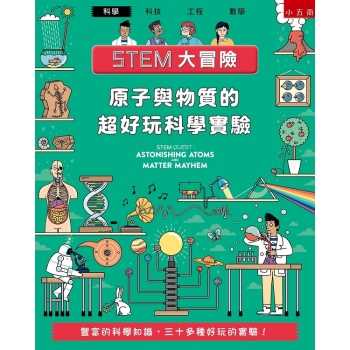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諾艾爾.卡列夫的圖書 |
 |
$ 1190 ~ 1275 | 大師級感動:從文學到影像的距離【精裝】(四冊套書: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後窗與另幾宗謀殺、肝臟大夫、通往死刑台的電梯)
作者:亨利-皮耶.侯歇、 (Henri-Pierre Roché,Cornell Woolrich,Sakaguchi Ango,Noël Calef) / 譯者:黃琪雯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出版日期:2025-06-0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精裝 / 1344頁 / 12.5 x 18 x 10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280 ~ 360 | 通往死刑台的電梯(法國電影新浪潮健將路易馬盧的黑色靈思) (電子書)
作者:諾艾爾.卡列夫(Noël Calef) / 譯者:陳郁雯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出版日期:2024-11-0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艾爾
星海爭霸是由暴雪娛樂有限公司製作發行的一系列戰爭題材科幻遊戲。遊戲系列主要由克里斯·梅森與James Phinney設計開發。遊戲的劇情發生在26世紀初期的克普魯星區——位於遙遠的銀河系中心。劇情講述了三個種族之間的鬥爭,包括來自地球的人類、神秘而強大的神族以及異形蟲族。1998年即時戰略遊戲《星海爭霸》發行,隨後便產生了一大批衍生產品,包括8部相關題材的小說、1款桌上遊戲以及其他授權商品比如模型玩具等。
暴雪娛樂於1995年開始著手設計《星海爭霸》系列遊戲。這款遊戲首先在1996年的電子娛樂大展上進行展示,並最初採用了《魔獸爭霸II》的遊戲引擎。《星海爭霸》同樣使暴雪娛樂建立了影片製作部門,最初用以在《星海爭霸》的故事主線中插入一系列過場電影短片。
1998年《星海爭霸》發行之後,大部分《星海爭霸》開發人員繼續進行了其官方資料片《怒火燎原》的開發。2001年,《星海爭霸:暗影獵殺》開始由Nihilistic Software領導開發。不同於先前的即時戰略系列遊戲,這是一部動作冒險遊戲。然而在2004年,《星海爭霸:暗影獵殺》宣布被無限期推遲。《星海爭霸II》於2010年7月27日發行。《星海爭霸II》資料片《星際爭霸II:蟲族之心》則於2013年3月12日發行。《星海爭霸II》最後一部資料片《星海爭霸II:虛空之遺》在2015年11月10日發行。和《星海爭霸II:自由之翼》以及《星海爭霸II:蟲族之心》不同的是,這次虛空之遺在中國大陸的發售與全球Battle.net伺服器的時間同步。於2017年8月14日《星際爭霸》及《星際爭霸:怒火燎原》資料片高畫質重製版正式發售。
原版《星海爭霸》及其資料片發行初期即受到大量好評,僅於1998年即售出了150萬套,,是當年銷量最好的PC遊戲;而十年內總銷售量則超過950萬套。 部分評論媒體將其視為史上最為傑出 和重要 的遊戲之一,並讚揚它對於即時戰略遊戲發展的貢獻。這一系列的遊戲吸引了全世界眾多的玩家。特別是在韓國,職業選手及戰隊在電視上進行對抗,收視率很好。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